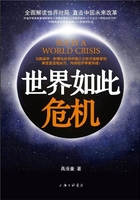回到贵阳后,刘子富觉得有许多话需要“向组织说”,于是提起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石宗源看到报告后做了很深的思考,”刘子富说,随后,省委书记在自己的驻地与他进行一次2个小时40分钟的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在这次谈话中,刘子富提出想返回瓮安,深入进行采访。石宗源立即表示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了招呼。于是刘子富重回瓮安,“这次采访前后经历14天,一共采访了87个人,涉及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
这次采访对刘子富的震撼是强大的。被免职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与刘子富长谈了3个多小时,“他的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他看来,王勤并不是一个腐败官员,“他不打麻将,不进舞厅,有空就进办公室看文件、看书学习。他在瓮安工作10年,没有过一个节假日、星期天,也没有过一个‘黄金周’。”
王勤也不是一个庸官。“他1998年刚调到瓮安时,瓮安县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县委常委会讨论支出项目时,细到50元的支出款项;县里开‘两会’,连用多少张纸都要事先批准。财政最困难时,党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拿香烟来抵。”
2000年以后的7年时间,王勤所带领的班子让瓮安县GDP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了近3倍。但是GDP并没有换来社会稳定。“王勤现象”引发刘子富的深思。
有专家预言:“瓮安‘6·28’事件是可以复制的。”这句话不幸言中,在其后,又发生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其中以“孟连事件”和“石首事件”最为典型。
2008年7月,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胶农因纠纷与孟连勐马橡胶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发生冲突。7月15日,孟连县派出工作组处理,并贴出限令自首通告。7月19日上午,当地民警传唤冲突人员时,遭到当地500多名村民、胶农围攻,致使41名民警受伤、8辆警车被砸坏,15名群众受伤;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致多名村民受伤,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2009年6月17日,湖北荆州市辖内石首市一酒店内发现一具尸体,死者为酒店厨师,留有一份遗书,因死因不明,死者家属将尸体停放在酒店大厅。事后两天,数千群众围观,阻碍交通,与部分警民发生冲突,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
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2006年逾9万起。
如何阻止“瓮安事件”的继续复制?亡羊补牢,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对瓮安事件作更深入的检讨。
富人投靠黑社会
刘子富的调查揭示,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多个黑帮组织。一位县人大代表说,黑恶势力比公安机关的势力还强大,5分钟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2小时都召不齐这么多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了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
“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瓮安县一位企业家说。
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本身就以团体成员参与,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公然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2元,老百姓叫苦不迭,怨声载道。
舒泰峰:根据您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瓮安黑社会横行?
刘子富: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比如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则麻木不仁。
第三,打击不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舒泰峰:“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共有300多人,其中学生、教师110多人,占参与打砸抢烧总人数的比重高达36.6%。在现场,甚至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洒在警察身上。为什么学生会冲在第一线,是出于仇视吗?
刘子富:八九岁的小姑娘,你说她仇视警察,这不大说的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参与打砸的中学生,多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以及凑热闹的性质。但是这背后仍然暴露了很深的社会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容易走向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死者李树芬所在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告诉我,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进入市场经济社会,进入开放型社会,追求自我意识的父母不少,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单亲家庭的学生比重高达13.3%。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不少青少年走向歧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反映出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帮派文化”已经渗透校园。
舒泰峰:教育体制的问题又怎么理解?
刘子富:事实上,瓮安教育质量在黔南州名列前茅,升学比例高,近年来每年高考都有2000多名学生被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录取。但是我在对一些校长和教师采访时,他们对此并没有流露多少喜悦,相反,吐露的是苦涩与自责。
他们说出了众多中小学生参与“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这是我国教育评价机制出了偏差,过分强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考评不到位,一俊遮百丑,一考定终生,驱使学校和教师重授业,轻传道。
瓮安县曾经推行过“教师末位淘汰制”,期末考试教学成绩排名倒数后三位的老师,一律被调到边远的学校去,这无异于“发配充军”,这更加驱使教师只关心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顾不上抓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
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祖祖辈辈靠两口井吃水,现在被磷矿给挖断了,吃的是从13里外引来的明沟水,牛粪、马尿、鸡屎都冲下来,看见了根本无法咽下去,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我们农民怎么活?”这是玉山镇大坪村村民杨天友接受刘子富采访时所说。
瓮安县磷、煤、铁、钼、铅、锌等矿产资源丰富。近几年来,随着矿产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矿产资源开发成为拉动当地财政收入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因素。2007年,瓮安以煤、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工业企业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0%。
矿产资源开发让政府增加了GDP和财政税收,让矿老板赚鼓了腰包,而普通群众特别是资源富集地的农民,他们不仅没有受惠,反而“守着煤山没煤烧”、“守着磷矿没钱赚”,原来山清水秀的家园,被毁损得百孔千疮: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房屋开裂,水源枯竭……不要说子孙后代,就是当代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都丧失殆尽了。
对抗随之发生。贵州爱思开老虎洞磷矿开发有限公司要在田坝村征地,征地费太低,村民不同意。企业就请社会上的3个恶棍将反对的人毒打一顿。
田坝村民咽不下这口恶气,几百人去堵路、堵车。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文举站出来替乡亲们说话,要求解决开矿挖断水源后的饮水和灌溉问题,要求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希望每吨矿提5~10元钱,用于整治矿区生态环境。
2007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派7个村民代表去解决问题,王文举他们高高兴兴就去了,想不到一去就被公安机关抓捕。消息传回田坝村,60多个村民立即赶去讨说法,被公安人员打伤13人,当场抓了20人,有的关了15天,有的关了20天。
舒泰峰:您在书中也采访了矿主,他们认为有的农民漫天要价,无理取闹,阻止开发,看起来矿主和农民各有各的理,关键问题在哪里?
刘子富: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政府应该出来进行协调,对农民进行合理的补偿。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为了拿管理费,抽税,图一时的政绩,屁股坐在矿主一边,失去了公道。
这造成了利益受损群众有冤无处诉,政府也丧失了在群众心中的尊严和价值。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总结起来就是“政府不作为,企业出下招,农民使狠招”。
刘子富通过调查发现,瓮安县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非常严重,县级工商、税务、金融、药检、质检、烟草等有关部门上划州垂直管理,严重削弱了县级政府的调控能力。
烟草部门在垂直管理部门中比较典型。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农村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瓮安烟草产业曾一度辉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离不开“烟财政”的支撑,每到发展烤烟生产季节,党委、政府都要花很大精力去发动农民种烤烟,深入各家各户,甚至田间地头动员农民种烤烟。可是,到了烤烟收购季节,烟草部门对农民出售烤烟在等级上却经常与烟农发生争执,个别烟叶收购站甚至发生压级压价坑农的现象。农民抱怨“蹲着栽烟,跪着卖烟”。往往在农民与烟草收购部门发生矛盾的时候,管理体制决定党委、政府说不上话,想保护农民的利益也毫无办法。相反,农民却把怨气撒向发动种烟的党政干部身上,弄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非常紧张。
瓮安现任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好多部门上划垂直管理了,手中又有特权,吃拿卡要,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搞坏了,群众就把个人的行为当成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行为,就把对个人不满的账,通通记在党委和政府身上。”
舒泰峰:您认为现在垂直部门太多了,但如果都交给地方,是不是又造成另一种倾向,即地方权力太大,这是不是也会带来另一种问题?
刘子富:长期以来,我国对“条块分割”体制的利弊争论不休,收了放,放了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我告诉你真话,以我多年采访得出的结论,现在走得过头了。中央或省垂直管理的部门越划越多,由几个、十几个增加到目前的工商、税务、金融、烟草、电力、国土、公检法司、质检、药监等20多个。
说白了,就是凡有好处的,有利益的都上收了,几乎将地方抽空。这导致地方管理的弱化。这不但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加剧了干群矛盾激化。
干部为什么躲避群众
总结这些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干群关系的恶化是其中核心的原因。坊间有个说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80年代以后就变成了油水关系;90年代以来则成了水火关系。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和石首事件为之提供了真实的注脚。“失人心者失天下”,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说明这个道理——每一个国家或王朝勃兴之时,朝野必能进行很好的沟通,而其之将衰,庙堂与草野的距离一定越拉越远。
上述3个事件发出了这样一种警示——我国的干群关系已经到了必须改善的关键时刻。
改善干群关系,关键在于官(干部),而不在于民。历来中国的老百姓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去与官员接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是严肃而富有威严的。即使如今官员被称为“公务员”,这种传统的心理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地改观。
因而,在干群关系中,官员居于主导地位。于是,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时期,只要官员主动亲民,干群关系就好;一旦官员脱离群众,干群关系就疏远乃至恶化。
就以20世纪80年代为例,虽然那时候干群关系已经出现下滑趋向,被戏称为“油水关系”,但事实上那个时期的干群关系仍然让许多人怀念。
因向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而闻名的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有一次与笔者谈起20世纪80年代的干群关系,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说,那时候,湖北省委书记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在农村做调研,并经常与农民同吃同住。
湖南农民、省劳动模范杨国锋说20世纪80年代时他可以经常去县领导家里坐一坐。到了1999年,他去找县委书记,等了一个多小时,书记的秘书一直在打游戏,他想知道书记的电话,秘书说:“不行,那是机密。”杨国锋的体会是那时“再苦再累,心里都很舒畅,不像现在这么压抑”。
孟连“7·19”事件后,据云南官方统计,县委书记胡文彬2007年下乡镇仅26次,都是当天返回;乡镇主要官员大都住在县城,周一上班,周末回家。
两相对比,问题昭然若揭。干群关系恶化不是群众脱离了干部,而是干部脱离了群众。现在的地方官员,行则警车开道,住则豪华酒店,试问还有几人能够深入农村,哪怕只是数天与农民同吃同住。这样的行事作风,对于改善干群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在一次研讨班上总结得很深刻,他说,陈毅当年率部队进驻上海,一再告诫部下不要惊扰市民。“我下乡,你们警车在前面开道,警笛越拉越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推到群众的对立面了!”他还说,“苏共垮台、齐奥塞斯库被乱枪打死,教训就是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