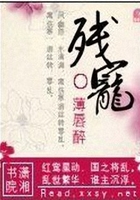伴随着宁月昭的呼喊声,等候在外的宫人们鱼贯而入。
“拿水来!”宁月昭眼角泪痕尤未干,唇边已经露出喜色。
宫人们见女皇提前苏醒,也是十分高兴。
宁月昭从宫女手上拿过水杯,以小勺舀了水,一点一点喂给女皇。
女皇依旧虚弱得很,干燥的喉头有了清水的滋润,她终于可以发出一些声音了,“别……为朕担心……生死……有命,不要……迁怒他人……”
原来,女皇虽然昏迷着,却对期间发生的事一清二楚。
宁月昭点了点头,“母皇,儿臣答应你,但您也一定要好起来!”
女皇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摇了摇头,“傻孩子……”
宁月昭将空了的杯子交给宫女,任性道:“儿臣就犯傻了,只要您能好起来。”
女皇看了看旁边的蒋年,吃力地抬手,摸了摸她的头,“朕……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朝蒋年的方向看了一眼,“不过现在……有蒋年在,朕就放心了……你们要好好的……”
宁月昭抓住女皇的手,哽咽道:“我们会的,儿臣……儿臣马上就下诏,将婚期提前!”
女皇欣慰地笑了,没有说话,只是努力地替宁月昭擦了擦眼泪,宁月昭抓住了她的手,紧紧握着。
无奈地摇了摇头,女皇看了看蒋年,朝他伸出另一只手。
蒋年见状,主动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
女皇将两只手交叠在一起,郑重道:“你们,一定要同心同德,相互扶持……”
蒋年的手覆在宁月昭的手上,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掌下仿若无骨的柔软,毫不犹豫地,他紧紧地握住了那只手。
宁月昭也察觉了蓦然收紧的那只手,碍于女皇灼灼的目光,她不好抽回手。
女皇看着他俩这样,释然一笑,觉得此生也无憾了。
昇龙殿内的宫人们,瞧见这一幕,也都纷纷用袖子偷偷抹眼泪。
当天夜里,宁月昭亲笔写下诏书,写完最后一个字时,眼睛不觉湿润了。
她闭上眼,深深吸一口气,拿起大印,重重盖上。
她和蒋年的婚事,提前到十日后。
因为礼部的官员先前已经将大婚的吉服制好了,属于她的那套礼服早就已经送到了锦绣宫,只是她一直都没有去试。
婚期敲定之后,就是大婚典礼的事了。因为时间紧迫,能够从简的就尽量从简。
可是尽管如此,依旧是忙坏了礼部的官员。
就在一干人等忙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女皇却传召了蒋年进宫。
这一日,女皇起身后精神好了许多,又见窗外阳光灿烂,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宁月昭命人准备了轮椅,好让女皇可以去御花园转转。
关于应该由谁来推女皇,宁月昭和蒋年还发生了小小的“不愉快”。
“我是男子,这种力气活自然应当由我来。”蒋年如是说道。
宁月昭却也不甘示弱,“男子又如何,我是母亲的女儿,我推她理所当然。再说了,我也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女子,不至于一个轮椅也推不动。”
最后,她也不等蒋年再开口,就直接亲自推着女皇往御花园走去了。
望着她的背影,蒋年笑了笑,缓缓地跟上,与她并肩而行。
此时已经是盛夏了,太液池的荷花进入了盛放期。
鉴于之前并蒂莲带来的不美好的回忆,三人自动选择避开这一带。
宁月昭推着女皇向紫薇苑走去,夏季少花,紫薇花却正当怒放。
盛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
行走在或红或白或紫的花海中,锦绣成堆,清香袅袅,浑然忘却了凡世的忧愁。
宫人们已经在凉亭石阶处铺上了木板,宁月昭不费什么力就把轮椅推上了凉亭。
这凉亭修在紫薇苑地势稍高处,极目望去,鲜花成海,再配以苑中的假山长廊,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宁月昭将轮椅停好,又细心帮女皇掖了掖膝上的薄毯。
女皇慈爱地替她将一络发丝别到耳后,笑道:“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一转眼,我的阿昭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宁月昭笑了笑,从宫女手中接过茶盏,递给女皇。
因为女皇在病中,不宜饮茶,杯中装得是温热的清水。
蒋年看着她们母女相互依偎的场景,突然心头一动,提议道:“陛下,微臣为您和公主作一幅画如何?”
女皇闻言,当即应下,“甚好。来人,去取笔墨来。”
宁月昭知道他擅长丹青,从之前的并蒂莲图就可以看出来了,便没有吭声默许了。
很快,宫人们就在凉亭内摆上了长案,笔墨纸砚及各色颜料依次摆好。
蒋年将宽大的袖子半挽起,固定好,用镇纸将宣纸铺平。
他却不急着下笔,反而轻轻闭上了眼睛。
宁月昭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道:“你在做什么?”
哪有人闭着眼睛作画的?在一旁伺候的宫人们也都好奇地看着这位状元郎。
蒋年依旧闭着眼,左手竖起一根食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不要吵。”
女皇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拉了一下宁月昭的衣袖,“不要急,蒋年的画技我们都见过的,朕猜他大约是有什么独门画技要施展。”
蒋年倏然睁开眼,如墨玉般的眸子流动着华彩,笑道:“独门秘技倒是没有,臣刚才只是在心中勾勒陛下和公主的风采。画人物贵在传神,所以你们也不必拘着不动,随意些。”
说完,蒋年就提笔落墨,笔下如有神。
宁月昭打量着他专注的神情,一种安心的情愫油然而生。
这时,正好蒋年抬头看向她,两人目光相接。
蒋年笑了笑,继续低头作画。
宁月昭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得看向亭外的花海,转移视线。
他们的小动作都落在了女皇眼中,她轻轻的笑了笑,满怀欣慰。
大约一个时辰后,蒋年搁了笔,松了一口气。
两个宫人走上前,一左一右,拿起画作,向女皇展示。
只见画上的女皇身着玄色常服,头戴玳瑁钗,神态端庄,全然不见一丝病容。身着红色宫装的公主依偎在女皇膝头。女皇端庄威严的脸上带着一丝慈爱的笑,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宁月昭的发鬓,嘴角微微翘起。
女皇看着那画,不禁抚上自己的脸颊,愣愣地道:“这是朕吗?”
蒋年微微欠身,道:“在微臣心中,陛下的形象就是如此。”
女皇顿了顿,叹息道:“若是早几年,或许还有着风姿,至于现在……”
顿了顿,她又继续道:“也罢,总是要留个好的影像的,不然日日对着形容枯槁的画像,也太折磨人了。”
总体上,女皇心里还是十分满意蒋年的画作的。
宁月昭则有些不悦,只是她看女皇兴致这么高,不好意思泼冷水,便不做声了。她在心中腹诽道:“这个蒋年分明是擅加臆断地作画,画上的她容颜俏丽,神色娇羞,根本就不符合自己英明神武的皇太女形象啊!”
女皇欢喜地命人将画作拿去装裱,宁月昭心中默默吐血。
出来久了,女皇的身子也乏了,宁月昭送其回昇龙殿。
服过药后,女皇便歇下了。
宁月昭和蒋年并排走出昇龙殿,和蒋年一脸温和浅笑的神情相比,宁月昭的脸色堪用风雨如晦来形容。
蒋年是要出宫的,宁月昭则是要回锦绣宫,两人有一段路是同行的。
“你方才什么意思?”宁月昭沉着脸问道。
“什么?”蒋年被她没来由的责问弄得一头雾水。
“就、是、刚、才、那、幅、画!”宁月昭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道。
蒋年这才恍然,随即笑道:“那画怎么了?陛下夸我画得好呢!”
不提女皇还好,一提宁月昭更火大,她怒道:“你那什么破画,把我画成那个样子!”
“那个什么样子?”蒋年故作疑惑地打量了一下她,了然道,“不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吗?”
七分俏丽,三分娇蛮。头顶皇太女的光环,让很多人忘了她其实只是个十六岁的少女而已。
不管怎么样,她面对着他时,总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针锋相对的模样了。
宁月昭气结,索性不再搭理他,感觉越和他计较,越接近那画作中的娇蛮形象。
“生气了?”见她低头走路不语,蒋年凑近她问道。
“没有。”宁月昭连个余光都没给他,直接大步前行,上了自己的步辇。
看着伊人渐行渐远,蒋年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他想要得到她的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到自己的锦绣宫,饮了一口宫女奉上的菊花普洱茶,宁月昭才觉得自己胸口的那团郁气疏散了不少。
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前几日左明曾递给了她一本折子,但是那时女皇突然发病,她顾不上看就走开了。
于是,她来到书房。
那本折子还被扔在原处,若不是书房日日都有宫人打扫,只怕都要积上一层灰尘了。
翻阅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宁月昭将折子重重地拍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