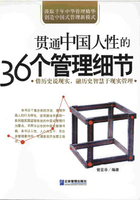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会怎样死去。虽然人从一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但对于年方二十五、风华正茂的我来说,死亡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现在,如果非要我对于死亡发表意见,那么我会说,如果能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我此生无憾。
是的,我才二十五岁,正处于美好的青春年华。今天,我将和我的爱人,苏伟平,正式登记结为合法夫妻。
他是普通的电子工程师,我是普通的实习医师。我们目前正为筑起爱的小巢而打拼着。在房价高企的年代,要想拥有自己的房产,必须要有坚韧的毅力努力存钱。
我是很现实的人,钱多就多花,钱少就省着花。所以,即使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仍然舍不得坐出租车,随着上班的人群挤上了塞得满满当当的公交车。
赶着上班的人前仆后继的用尽吃奶的力气往里挤,我一不小心,差点摔倒。苏伟平及时扶住了我。
他满脸愧疚:“兰芝,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你嫁给我,我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不能买给你,还要挤公车受罪。”
我把头靠在他的胸膛,宽厚的,温暖的胸膛。听着他规律有力的心跳声,我抬起左手,衣袖滑下,露出手臂光洁的肌肤,与肌肤争相辉映的,是一只古朴的玉镯,闪着柔和的洁白的光泽。透过光线,隐约能看到里面几丝血红,构成一朵怒放的幽兰,惟妙惟肖。
我笑了:“我不觉得委屈,有你,够了。再说,你已经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这只玉镯,像是我命中注定的属于我的东西,你看,它好像比原来小了一圈,紧紧的套着我了。这个尺寸,我看我这辈子是不能再把它拿下来了。”
苏伟平握住我的手,拇指来回摩擦着玉镯,宠溺的看着我,说道:“玉这种东西,讲究的是个缘分。我那天在天桥上一眼看到它,就觉得它是属于你的。就想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我朝苏伟平挤眉弄眼,心中充满甜蜜。
看我心情大好,苏伟平趁机提出要求:“兰芝,我想,我们结婚后,还是把我妈……”我知道,他是想说把他妈接过来一起住。看我脸色不善,最后的几个字,他终究没有说出来。
我的心寸寸下沉,我的眉头紧紧皱起。我没回答,只是默默的把手抽了回来。
这个问题,我不想再作讨论,尤其是在拥挤的公车上,去登记结婚的路上。
在我答应他的求婚的时候,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自古婆媳关系就是一大难题,我没有信心跟苏伟平生活态度太过严谨的老妈和平相处,也不愿意苏伟平有当夹心饼干的可能性,更不希望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不需要礼金,不需要出钱给我买房,不需要高档的首饰和名贵的衣物。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结婚后必须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从小到大,我看着妈妈被奶奶呼来喝去的使唤,看着奶奶一不顺心就拿我妈妈出气,我对婆媳生活在一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我爸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却不是个好丈夫。每当妈妈受气的时候,他从不啃声。只有我敢跟奶奶顶嘴,为妈妈讨公道。
我很不屑我爸爸的为人,另一方面,对妈妈也是恨铁不成钢。每次妈妈被奶奶欺负、爸爸视而不见的时候,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如果我是你,我就把那个窝囊的男人一脚踢到九霄云外去,自己的媳妇也保护不了,算是男人吗?”
妈妈每次都用微笑来回答,并不反驳,可我看得出,她的笑很无奈。她太爱爸爸,爱到愿意为了爸爸受尽委屈。
我和我妈不一样。我的爱情里,揉不得一点沙子。委曲求全换来的爱,我不稀罕。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不孝顺,我有我自己的孝顺方式,我只是尽可能避免发生婆媳冲突的可能性。
苏伟平面露愧色,他知道,他答应过我的事情,不该再提及。他是个一诺千金的人,但为了他妈妈,他今天第一次表现了后悔。但显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准备遵守他的承诺,不会再要求我们婆媳同住。
我们不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摇摇晃晃的过了一站,幸运的是,我面前的位置——靠车前门横排着的——竟然空了出来,苏伟平扶着我坐了下来,他则站在我面前,趁机再次握着我的手。
人潮再一次涌动起来。上车的,下车的,拥挤不堪。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不堪重压,失去重心,向我倒了过来,趴在我腿上。她忙不迭的道歉,挣扎着站直,去抓住上面的扶手。
我朝小姑娘一笑,伸手扶了她一把,她站直之后,也冲我点头微笑。
一个老头挤上车来,他斜吊的三角眼往车内扫视了一圈,便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朝我这边挤过来,让人觉得他随时都要倒下。
我虽不是无私的人,但也有点小善良。我站起来,把还没有坐热的椅子,让给了他。
岂料我还未完全站直身子让出座位,老头一改之前的老态龙钟,飞快的扑向座位,好像生怕别人抢了去。我被他撞得直往前跌,幸好苏伟平握着我的手,他眼疾手快扶住了我。老头却像没事人一样,惬意的坐在椅子上,双腿大咧咧的分开,霸占两旁别人的地盘,活脱脱一副老流氓的模样。
此时,车门刚好关闭,公车缓缓向前开去。
苏伟平眉毛一横就要爆发,我拉了拉他,摇摇头。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人而生气。
我们打算息事宁人,旁边跟我点头微笑过的小姑娘却看不过去了。她瞪大眼睛,大声说:“你抢什么啊抢,人家看你是老人家专门把座位让给你,你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还差点把人家推倒,还一点歉意都没有,真是为老不尊!”
周围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的人也纷纷附和,谴责老头行为不端。
“我X妈的,老子要你丫的多管闲事,¥&@……”老头张口就骂,脏话连篇,唾液横飞。小姑娘张了张口,但太恶俗的脏话她实在是说不来。她怎是老流氓的敌手,三言两语,已经被气得脸蛋通红,连连跺脚。
我感觉到苏伟平的异动,使劲拉住他,对他摇头使眼色。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会把老流氓从位上拉起来,揍得他满脸桃花开。痛快是痛快了,但接下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敢肯定如果苏伟平这么干了,这个老流氓会赖上我们。
苏伟平看懂了我的眼色,攥紧的拳头松开了。我对他坏坏一笑,从挎包里掏出一支银针。我学的是中医,除了把脉开药方,我还学习了针灸。大概是职业病,我的挎包里除了化妆品,还有银针。
老流氓仍然在唾液横飞的问候别人的全家,周围的人虽然气愤却也无人为小姑娘出头。
车上的人是那么的多,谁也没有发现我的手上多了一枚小小的银针。这枚小小的银针,不经意间,悄悄的刺入了老流氓的腿某处穴道。
老流氓痛得跳了起来,屁股离开了座位,他气势汹汹的吼道:“谁扎我?他妈的,¥*@……”又是一串不堪入耳的脏话,斜吊的三角眼四顾寻找凶手,唾沫飞溅到我脸上,我一阵恶心。
我非常的生气了。
我趁他转身到另一边继续骂人家娘的时候,一针扎到他腰间。他浑身一软,站不住脚,一声惊呼就向前扑倒。站他前面的正是那个打抱不平的小姑娘。她见到老流氓扑了过去,也是一声惊呼,下意识的拼命往后靠,想要躲过老流氓倒下的身体。
任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一场由让座引发的血案,发生了。
车上本来人挤人,每个人的身体都靠一只手在勉强掌握着平衡。小姑娘像后一靠,她身后的人平衡被打破,惊呼连连,一个接一个的朝同一个方向倾斜倒下。不妙的是,人群倾斜的方向,是汽车前车门,那里有一个后视镜。就在此时,另一辆公车从右后方加速横冲直撞了过来,想插到前面去。
司机大呼:“别挡着后视镜,我看不见了!”
刺耳的刮碰声,惊呆了所有人。两辆公车刮上了。车身剧烈震动起来,所有人放声尖叫。苏伟平一手紧紧抱着我,另一只手抓紧了扶手。司机大概是新手,被吓懵了,他没有踩刹车停下来,反而心慌意乱的加大油门,把方向盘往左一扭,下意识想避开右边的公车。
他太慌乱,以至于没有看到,左后方,一辆小车正在加速前行。
道路左边,地铁工程正在施工。
电光石火间,一切尘埃落定。
公车撞飞了左后方来的小车,一头插入到施工工地里。工地上有几条横放着的裸露的钢筋,瞬间刺穿了公车窗玻璃,刺过好几个人——包括可爱的小姑娘和可恨的老流氓——刺过苏伟平的胃部,刺进我的胸膛。飞溅的玻璃渣子,划破许多人的肌肤。跌倒的,撞破头的,不在少数。车内顿时哭喊四起,血流成河。
我没有觉得痛。苏伟平的鲜血顺着钢筋流到我的身体里,温温热热的,很舒服。我听不到刺耳的刹车声,听不到人们的尖叫声,听不到伤者的哭喊声。此刻我竟然觉得周围好安静,安静到我听得到鲜血飙出的吱吱声。
我安静的看着苏伟平,苏伟平悲伤的看着我。他仍然紧紧的抱着我,我说不出话,只好用尽力气抬手抚摸他的脸。
“兰……芝……,下辈子……我还要……”苏伟平没有说完,眼睛就闭上了。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说下辈子,还要和我做夫妻。
我竟然笑了。
都说人快死的时候会把一生的足迹回放。我却没有想起我的过往,甚至没有想起我的家人和朋友。
不知为何,我跟我表妹每人手提一串蚱蜢在田间疯跑的场景却忽然浮现在眼前。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在外婆乡下度过的一个美好周末。那年初夏的五月,天空湛蓝,风暖花香,草长莺飞。好美。
看着刺过我胸膛的钢筋,看着被钢筋刺过的一串身体,我突然觉得我们就像那串垂死挣扎的蚂蚱。这是否就是因果循环?
我从未想过我会像蚂蚱一般跟别人串成一串儿血肉模糊的死去。
但能跟心爱的人死在一起,我此生无憾。
我的视线模糊了,神智也开始不清醒。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记忆,是我手上的玉镯,突然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