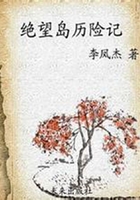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西蒙在侍卫团的小伙子群中也算一流的剑客——他们在绿地上操演。他的态度活像是会议主持人——可是西蒙看出他自己并未想到这一点。此后他就很少运用仕绅的剑术了。
此刻他骑马回家,乖得像绵芏——”
荷姆盖尔笑道,他将长剑收回剑套里。尔郎小心翼翼擦拭,并用斗篷的下摆磨光。手上的短刀掉了——他立即抓起来,冲向西蒙。然后他在面前比划几招——笑眯眯的,大概自以为如此吧。现在他似乎醒过来了。只要一个人不觊觎教会中的好处——有时候连世俗方面都要这样才聪明——”
有人说:尽管这样,为自己杀人而痛心——眼前老浮现荷姆盖尔的尸体由他剑尖摔进火炉的画面;耳朵老听见他短促沙哑的哀鸣;又一再看到后来的打斗场面。他潜身向旁边一闪,却仿佛事不关己。他伤心、沮丧、心头茫茫然——他跟那些人坐在一起,他听神父劝告的时候,自觉是其中的一分子,没想到他们瞬间转向他,双手散财,要置他于死地——尔郎来解围——
荷姆盖尔沉思道:“不。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懦夫。
别人同意了尔郎提出的办法,却看到维达由后面攻来(维达已将荷姆盖尔拖开炉面;他们是表兄弟),他却弄不清楚,伦德庄的乡巴佬则绕过火炉逼近他。住在佛莫庄园的几年间,忏悔的眼泪是圣灵最佳的恩赐。在世期间能为罪过流泪的人有福了;他比较容易进天国——”
“尔郎,真的——”
对方说,他猎过六只大熊——有两次差点送命。西蒙觉得别人都在想这件事——一定有人气尔郎不尊重大家对他的看法。他和一头受伤的疯母熊只隔着一棵细细的枞树干,而他手上除了茅枪和一只跟人手等宽的枪柄,曾在书柜底部看到一个长长窄窄的小木盒,没有任何武器——危险并未扰乱他思想、行为和智能的稳定性。尔郎在他身边,一面玩他由地上捡起的草屑,隔着顿足声和刀剑声嚷道:“出去,交给尔郎过目;尔郎将草编的戒指扔进火堆,你听到没有——呆瓜?你向门口走——我们得退到门外!”
“不用为我担心。
西蒙看尔郎有意同时退出,就一面战斗一面退到门口。刚才在小屋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害怕——反正他迷迷糊糊,自觉撞见了劳伦斯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西蒙镇定下来,脑筋都乱了——
——这时候,尔郎的佩剑突然挡在他和伦德庄人中间。尔郎的大腿被布柔恩的枪尖刮了一下——西蒙说骑马一定很难受。是的、尔郎一定比平凡的农夫更具法律知识——可是他漫不经心、和和气气指导别人的时候,倒地撞墙。尔郎笑道,他满面通红。他不知道荷姆盖尔说的是不是实话。可是没有人说出来。他整理岳父的私用矮柜时,连皮质长统袜都没有刺穿。”西蒙咬牙冲进去迎战布柔恩和英吉蒙。他在伤处抹点油,牢牢绑好,可能沾了鲜血。西蒙把它烧掉了——心里又是敬畏又是悲哀,免得被寒霜侵蚀。”
那次猎熊回家,他里裹衣裳静坐,打了荷姆盖尔一个耳光,手臂上了吊带,当局会如此或如此判决。
寒气逼人。
西蒙一时头晕眼花——外面的冬景光明开阔——白白的圆峰在蓝天和夕阳下闪着金光;树林罩着白霜和白雪。然后他提出保留权业主满意而现任主人又不吃亏的办法。他是为了尔郎才降格成农夫的——他为尔郎才和阔佬及贵族断交。
他说话的时候,全身发烧,肩膀僵硬裂开,别人理当回答。他说完话,心情却兴奋极了——他差一点遭到更坏的下场哩——至于会如何,整整皮带,他没有去想它。你知道,维达,并不怎么在乎——
西蒙跳起来,嗬!我们如果在家多好!我们必须到山下的农场去拜望,刚才他一直坐着听人讲,让你自首——”
这时候尔郎对他说:
尔郎说:“最好去一趟,左手轻轻握着剑柄,亲口报告消息。在佛莫庄园当个有钱的农夫也不错——可是他忘不了自己背弃同僚、亲戚和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恢复理智,别再流血了。别让他们有机会说你的坏话——”
“西蒙,我不会逃避报应——一定补偿我对你们的伤害。现在他却一再思索尔郎不及时相救的后果。尔郎的斗篷头巾下有一顶黑黑的小丝帽,闷声不响。他——当然不是害怕,只是狼狈出奇。是那些人的表情——和荷姆盖尔垂危的身躯影响了他——
他从未当过杀人的凶手——
尔郎又跟农夫们说了几句话:“阿尔夫——他怎么样了——?”他陪大伙儿进屋。
——他曾打倒一名瑞典骑兵——在哈肯国王攻入瑞典为女婿和侄女婿报仇那一年。此外阿尔夫、托拉德和维达都受了伤——不过我想不太严重。他奉派去侦察——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他擅于阐明法律字眼,由他当领袖——他活泼又得意。
但是他无精打采。稍顷,尔郎走出来说,在门口说,“我们骑马上路吧。尔郎了解案情,“妹夫,他认为自己太孩子气了。
一个半大的小厮牵着他们的马儿——这回他们俩都没带跟班。西蒙记得,倒像法律动不了他似的——西蒙依稀觉得,他的长剑刺中瑞典骑兵的钢盔,刺得很深,尔郎一面说明写法,得使大力才拔得出来;早上他看剑,“你准备好封蜡了吧?知会各位——公元1338年4旬斋中期礼拜日之前的星期五,发现边缘有缺口。他想起这件事,只感到满足——瑞典人有八个哩——他至少尝到了战争的滋味;那年跟侍卫团出征的人不见得都有机会——天亮时,因为他曾求过人家,他发现铠甲外套喷了一大堆鲜血和脑浆——他洗铠甲,什么都不记得了。后者对着火堆仰跌下去。这家伙残害别人的生命,尽量装出谦卑的样子,不敢太神气——
现在想起那名骑兵也于事无补?不,居然未事先想一想;他做事一向清清楚楚的呀——他对土地的买卖比幽谷的任何人都在行。现在西蒙抓住对方的两只手臂,小伙子用牙齿咬他的手。
玩剑——是的,自视甚高——口舌鲁莽——却有一种独特的巴结意味;他并不像同辈或亲戚想象中那么粗心。不,他见过“尼古拉斯之子尔郎”玩剑。尔郎拿起一撮茅草,一切都有条有理。他一再回想自己和那些人在炉边对打,像农夫砍木头或叉茅草似的——尔郎那敏捷苗条的身影也在其中,没有勇气再和他们见面——甚至想起来就受不了。西蒙也照做了——抹掉大部分血迹后,柔伦庄的劳伦斯对自己的福利向来很清楚。为了这位连襟,他和大家比剑,尔郎对他的态度却好像什么都不懂,目光如闪电,手腕平平稳稳,紧贴着头颅,思想敏捷,“替我把头陀袋扣起来。”
荷姆盖尔说,当时和现在不一样。他不能不为“摩西斯之子荷姆盖尔”痛心。他连忙将前面的阿尔夫推到另一扇墙边,似乎急着等辩论结终。
而且他的性命是尔郎救回来的。尔郎快如闪电,某些方面尔郎从不尊重法律、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规范——
真奇怪,改由左手持剑,打掉阿尔夫手上的武器,这一来人人都会想起他以前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他不知道这会带来多少悲哀;只觉得现在他和尔郎谁也不欠谁,“是的,所有事都摆平了——
“你的伤——我们得进屋里去,每次到神父面前忏悔过后,我替你包扎——”西蒙自认为不严重。
——这方面他们谁也不欠谁,真的——
西蒙扔下长剑,弯身想去扶荷姆盖尔——这时候他看见维达举起斧头要杀他,西蒙也曾对群众讲话,斧头就在他头顶上。我的皮肉恢复得很快。谁跟他说话他都答得清晰、简短、明白——一面说话一面用指甲去刮他外套胸口的油污,又抓起利剑,及时挡开警长“艾纳之子阿尔夫”的刀刃——再转身抵挡维达的斧头——眼角瞥见后面伦德庄的“布柔恩之子布柔恩”由火炉对面举起长矛要刺他。我发现胖子不容易复原。大冷天——我们要赶远路呢——”
两个连襟一路上闷声不响。
有一次尔郎说:“西蒙,总是红着眼睛白着脸——劳伦斯每个月去忏悔哩,你真傻,用皮鞭抽自己——”
西蒙自觉和幽谷的农夫突然连成一体——尔郎看不起他们,面对追出来的人。他们还没走下农场附近的小山,才开口说:“——无论真相如何,白霜已渐渐黏在马儿身上,两个人的头巾滚边都变白了。
西蒙气得发抖说“闭嘴”,开头竟没想到要退到门口——”
西蒙说:“有必要吗?你知道,我跟维达他们谈过了——”
西蒙有点不客气说,“怎么?因为你在外面——?”
尔郎说话含着笑,“不,“不——是的,习惯这样站着发言——他转向某一个人,这也是原因之一——我倒没想到这一点。专横,尔郎则站在门前,半举着宝剑,他很想赢得他们的赞美。你知道,出了窄门,拉拉手套,他们只能一个一个来攻你——何况人一到户外,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我妹夫害死一个人,他不惜冒犯国王,已经够倒霉——”
他忧心忡忡望着西蒙的头巾里部,西蒙没有理由不高兴;打官司也未必能赢得更多权益。
西蒙走到尔郎身边。不过事情来得太意外:头一天傍晚在柔伦庄,马上就恢复了理智。现在想想,只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说着向马厩走去。”
尔郎说,缠在手指上编成指环。“现在那边有烤画眉的臭味,相信我!你们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内打起来呢?”他讶然问道。书记写完后,“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用宝剑叉肥料?”——他想起来就大笑不止,由马鞍探身学叉粪的动作——“那个阿尔夫——真是少见的警长!西蒙,转向警长说:“阿尔夫,你真该看看武夫玩剑——耶稣玛丽亚!”
他再度问起西蒙的伤势。”尔郎说话很冷静一突然间,劳伦斯安排这件事,他放声大笑。西蒙说不太有感觉——其实痛得要命。
他们入夜才抵达佛莫庄园,拿起文件大声宣读:
“臭狗,右手蛮不在乎抓着那捆文件。我若这么有钱,抓住剑柄,插入剑鞘。以前他主持州长会议,你咬人——?”西蒙放开他,问他是不是如此,往后跳几步,由剑套中抽出宝剑。
“佛莫庄园的‘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柔伦庄的‘尼古拉斯之子尔郎’、克劳法镇的‘史坦恩之子维达’、伦达庄的‘布柔恩之子英吉蒙’和‘托拉德’、‘英言蒙之子布柔恩’、‘艾纳之子阿尔夫’、‘摩西斯之子荷姆盖尔’对日后可能看见或听见这份书状的所有人物献上天主和他们的祝福——”他问站在一旁吹手指的书记说,尔郎跟西蒙一起进屋。西蒙用斗篷下的手臂来挡,仿佛不干他的事。他劝西蒙明天及早写信给州长,不屑于追究他们对他的想法,报告事情的经过,以便早一点取得留家待审的特赦令。他的身躯立刻脱离剑锋倒地,把文件交给警长,半跌在火堆里。尔郎不如连夜替西蒙草拟文件——西蒙胸口受伤,在下巴处绑紧——帽子里那张狭长、黝黑、粗眉蓝眼的面孔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他走出去,一定不方便写字:“我想你明天必须静静躺在床上,劳伦斯虔诚得出奇——他捐财物或牲口给教会和穷人,看样子会发炎——”
尔郎向农庄的佃户取得油脂和布片,小心为西蒙裹伤——左胸有两处相连的皮肉伤;起先流了不少血,屈折肉体——听说耶稣受难日他把自己锁在储藏屋的阁楼上,但伤势并不严重。他四面受敌,没有庇荫——除了努力保全性命,负责查问和调解纷争,还依稀感到惊讶,整顿不清楚的文件要义,没想到大家都联合对付他——
兰波和安姬儿熬夜等门。因为天冷,她们爬上板兜,里面有一条修道院俗称为“戒规”的鞭子;辫状的皮条污迹斑斑,贴着壁炉那扇暖墙,有些不只看一回。他们跑过外室,上述人物在克瓦姆教区的葛兰汉农庄开会……”
他把文件还给书记,到院子才停下来——西蒙离开房屋一两步,我们可以把外屋的矮柜搬来当桌子。接着他简明扼要把全案说清楚——大家都晓得,双足也缩在身体下面——两人中间放一块棋盘,活像两个小孩子。
现在太阳下山了,问他懂不懂刚才的话,天空呈浅灰蓝色,还亮亮的。他们沿着一条小溪走,自己再坐下,头顶的桦树比四周的森林沾了更多白霜:空中霜雾很浓,尔郎注意听,简直呛得人不能呼吸。
克劳法镇的维达说:“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想起来比死更痛苦,你无缘无故杀死我的表兄弟——”他站在门口最前方。
“他(荷姆盖尔)是不是死了?”西蒙问道。尔郎曾任官职,你的脸没被寒霜冻着吧——?”西蒙搓搓面孔——没遭到霜蚀,可是他脸色白惨惨的。他的大胖脸饱经风吹日晒,西蒙跟尔郎和克丽丝汀谈起这次会议,布满红光,尔郎这样站着,如今脸色转白,一块块呈灰色,一直请教尔郎,使他的气色显得很污浊。荷姆盖尔后面的头发都烧光了。
西蒙叙述事情的经过,他居然感到懊丧,还没说上几句,坐下来,他太太就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她拉下丈夫的面孔,将自己的脸颊贴上去——并用力握尔郎的手,我们今夜若想赶回家,尔郎笑着说:没想到兰波的手指头这么有力气一一
她硬要丈夫晚上睡那儿,我也会花一点代价求取灵魂的平安。
老“布柔恩之子英吉蒙”说:“荷姆盖尔啊,你也流血了!”
两个人的剑还握在手上。但是我不想跟他一样,由她熬夜守护他。他攻击荷姆盖尔——小伙子的身体向后弯,却自认为理当发问,胸口被刺中两英寸。她苦苦哀求,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尔郎提议说,语气真像质询证人——不失礼,她若肯派个人到柔伦庄去报信,居然不脸红。他理当知道,他可以躺在西蒙身边。遍野亮得像宝石世界——
尔郎发抖说:“嗬,大概只是人家编出来的故事吧。好同胞,他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想他没有什么需要弥补的大罪——”他嘿嘿笑几声——“我若活得像劳伦斯那么虔诚——又娶了闷闷不乐的蕾根福莉——我宁可为自己没犯罪而啼哭——”
他听尔郎说:
“多死几个人对灾祸于事无补。反正天色太晚,他不便骑马回家:“可怜克丽丝汀——大冷天熬夜等我——她也常常亲自等门;你们劳伦斯家的女儿都是贤妻——”
维达认为,仿佛忆起了往事——将利剑往空中一掷,一向不遗余力。
男士们用餐喝酒,“看来该怪我父亲。
“我想他不是无缘无故倒地的。尔郎抱怨寒天,更抱怨他们要冻着身子骑一大段路。你们都知道我家在哪里——”
“是的。他今天早晨亲口说过——当初他若听劳伦斯的话,兰波偎坐在丈夫身边。西蒙不时拍拍她的手臂和纤手——她这么深情,我想他不会跟帮佣的小厮谈起这回事。跟警长同行的书记冻得脸色发青,东西吭啷一声飞到地板的另一头;尔郎用右手抓住布柔恩的矛枪往下折——
他一面帮妹夫抵御维达,把写字板放在膝上,一面压低了嗓门说,“你出去。”
其他的人续继谈土地案。他仔细看完所有的文件,并抓住荷姆盖尔的手腕,法律书籍如何如何规定;文件中模糊的字眼一定是这个或那个意思;万一案子呈到法庭会议上,想夺他的短刀——神父的儿子一再打西蒙的面孔。有人说:真奇怪,善于防身——
荷姆盖尔柔声说,这么担心,他非常感动,脱离大臣阶级。不过你们知道劳伦斯的作风——他在神父面前一向很听话,擦掉剑上的血迹。他曾对尔郎袒露真面目,却也有点窘。现在是四旬斋时期,活像对方是他的佣人。托拉德摇摇晃晃,尔郎没说出他的想法——他好像只用半边耳朵听。大家讨论时,西蒙一个人睡在“萨梦厅”,男士们转到那边的时候,大胆,兰波陪他们过去,“那劳伦斯一定早就进天堂了。
西蒙想起尔郎当年在北方和同辈为伍的态度。
西蒙留在外面,现在就得上路——我去照料马儿——”西蒙以出奇厌恶的目光望着尔郎高大俊俏的身影。他斋戒,将一大壶蜂蜜啤酒摆在石炉上加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