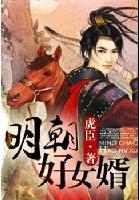谢青一走过木桥,马上被秋媚身边的人引上汽车。汽车飞驶而去。秋媚让谢青安静,什么也不要说。谢青听到秋媚和那几个人说的是意大利话,凭他的感觉,那几个人是真正的意大利人,而不是会说意大利话的阿尔巴尼亚人。
不久后,车子进入了一个不很大的院子。谢青下了车,认出这里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私人医院。谢青马上被两个戴着白帽的女护士领进了护理室。她们给他量过血压测过体温之后,用剪刀剪开了他身上的脏衣服,用热水毛巾擦拭他的身体,然后给他被绳子捆伤的手腕做了消毒和包扎。做好了这一切,他被领到了一间单人病房,在一张铺着雪白的床单的病床上躺下来。护士给他挂上了盐水输液,然后给他端来一份热乎乎的流质食物。这个时候,秋媚走进了病房。
“让你受苦了。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秋媚坐在他床前,说。
“没有你来救我,我大概死定了。我想不到你会亲自过来。”谢青说。
“我应该来的。自从让你到阿尔巴尼亚之后,我心里一直有点不踏实,觉得不应该让你走这条道。想不到真出事了。”秋媚说。
“绑架我的是些什么人?”谢青问。
“是些本地的马匪。我已经让这里的意大利人把事情摆平了。以后意大利人会保护我们。”
“你一定花了很多钱。”
“钱花多少没关系,只要人平安。你现在身体怎么样?身上是不是有伤?要是你不想继续呆在这里,今天就可以跟我一起离开,回法国去。”秋媚说。
“不,我要留下来。我只是手腕被捆伤了,其他没事。过几天就会好的。”谢青说。
“你这么说,我放心了。那你在这里多住几天,养好身体。我不能在这里久留,今天就会飞到苏黎世,再转巴黎。我走了之后,你手下那班人会来看你的。”
“你放心走吧,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做好的。多谢你来救我一命啊!”谢青说。秋媚摸摸他的头,对他微笑,然后站了起来,退出了病房。谢青听到她的皮鞋声快速响过了走廊,消失了。
崔作高和郭林飞很快就来到了医院。他们对他是怎么获救,怎么住在这个医院里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半小时前接到一个意大利人打来的电话,说谢青在意大利医院,让他们去见他。谢青明白秋媚独身而来,依靠意大利人摆平了事情,没走漏一点风声。他这回才知道她真是个有本事的人。谢青问他们客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没出现问题。自从他被绑架之后,他们集中了力量保护客人。意大利方面的接头人让他们等待,营救谢青的事情他们正在进行。现在他们看见谢青平安地出来了,其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
谢青在医院呆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到了自己人的中间。他第一件事是到客人的居住点去看一看。客人们在他被绑架之后,受尽了惊吓。不管怎么样,在偷渡的路途中,他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看到他回来,他们都开心地笑了。
“老板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意大利啊?”一个女客人问谢青。她的名字叫叶三华,那次在克米纳德厂区和“北京李”的战斗中,她主动要求参战,帮助压子弹。她是个青田人,老公已在西班牙,弟弟在荷兰。
“快了吧,我们总会找到办法的。”谢青说。他看到好几个女客人围了过来。这些女孩子看起来气色还不坏,毕竟年轻,能抗得起愁滋味。她们正做好饭,是水煮的意大利通心面条,里面放了一些青菜和肉丝。她们问谢青要不要吃?发罗拉没有中餐馆,谢青最近又饿了这么久,看到了带汤的面条,胃口大开,不客气地坐下来吃起来。吃了还想要,发现已经没有了。于是他说了一个当兵时的故事给她们听:有一次一群师部女兵组成的业余文工团到连队去慰问演出。连队正好开饭,女兵就坐下一起吃,结果饭不够了。司务长对着大家用山东话解释说:同志们,本来今天的饭是“狗”(够)吃的,可是突然来了一群女兵,就“母狗”(没够)吃了!
女客人都笑得弯下了腰。自从踏上了偷渡的路,大概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一次。
叶三华说:“老板呀,等我们到了意大利,一定请你好好吃顿饭,很‘狗吃很狗吃’的。”
“到了意大利,你们都陪老公去了,哪里还想得起我呢?”谢青说。
“老公我倒无所谓,我就是想我儿子。他在青田家里,听说每天都哭着要妈妈,饭都不吃。”叶三华抹起了眼泪。
不知怎么的,谢青也觉得心里一动,想起了在海边寄养的杨虹孩子。
倒霉的事情总会结伴而来。无奈的等待还遥遥无期时,风季又提前来了。风季的时候,海上会有暴风雨,会起巨浪。这个时候发罗拉几十公里的海滩上,见不到船只的踪影,只有海边的橄榄树林在暴风雨中摇晃咆哮。谢青非常关注海上的天气,整天看着电视的气象节目,他听不懂那个气象主持人在说什么,只是看到电视气象图上风暴像漩涡一样盘旋着。
这天的下午,海上风暴越加厉害。可是法托茨在当地的代理人送来了一个消息,说今天夜里有一条大船要出动,让谢青安排一百来个客人过去。谢青说这样的天怎么可开船?法托茨的人说气候是险恶,不过由于坏天气,意大利的海军发现这几天没偷渡者过来,取消了海上巡逻,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平常这里走的都是一些只能坐二十来人的快艇,速度很快,可抗不了风浪。今晚走的是一条能载几百人的铁壳货船,抗风浪能力较强,船长很有恶劣天气航海的经验。他告诉谢青,错过了这只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新的机会。所以,他必须马上做出决定。
情况摆在他的面前:要么冒着海上风暴过去,要么无休止地等待。谢青让崔作高听听客人的想法,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冒险过去。路上的艰辛和恐惧已让他们对危险麻木了,只想早点渡过海去。谢青不再犹豫,拿出了客人的名单。总人数还有两百来人,分为十来个组,今晚得过去一半。谢青不加思索地拿起笔隔着一个小组就打个圈,打圈的组要先过去。不过他的笔在叶三华那个组上停了一下,他把它跳了过去,让下一组先走。白天一起吃饭让他对这些女孩有了点印象,他有点不忍让她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开船时间是在深夜,但是从下午开始各个居住点已是一片混乱。谢青要求所有人吃饱饭,喝足水。然后把所有的私人用品全留下来。尤其是各种证件,不管是真正的还是伪造的都绝对不能带在身边,因为他们要随时做好被意大利边防警察扣留的准备。如果有证件在身边,警方就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遣送他们回中国。每个人只能穿最简单的衣服,不能穿高跟鞋,因为随时要准备逃跑。要记住万一被抓住了,要装作什么也听不懂,绝对不要开口说话,就算警方派来中文翻译也不能和他说话,这样他们的国籍才不能被确定,当局无法遣送他们回国。谢青对即将过海的人员作了反复交代,让他们把身上重要的东西交出来集中。这些人尽管在路上走了那么久,身上还是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谢青让人做了登记,说好以后会带到意大利还给他们。这个时候的场景很有点像二战时期的犹太人集中营。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带到毒气室之前,好像也都有一套繁琐的手续,而且那些人也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死亡。好不容易把出发人员的准备工作做好了,谢青驱车去码头。码头在一个废弃的修船厂里边,离市区有几十公里。谢青的车在海边走时,狂风暴雨差点把车掀翻在路边。那条锈迹斑斑的铁壳货轮的船名让油漆抹掉了,靠在浮桥上摇摇晃晃。一队队的塞尔维亚人,库尔德人,伊朗人还有中国人手脚并用爬上一个铁梯子才上到船甲板,然后又钻进了货舱里。
谢青看着名单里所有的客人都上了船。跟随着偷渡的客人,有崔作高等五个带队的,他们分别要带五个组的客人在到达海岸后与接应人取得联系,把客人交给接应人。谢青和崔作高握手告别,这个武功高强长相如童安格的小白脸和他已有了深深的交情。
深夜一点光景,这条货轮解缆启航。看它倾斜的船体好像马上要倾覆到海里的样子,不过它很快调整了姿势,冲进了巨浪滔天的奥托兰多海峡,很快就被漆黑的夜色吞没了。
天亮之前,谢青接到秋媚那边来的好消息,说船已顺利到岸。人员上岸后各组分头疏散,除了崔作高带领的那个小组还没联系上,其他人都已和接应人会合。
崔作高在进入黑蒙蒙的货舱之后,有一种死神就在身边的恐怖感觉。货舱内空气稀薄,充满了柴油和人的呕吐物排泄物的气味,还有各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气味。舱内只有几根柱子,在船体大幅度摆动起伏的情况下,人们得抓住一个支撑点。所以人们就像生长在礁石的甲壳类动物似的,一个挨一个贴在舱壁和柱子上,摇来晃去,把呕吐物吐得满地都是。崔作高是个平衡能力超强的人,他没有晕船的感觉,但是对于这样摇晃的船还是害怕之极。不过他知道,渡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如果两个小时内船没有翻掉,他就不会死。在他的手表走了一个小时后,他知道,看来他不会死了。
又过了近半个小时,舱门被打开,一道手电筒的光照进来。一个水手用意大利话喊着:船快到了!上帝保佑!你们做好上岸的准备吧!随后,舱门又关上,但黑暗中的乘船者已经看到了生命的光明升起。对于一心想到西欧的偷渡者来说,新大陆的曙光出现了!
过不了多久,崔作高感觉到船撞到了一个硬物。很快舱门打开了,手电筒的光再次照进来。人们赶紧爬上楼梯,踩着上下起伏的跳板跳上了岸。他们踩到的地就是亚平宁平原,是真正的西欧的土地。但是这块大地现在是漆黑一片,风雨交加,看起来比落后的阿尔巴尼亚还要荒凉。几百个新移民就这么走进了黑暗之极的欧洲大地,去寻找自己的美好梦想。这个时候天空中有雷电,一道耀眼的闪电让他们看到了这是个没有房屋的荒野海滩。他们分散成各个小组,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比起刚才在海上的惊险,现在的黑暗算得了什么呢?
崔作高尽管是第二次踏上西欧的土地,还是觉得心里有一种来到新大陆的兴奋。他带的二十六个客人都平安无事地跟着他。由于眼下海上气象险恶,船主无法确定登陆的地点,所以接应的人只能等他们上岸打电话后才能过来。崔作高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要找到一部公用电话。他们开始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一条大路,借着不时闪现的雷电能看见周围的景物。但是不久后他们看到身边是一片树林,道路不见了。树林越来越密,树叶把闪电的光都遮住了。他们只能根据摸到树木的感觉知道还在树林里。他们想退回到刚才的大路上,可是已经迷失了方向。
这个时候的情形大概有点像高尔基那篇《丹柯》里所写的情形。一个叫丹柯的人想带众人走出黑暗,却迷失在森林里,结果被人咒骂。没有人敢咒骂崔作高,崔作高也不会像那个丹柯掏出心脏当火把照亮前进之路。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故事。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崔作高的确是把这群人从黑暗领向了光明。因为这些生在山沟里的人如果不出国,只能老死在山里,在中国的过度密集人群里,他们永远是劣势的族群。只有在亲友成群的西欧,他们才会有可能靠辛勤劳动加上东方人的狡猾和冒险精神成就一番事业。在浙闽一带光祖耀宗回国投资的华侨中,有大部分人当年就是这样偷渡出去的。
在泥泞的树林里一群人摸索了好久,还是找不到出路。好在这时天开始微微发亮了,他们走出了树林,看到远方有山的影子。前面是一片平原,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他们找到了一条铺着沥青的路,不过在暴风雨中天还是灰蒙蒙。这时远处出现了一座房子,窗内还亮着灯光,屋顶上的烟囱明显冒着白烟。这群刚走出树林的人停住了脚步,看着这个温暖的房子不知该怎么办。他们跟着崔作高慢慢走近了房子,突然一只体态庞大的牧羊犬钻出房子,极其凶狠地吠叫,随时要扑向他们。接着从屋里出来一个人,满脸的胡子,看起来很凶狠,朝人群大声嚷着,大概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崔作高在维也纳呆过几年,会说一些德语。在阿尔巴尼亚时也学了几句意大利语,这时都用上了。他说是他们要去莱切市,迷路了。问能否用一下电话。这个乡下的意大利牧羊人在海边住久了,大概知道了他们是些什么人。他没有答应崔作高让他用电话,但是把一个门打开了,放他们进了屋。这里是个库房,里边放着一捆捆干草,很干燥暖和。隔着一层板壁,是一个很大的羊圈,能听到羊群发出轻微的叫声。过了一会,这意大利人给他们端来了一大篮子面包,一大壶热咖啡,比划着让他们快吃。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看着崔作高。崔作高说:吃吧,吃饱了再说。
饥饿疲惫的人在饱食之后,反而会懒洋洋地不能动弹了,一个个靠在草堆上睡了过去。崔作高觉得这个牧羊人不让他用电话,又慷慨地送来面包咖啡有点不对劲。他贴着和牧羊人屋子连接的那扇门倾听,听到牧羊人在打电话。他知道牧羊人的电话一定是打给警察报信的。但这个时候想逃跑也已经太晚,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你还能跑多远呢?不过让崔作高决定不逃跑的主要原因还是,即使让意大利警察抓住了,后果并不会太坏。只要警察搞不定你的国籍你的身份,不会遣送你回国。通常是关押几天,最后发一张象征性的驱逐令放你走。
果然,不到十分钟门口就有警笛鸣响,好多辆警车把房子包围了。崔作高他们已经吃饱肚子,烘干了衣服,懒洋洋地跟着警察上了警车,呼啸着离去。好多人一上车就又迷迷糊糊睡去了。不久后他们被带下了车,崔作高看见了墙上的一个广告上电话号码的区号是832,正是意大利莱切市的区号。
他们被关押在警察局里,有吃有喝,还有烟抽。后来有人来问话,谁也听不懂,也不说话,都像木头一样。警察派来了说中文的翻译,他们还是装聋作哑。到了下午,警察给每个人照了像。照相印在一张纸上,上面还写了好多字,发给了本人。这个时候翻译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听得懂我的话。这张纸是驱逐你们离境的命令,也是你们的临时证件,有效期二十一天。你们必须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离开意大利。崔作高知道这个驱逐令没有一点约束力。过了二十一天你不离开意大利他们也拿你没办法。那个翻译还是很有点乡情,说:“你们现在可以走了,祝你们好运!”
出了警察局,崔作高把一群人带到了火车站,让他们坐在一起。他没有马上打电话给接头人,怕警察暗中监视。到了晚上九点,他觉得确实没有人跟踪,才打电话给接头人。接头人很快来了,那人按照约定戴着黑色的棒球帽,手持红色雨伞。崔作高对他说:“二十六个,一个没少,交给了你了。”说完,他就独自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