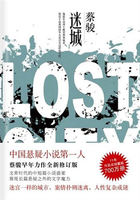一九八六年,杨虹在和谢青结婚的第二年,调入了《AC日报》当记者。她早几年业余读函授大专新闻写作专业,常给报社写一些小通讯小散文之类的东西。报社那时缺人,她很顺利进去了。杨虹从小爱看书,尤其是俄国苏联文学看得很多,有些文学底子,文章写得有特色,加之人们知道她父亲是原AC地区最高长官,因此在报社颇受器重。这年杨红才三十出头,身高一米七一,一头会甩动的齐肩短发,高高的鼻梁,坚毅的嘴唇,微陷的眼睛,和她父亲青年时十分相像。她喜欢穿一件米色的风衣,脖子上随便挂一条方格子围巾。她的父亲有一张在西湖边的旧照片就是这样的穿着,她觉得很有风度,仿照着穿起来。
但这些年来,她变得成熟沉默了,在性格方面,越来越像她的父亲。关于父亲,她其实知道的很少。他死的那年她才十来岁。而且,父亲死后的遗体她都没见到,骨灰最后也不知去向。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一个中午。刚下过一场大雨,小院子里花坞上鸡冠花红得象燃烧一样,好多平常见不到的大蜻蜓飞来歇在草叶上。父亲穿着风衣,提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公文包,对杨虹说要出差开会去。杨虹问爸爸去什么地方开会?爸爸说是去鼓山岛,三年前爸爸曾经带杨虹去鼓山海岛玩过,所以她能记得这个名字。爸爸走了很多天都没回来,后来有好多的人来家里翻箱倒柜搜查。这个时候,杨虹才知道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她经常会翻阅父亲留下的书籍,那都是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父亲本来还有很多的笔记,但在他自杀后被造反派全抄走了。父亲读过的书很多地方画着红杠。杨虹发现父亲对恩格斯的书更偏爱一些,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等著作的页边写着大量的心得。她还经常会去翻阅一大叠六十年代初的《红旗》杂志,那上面有父亲写的理论文章。但是她总是觉得很难看懂,因为她并没有看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著。
做记者要接触各种人。她有时要到不通公路的山区,有时要下矿山的巷道,比起那些骄生惯养的女孩,她更愿意往那些艰苦偏僻的地方跑。AC在八十年代经济已出名,很多中央领导都来视察,在前呼后拥的随从里,杨虹有时也会在其中,但她总是远远站在最外边的一圈。文艺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好多是来走穴的,什么姜昆啊,毛阿敏啊,郭兰英啊。每次有大腕来,报社领导总是让杨虹去采访。还有就是无数的会议,无数的应酬,每个晚上都会接到好几个饭局的邀请。生活看起来变得多姿多彩,工作也充满刺激和兴奋。但是,沉闷和窒息的感觉还是会时常出其不意地笼罩着杨虹。
她和谢青的婚姻,没多久就显示出是一个错误。刚结婚时,他们好像也火过一把。他们在南洋照相馆拍的结婚放大照片被陈列到橱窗里。那个时候,AC城里谁的照片要是被陈列到南洋照相馆的橱窗,就相当于现在上了名牌娱乐杂志封面一样轰动。然而到了第二年,两个人的性格、志向的差异开始凸现出来。杨虹和谢青激烈吵过几次,但她很快平静了下来。
她明白了谢青和她完全是两回事的人,她根本改变不了他,也不想改变他。于是她和谢青相安无事地呆了下去。结婚后她一直没怀孕。这不是她这个北方来的革命者后代和谢青这个土生土长的本地拉车人后代在DNA上有基因排斥而无法怀孕,而是她从一开始就偷偷在吃避孕药。她不想生孩子,不是她不喜欢孩子,而是有一种想保持纯正血统的心理。她无法想象和谢青生下来的孩子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她不喜欢这个孩子,还不如不把他生下来。但是她并没有很后悔和谢青结婚,某种意义上看,谢青算是一个不坏的人。尽管他很乏味,但比起那些装腔作势的官场上的势力狂,那些油光满面的暴发户,还是好接受得多。她越来越不喜欢夜郎自大的AC本地人了。她发现,AC人像井底之蛙,老是觉得AC这个地方是领导世界潮流的中心,到处在吹嘘什么AC模式AC现象。如果仔细地观察,AC人的土著特征还是很明显:低矮,猥琐,没有鼻梁,颧骨突出。尤其是AC人讲的普通话令她难以忍受。有一次,市机关开大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先后在会上作报告。两位领导都是本地干部,说的普通话AC方言口音都很重。报社的同事听了报告后闲说书记和市长的普通话谁的更难听?杨虹的嘴里蹦出了一句恶毒的话:屁和屎一样地臭。
有一天,杨虹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她闻名已久。她花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看完了这本398页的书的前167页,觉得里面的故事云山雾罩摸不到头绪。但是接下去看到的那篇叫《爱玛·聪茨》的小说她一下子就看明白了。故事说一个叫爱玛的女工的爸爸因被人诬陷而服药死亡。爱玛觉得必须为父亲复仇,而她也知道仇人是工厂主。她的复仇过程是这样的:先装成妓女在码头附近让一个水手在她身上尽情发泄,然后带着被搞脏的身体立即去见工厂主,说要向他告密。在工厂主为她倒水的时候,她从抽屉里拿出工厂主的手枪,把他打死了。她撕破了自己的裙子,把沙发弄乱,解开了死者的衣服扣子和裤带。然后打电话报警:“工厂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强奸了我。我把他杀了……”这个复仇故事看得她心跳加剧,因为它很像她自己多次进入过的一个梦境。
杨虹常常会想:父亲是被AC这个地方害死的,她和这个地方有杀父之仇。
八月份,AC市委市府开工作会议,各县和直属机构的三套班子人员都要集中参加。报社派杨虹参加会议做新闻报道。会议开了五天。最后一天,会务组的人通知杨虹,说鼓山县的人大李闪梅副主任想和她见个面。杨虹给李闪梅副主任的房间打了电话,说好了中午见面。杨虹知道她是全国有名的见过毛主席的女子民兵连连长。她年轻时那样风光,现在也已是皱纹满面五十多岁的人了。当杨虹走进她的房间,看到她的眼睛发出了光辉。
“你还认识我吗?杨记者。”她说。
“当然认识。我虽没采访过你,可经常看见你坐在主席台上。也常在媒体上看到你的消息。”杨虹说。
“不,我不是说这些。我是说以前,你还不到十岁时,你爸爸有一次带你到海岛开会。是我摇着船带你们去小岛上玩的。”
“你认识我爸爸?”杨虹有点惊讶,看着对方。她努力去想这件事,可脑子里一下子还是一片空白。“你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呢?”
“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他们不说罢了。”李副主任端详着她,好像要找出一点过去的印象。
“你爸爸是个好领导,他那时经常来海岛调查指导工作。鼓山岛是国防前线,生活很艰苦,他对我们女子民兵连特别关心。他虽然是领导,但他也写文章。是他最早写文章给《解放军报》报道女子民兵连的,然后才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起派记者来把女子民兵连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让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李闪梅还说,如果没有三十年前杨苏林那篇报道,女子民兵连说不定早已自生自灭被人忘记了。
杨虹认真地听着,她没有听一个人说过对父亲这样深情的话。她还注意到,李副主任说的普通话里没有AC的口音,却有福建话的成分。不久后,她明白了鼓山岛行政上属AC地区,说的却是闽南话,那里的人都是福建渔民的后代。她对于最初报导女子民兵连事迹的是他父亲感到有点惊讶。
“我父亲是怎么发现你们的?”杨虹开始对这件事有了好奇心。
“这事说来话长啦。你知道,鼓山岛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岛上盘踞了很久。他们逃往台湾前在岛上抓走了很多壮丁,所以那时岛上的男人特别少。男人要出海捕鱼,家里的农活啦,修船织网啦全是女的做。那时要全民皆兵,要每家出一个民兵。好些人家里没有男的,只好女的出来了。女子民兵连成立后,我们每天在海滩上巡逻,有一天,发现刚退潮不久的沙滩上有几个可疑的脚印。我们一边派人报告了部队,一边跟踪着目标,最后抓到了一伙台湾特务。你爸爸为这事专门来到海岛为我们开庆功会。《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通讯一出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
“那个年代的人好像很容易激动的,对吗?”杨虹说。
“没错,那个时候人们都等待着好事情发生。”
“你对于过去的事有一种真诚的怀念。”杨虹微笑地看着李闪梅,她感觉到这个传奇女人对父亲很了解。
“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思的时光啊。”她说。“杨记者,我今天请你来,是以鼓山县委的名义邀请你来鼓山写写我们美丽的海岛。你可以采访我们女子民兵连新的一代。”
“我恐怕很难写出好东西,鼓山的女子民兵连太有名,已经被人写到顶峰了。”
“不写女民兵也行,写你任何感兴趣的东西。鼓山岛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应该在鼓山多住些时候,你会听到你爸爸的一些故事的。”
“那好吧,我得向报社领导汇报这个事,不知他们同意不?”
“没有事的,报社领导我已做过工作,他们同意了。”
几天后,杨虹坐上开往鼓山岛的船。这个时候她已和谢青分居,出差旅行是家常便饭。
船离开码头,在潮涨中驶离港口。江水中有许多沙渚,上面停留着很多好看的水鸟,尤其是那种长腿的鸬鹚,让杨虹看得发呆。江水原来是黄的,慢慢变清,变成了蔚蓝。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东海。杨虹只觉得心情阵阵愉快。她小时那次跟爸爸到海岛的记忆慢慢从意识的深海里浮现出来。她站在船头,风吹起了她的头发,心情不觉有点激动。不到半天,她看见了鼓山岛的码头。杨虹上岸时,没看到李副主任,是现任的女子民兵连长来接她。连长的名字叫许丽丽,一个现代人的名字,人也长得很性感。她说自己是第六代女民兵连长了。她说李闪梅主任今天有会议,不能脱身,让她来陪杨虹参观。
不久,车子到了海滩边一个崭新的建筑前面。这是新落成不久的女子民兵连纪念馆,红瓦白墙,门口停着一门一三零毫米的加农海岸炮。一进门,就能看见一张毛主席和李闪梅握手的大照片。一个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朱德元帅赠给女子民兵连的半自动步枪,还有朱德和女民兵的合影。纪念馆内有很多军队高级将领视察海岛的照片,杨虹认出有叶剑英、罗瑞卿、姜启良。令她激动是一张她父亲和女民兵的照片。她以前没看见过父亲的这张照片,照片放大得和真人一样大,看起来呼之欲出。她的父亲长得是那样气宇非凡,目光有神,今天这些油头粉面的官员怎么能和他比呢?父亲的身边围着一群女民兵。杨虹看到了年轻时的李闪梅的动人形象。她穿着一条大红的衣服,剪着短头发。她丰满的胸部在扎上了军用腰带和两条交叉的枪背带和子弹带之后,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性感。照片中她站在父亲的对面,和父亲说着话。让杨虹感到吃惊的是照片上李闪梅看父亲时的眼神,那可是一种充满情感的目光。杨虹难以相信一张旧照片会包藏着什么秘密。也许是偶然的因素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目光吧?但是不对呀,这次李副主任邀请她来鼓山采访,本身就好像不同寻常。杨虹回过头来又仔细研究其他照片。她看到李闪梅和毛主席照的那张眼睛里全是激动泪水,她怎么敢对毛主席放电呢?和朱德的这张照片她的眼睛是看着那支半自动步枪的。和姜启良将军的那张呢,她的眼睛闪着明亮而坚决的光辉,好像正向首长报告过什么重大事情。只有这张和父亲的照片,她的眼睛一不小心流露出了女人的秘密。李闪梅从侧面看着父亲,眼神充满了幻想,有一种热烈又温柔的光。“这张照片中存在什么秘密吗?可能是我的联想太多了。”杨虹寻思着。
这天晚上,杨虹被安排住在台胞招待所。这些年,有很多台湾渔船在鼓山一带海面作业,因此有大量台湾渔民在鼓山岛加油、修船、休闲。鼓山岛新开的台胞招待所是这里最好的旅馆。晚饭由县委宣传部出面摆了两桌酒席,来了好多领导。但是李闪梅还是没来。餐厅里声音很大,那些大呼大叫的台湾人十分令人讨厌。一个个领导轮流向杨虹敬酒,累得她只想早点结束。好不容易吃好了饭,他们说请她去唱卡拉OK,杨虹赶紧说自己今天坐船晕船了,头疼得厉害,才脱身回房间休息。
杨虹回到房间,头的确有些疼,加上刚才被逼得喝了不少酒,她和衣躺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她醒了过来,听到招待所里的卡拉OK厅里无休止地唱着同一首歌,是那首用闽南话唱的“爱拼才会赢”。她把窗关了,先是觉得安静了些,可没多久,那些噪音无孔不入,又充斥了房间。她去洗手间洗澡,看到梳洗台上摆了两个安全套,还有一些防治性病的药液。这让她觉得好像自己住进了一个妓院。电话响了,刚拿起话筒,那边就说:喂,要小姐按摩吗?杨虹一声没响把电话挂了。她开始冲澡,水质非常的好,溅到嘴里有清甜的味道,不像AC城里的自来水带一种臭味和碱味。她刚洗好澡,电话又响了。她想一定是那些小姐又来电话了。
电话响了三下,她没接。响了五下,她还是没接。到第七下时,她无奈地拿起了话筒。但是她不想开口,以为对方的小姐会先说话。可是听筒里却无人说话,静静的,但能感觉到对面的电话机前一定有个人拿着话筒,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杨虹只得说:“喂,请问你找谁?”
“是杨记者吗?”对方说。杨虹马上听出是李闪梅的声音。
“我是,你是李副主任吧,这么晚了还没睡?”杨虹说。
“是呀,我睡得晚。对不起今天没陪你吃饭。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没出去。”
“那你要注意休息哦。”杨虹说。但她觉得李闪梅说身体不好不大真实。她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来。其实她不来杨虹倒放松些,要不会觉得更累。
“没什么事,我就是向你问候一下。早点睡吧。哦,对了。要是睡不着,你可以把窗打开吹吹海风。窗子外边就是海对吗?你有没有看见远处有个一闪一闪的灯塔?那个灯塔还是你爸爸在一九六三年特别拨款批准建造的。”
“知道了,谢谢你的提示。”杨虹又和她说了几句客气话,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