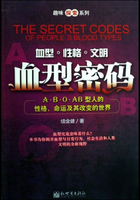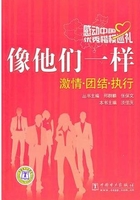坦白地说,我家里的事全由太太做主。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不像有些人那么虚荣,明明一切都由老婆说了算,却在外面愣充大丈夫,口吐狂言:大事听我的!谁不知道那大事指的是什么——全球气候变暖、防止核武扩散以及美国总统大选而已。
我常如实地告知我的同事,在我们家屁大的事都得听老婆的,我只管比屁还小的事。
老一辈人说:“牛驾辕,马拉套,老娘儿们当家瞎胡闹。”这话虽然既难听,又偏激,可也有一定的道理。女人做主不见得事事都做得对,以我家为例,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我老婆就犯了个不小的错误,给我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
按我的想法,楼层不必太高,住三四层就挺方便的。她说我弱智,三十层的塔楼,住在三层跟住在地下室里没什么两样!这叫什么话嘛,三层和地下室怎么会一样呢!我心里不服,但嘴上没说。
最后当然由她拍板,买了二十八层,比选择三层同样的户型多花了二十几万。
住高层的优点很多,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连下雨都比楼下的人知道得早。上下楼乘电梯,省时又省力。我也觉得满舒服的。
没过几天,一个新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越来越心神不宁、忐忑不安。
负责开电梯的女工,每天捎带着卖《晚报》,搞起了第二职业。《晚报》摆在电梯里的小桌子上,一块钱一份。很多住户上电梯时都顺手拿一份,再扔下一块钱。有时,开电梯的女工还唯恐别人忘了,对没买报纸的人关心地问上一句:“您不来一份?”我就被她提醒过好几回。我每次都笑着摇摇头或摆摆手,说:“不用了!”时间久了,那女人脸色越来越阴沉,像是挺生气的,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生硬起来。有几次,她明明看见我跑过来了,却关上了电梯门,让我不得不再等一趟。我觉得问题出在报纸上了。
有一天,就在她关门的那一瞬间我挤上了电梯。“没长眼睛啊,电梯门夹坏了你负责呀!”她没好气地冲我嚷着。我不好意思吭气,电梯里还有别人呢!“来一份报纸吧!”她白了我一眼。“不买了,我家里订了。”我想撒个谎,打消她的念头。“真小气!”她小声嘟囔着,很伤我的自尊。
我很少看报纸,各类新闻网上都有,在办公室里早就浏览过了。再说,女人当家,心细如发。我老婆每月只给我留出三十块的零用钱,平均一天一元。她说,男人有钱容易变坏。为了把我塑造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她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有效手段。如果我每天都买一张晚报,那一个月下来我恐怕连头发都理不了啦!所以,我不买报纸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那开电梯的女工却不管我拮据的经济状况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她不断地用殷勤、热情以及白眼和恶语对我交替施加压力,我终于坚守不住了,不得不也“来一份晚报”!
一连二十多天,她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而我口袋里仅剩下四块钱了,我的头发快遮住耳朵了,如果我老婆知道我把理发的钱花在了开电梯的女人身上,她会发疯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决定爬楼梯上下班,尽管我的关节炎一直折磨着我,但那也比心理折磨更容易忍受。二十八层楼啊,对于我这样一位体重接近两百斤、脚上长鸡眼、膝盖里积水的“残疾”人来讲,的确是一个致命的考验。我还是要咬牙坚持,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电梯女工那嘲讽鄙视的表情时,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连续爬了半个月,实在熬不下去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攒够了理发钱,可以让耳朵重见天日了。我完全有资格大大方方地坐一次电梯,感受一下迅速升起的快乐。
开电梯的女人热情地冲我笑着,像是久别的亲人一般。“您出差了吧,看您瘦了不少。”她关心地问我,我嗯嗯地点了点头。她弯腰从椅子下面抽出了一沓报纸塞给了我:“这些报纸是我每天替你留下的,一共十五份。”
天呐,我的脑袋一阵晕眩。我正准备用那十五块钱明天去理发呐!
惹火烧身
我和我的朋友老梅同时染上了写小说的毛病,但结局却大不相同。
我比老梅先动笔,写了个短篇。老梅过目后,很宽容地夸奖了我几句,说我有一定的写作天才,文字水平“相当凑合”。我的作品唤醒了他创作的冲动和勇气,他拍拍胸脯跟我夸下海口:“我要么不写,要写就写个大的——长篇,一炮打响,一鸣惊人!”然后,便像仪仗兵似的迈着正步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儿。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当兴奋时便夸张地走上几步。
老梅办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出一年,老梅的长篇小说——《惹火烧身》隆重推出,没等卖出几本,一场轩然大波却在老梅的单位内部掀起。整个单位上下从领导到同事,包括看大门的,都纷纷登门找老梅算账,要讨个说法。据说,他们个个都从《惹火烧身》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换句话说,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能从本单位找出相对应的真人真事。这下可麻烦了,老梅家的窗户玻璃没剩下一块完整的,老婆孩子也跑到外地的亲戚家躲了起来。只有老梅还待在家里——不是他愿意住,而是被同事、领导们“监视居住”,未经允许,不准离开。
我十分担忧地跟他通电话。“没事的,你放心。”老梅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小说创作纯属虚构,那些对号入座者,完全是自作多情、自寻麻烦。”他进一步安慰我。
“听媒体上说,你们单位的全体同事要联合起诉你?”我心里还是不太有底,在电话里小声问道。
“没事的,我那是个小单位,全部加起来不过三百多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梅还真能想得开,说得多轻松,“不过三百多人”。我心想,别说三百人全去法院告你,就是三个人也能把你搞垮。
“你那小说到底是怎么写的,写举报信也不至于所有的情节都能对得上呀!”我不仅替他担心,也有些好奇。
“真实呗!文学的本质就是真实。我不像你那样,什么虚构啊,幻想啊,那都是胡编乱造。我写得实在,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老梅挺倔,不允许我对他的大作有任何质疑。
此后,我一直想找到那部长篇看看,但一直没找到。听说本来印数就不多,又被要求停止发行了。
差不多过了半年,我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惹火烧身》侵权案的审判结果。报道中介绍了“惹火”事件的来龙去脉、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法律专家的相关评论。从那篇详细的报道中我了解到,老梅的大作《惹火烧身》的确写得太实在了。连故事发生的单位都用了他所在公司在工商局里注册的真实名字,小说中的人物也都能从他单位的电话号码薄中一一查到,故事情节据说与这些年里老梅公司里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甚至连主要人物(小说中以贪污好色而闻名的领导)居住的楼牌号码都与现任领导的一模一样。老梅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把他所知道的同事们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正如某位法律专家所说:小说在当事人看来,只是一个幌子。书中的少许虚构部分均是作者别有用心的恶意猜想和肆意丑化。这显然不是一部所谓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封内容龉龊的匿名信。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取得了大量翔实可信的证据,最后判定老梅赔礼道歉并处以二十三万元的经济赔偿。
我至今仍十分珍惜地保存着那张报纸,我不是想从那篇报道中汲取教训,而是因为那张报纸上同时刊发了我的中篇小说《相安无事》获奖的消息。
莫提包
莫教授的手提包至少陪伴了他半辈子,里面装着他一生的荣耀。
我第一次结识莫教授时,估摸他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头上的黑发已经屈指可数了。他从提包里翻找好一阵子,才抽出了两张纸,那是他的个人简历,上面除了姓名、性别、民族、籍贯、本人成分和政治面貌之外,还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出生日期——1930年某月某日。那一年他正好五十周岁,与我估计的年龄略有出入。履历表上用红笔校注的另一个时间点格外引人注目——1945年8月14日——那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每当给人出示这张表格时,莫教授都要反复强调这个日子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越说越激动,嗓门越拔越高,直到对方点头称是为止。因为莫教授参加革命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投降了。曾有人调侃他:“您太厉害了!别人打了八年都没管用,您一参军就把日寇吓跑了,大大的厉害!”他得意地自谦道:“那倒不是。关键是涉及离休待遇问题,这可马虎不得。”
莫教授的手提包内容可丰富了,据我观察,至少有二十多种他逢人便掏出来如数家珍般向人炫耀的宝贝。我看过无数次的珍品有:奖状两张、工作证一本、出席国庆游园会请柬两份、会议代表证三个、参加大合唱时与国家领导人的集体合影一卷(照片有一米长,卷成筒状)、名人信件五封(他当年的战友和同学,后身居要职)、他参编的《人民公社万岁》一本、发表的文章四篇(代表作为《从〈红灯记〉的演出成功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胜利》)等等,前两年包里又塞进了两本砖头般沉重的精装大作——《中华名家辞典》和《世界名人大全》,书中各用二十多个字系统地介绍了莫教授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