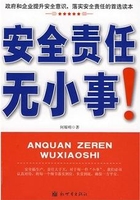他俩一来二去文采斐然,简直不像行将就义之士,倒如同两个醉入他乡的豪客。正说话间只见一个异族服饰的男子带着三个属下拎着三坛酒上来了,这人就是曾祖父的贴身侍卫扎西。他奉主子之命带着两个属下骑着跑马去太白楼买了三坛好酒,经过华西坝时又砍了两根翠竹,将竹节打通,做成饮酒的吸管。刚才刘大人已经同意了曾祖父的请求,天气太热,刽子手一时无法行刑,曾祖父说自己有办法让刽子手立即动起手来,便派人去买了酒回来。扎西将坛子揭开,端起一坛酒倒在刽子手身上,血立即随着酒化解,浓浓的酒香掩盖了膻人的腥味儿。衙役派人提了一桶水回来,给刽子手从头上淋到脚下,扎西又递了一坛酒给他,刽子手感激地大口灌了起来。扎西按照曾祖父事先做好的安排,顺手将一坛酒倒进刚才的那个水桶里,衙役们只以为他还要给刽子手冲洗,都没有去阻拦他。接着,扎西将酒坛子里剩下的酒高高举起,全部倒在了刽子手头上。石达开和黄再忠闻到酒香,嗓子眼儿里冒起火来,想骂又不愿开口,不骂又不甘心,胸中窝火难受,二人便都不说话了。这时候曾祖父赶紧来到刘大人跟前,对他说道:
“刘大人,在下的办法可还有效?”
刘大人见刽子手刚才还萎靡不振,现在已是生龙活虎,便高兴地赞道:“己大人的办法果然不错,那厮已然捡回魂来。”
曾祖父说道:“这么热的天,谁愿意顶着大太阳干这么无聊的事儿,早点结束早点交差,咱们回去还可以小饮几杯,您说是否?”
刘大人也说:“己大人所言甚是,这天气实在太热了!”
曾祖父趁机问道:“大人您看那两个逆贼,气息奄奄,无精打采,一副死相,刚才还精神矍铄唱来和去,现在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煞朝廷的苦心。这么热的天,不如提桶水给他们润润嗓子如何?”
刘大人当然应允,嘱咐道一定要他们打起精神,让老百姓瞧瞧造反的人不得好死的下场。曾祖父唤来扎西告诉他依照计划行事,扎西便将打通的竹管扔进盛着酒的水桶里,刽子手身上和地上散发的酒味儿掩盖了水桶里酒的味道,扎西拎着水桶迈着沉重的步伐,一边用摩梭语唱着《敬酒歌》,一边朝石达开走去。石达开听到扎西的歌声立即热泪盈眶,昔日他在大渡河畔,曾造访过宁属地区的摩梭人家,他们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摩梭人有一种习俗,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便要打开一坛苏里玛酒,将凿通了节芯的翠竹插入坛中吸出酒来招待客人,在向客人敬酒的时候大家便一起唱《敬酒歌》,整个气氛又热闹又亲切,故而苏里玛酒也有竿竿酒大家唱着大家喝的美称。汉人听不懂摩梭语,不知道扎西唱的是什么,倒是石达开心里明白,这个小伙子是在给自己敬酒。衙役们都不知道水桶里盛着美酒,就连石达开也认为那不过是刚才给刽子手洗身子的清水,要不是扎西唱着《敬酒歌》上去,他怕是到死也不会喝的。扎西来到行刑柱跟前,举起水桶,将竹管伸到石达开嘴边,用摩梭语对他说:“喝吧,英雄!”
石达开一听,无限感慨,昔日在摩梭人家的宴席上,他也跟着大家入乡随俗,和大家一起说着敬酒的摩梭语,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然而诸多祝福的语言他早已忘却,唯有这句“喝吧,英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每当《敬酒歌》结束,大家总会一起喊道:“喝吧,英雄!”次日席散,他习惯地在每一张桌子上放一锭银子,算是给主人家的谢礼。可是不到中午,几个摩梭汉子便骑着跑马赶了来,将所有的银子退还给他,很不高兴地说:“我们摩梭人招待你们汉人喝酒,看得起你们是英雄,你给钱就是看不起我们,我们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崇敬英雄。我们招待你是真心真意的,所以把你的银子拿回去。”石达开只好收下银子,又在军中宰牛赔礼,双方喝了酒,方才解了误会。今日,他虎落平阳,身为刀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却有这样一个摩梭汉子突破层层阻挠上来献酒,心中想起自己曾经在苗家山寨里即兴所赋的诗,默默念了出来:
千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
五岳抱住擎天柱,喝尽黄河水倒流。
石达开一口气吸干了大半桶酒,真有“喝尽黄河水倒流”的气势,他知道自己不能赞叹这美酒,也不能感谢这送酒的人,因为他将整个精心计划的过程全看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由于全身无法动弹,他只得向扎西眨眨眼睛,扎西点点头便提着空桶退了下来。石达开的目光一直跟着扎西,扎西来到主子跟前,曾祖父便起身向刘大人告辞,说自己是高山上下来的,受不住你们这样炎热的天气。刽子手就要准备给黄再忠行刑,刘大人分不出心思来跟曾祖父道别,便礼节性地应了一声,劝他早点回去,免得在外中暑。临走时,曾祖父满怀悲痛的心情向二位英雄望去,却正巧碰见了石达开的眼神,二人注视良久,心中默默,仿佛久已相识。为了不引起其他朝廷官员的注意,曾祖父只轻轻地点了点头,石达开也眨了眨眼睛作为答复,二人便就此别过。
曾祖父回到总督府,齐集人马,当天晚上便辞别了骆大人,带着马帮出发了。昨日他还答应要将一百精骥借给骆大人巡城三日呢,现在却已忘到九霄云外,只剩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郁闷。经过十余天的长途跋涉,土司的队伍终于进入凉山地界,沿途碰见许多游兵散勇,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纷纷朝着汉地逃窜。又遇到不少清军在追,沿途设关立卡,只要怀疑口音稍有不正,不问所以,立即就地正法。一日,他们行至沙马土司界内,碰见一队彝族士兵押着几个穿着破烂的汉人,脖子上戴着的铁链吊着手铐,每个人的脚上都穿着沉重的木靴。曾祖父碰到他们的时候,大家都在同一条小溪边歇脚。
一个老人家说话的口音引起了他的注意,老人家说:“娃崽,莫要哭,只鳖七坏透骨,侬莫要硬颈……”
曾祖父一听,老人家的口音竟如此熟悉,让他想到了某人,那就是翼王石达开。那日他曾听石达开用方言与部下交谈,说话的腔调跟这老人家的一模一样,便好奇地聆听他们的谈话,却发现只有这爷孙俩才是这种口音。曾祖父叫扎西过去,把彝兵的头领叫了过来。彝兵头领听说是鼎鼎大名的瓜别土司,便赶紧过来下跪行礼,说自己是沙马土司的卫队,押着这些奴隶卖到深山里去。
“他们都是汉人吗?”曾祖父用彝语问道。
“回禀老爷,”彝族头领回答说,“他们都是汉人,有从汉地抢来的,有别人卖给土司的,有我们自己俘获的。”
“他们是长毛吗?”曾祖父指着老人和孩子又问。
“是。”彝族头领说。
“你把他们带来。”曾祖父命令道。
头领跑了过去,强行将老人从孩子身边拖了过来,曾祖父就用汉语问道:“老汉您是哪里人?”
老人并不言语,也不看曾祖父。
“老汉可是广西贵县人?”
老人瞅了一眼曾祖父,眼神里充满恐惧,又将头埋了下去,仍不说话。
曾祖父用彝语问彝族头领:“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抓到他的?”
“马颈子附近的山上。”
“是与长毛交战的地方吗?”
“是。”
“还有其他长毛吗?”
“有好几个,”头领回答,“其中一个年轻的,想要怂恿娃子逃跑,给打断了腿,关在猪圈里了。”
“你去问一问你们老爷,瓜别土司说他从成都领赏回来,路过你们沙马家的地盘,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他欢不欢迎?”曾祖父说。
“当然欢迎,”头人拍马道,“小人马上回去禀报。”
头人骑着跑马一路飞奔而去,等他走远了,其他的彝族士兵又离曾祖父他们很远,这才对老人问道:
“杨斤木鼎酒,已盖大?”
曾祖父的话音很古怪,他其实想说:“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这是石达开行刑当日,他在刑场边偶然听到的几句话。他很想知道这几个汉子临刑时何以那么坦然,又都在说些什么,无意中便记下了这么一两句。
老人家没有听懂他的话,还是不理他,眼睛却望着自己的孙子。
“引基母……”曾祖父又吞吞吐吐地说起了这句话,可还是学不会说不全,便索性不说了。过了一会儿,两个彝族士兵过来,把老人押了回去。老人临走时,曾祖父突然想到什么,便马上说了一句:
“马……别……宰?”
老人猛然回头,曾祖父又说道:“宰……别……马?”
“妈别崽,崽别妈。”老人说。
“对对对,就是这句,”曾祖父高兴地叫道,“妈别崽,崽别妈。”接着又脱口而出:“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老人赶紧接道:“只恨苍天昏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彝族士兵想将老人强行拖走,扎西用彝语制止道:“嘿,没看见土司老爷正在跟老人家说话吗?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赶紧退下。”
一听扎西的吆喝,他们又将老人扶了回来。曾祖父跳下马,上前握住老人的双手,亲切地说:“你是广西人,你的声音跟他一模一样。”
“您是?”老人看到彝兵如此畏惧这个衣着异族服饰的中年男子,带着恐惧疑惑不解地问道。
“我是瓜别土司,住牧在九所地区,跟他们的主子平起平坐。”曾祖父指着两个彝兵说。
“你是蛮子?”老人家的神色略显紧张。
“我是摩梭人。”曾祖父看看那两个彝兵,安慰道,“老汉尽可放心,我不会伤害于你。”
“您怎么会……”
“我见过你们的首领了,”曾祖父打断老人的话,继续说道,“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正的英雄。我己格部家一生中敬佩过两个人,不过现在只有一个了,那就是他。”
“您是说……”
“你们的翼王石达开!”曾祖父再次打断老人的话,一听到“石达开”三个字,老人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道:“他……他……怎么样了?可是……保住了……保住性……性……命了没有?”
“老汉,节哀吧,他已经……”
“算了。”老人迫不及待地打断道,他早已经料到有如此结果了。“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清妖之言不可信,天要亡我,天要亡我啊!”
老人说完,伤心欲绝地号啕大哭起来,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几个彝族士兵赶紧围了上来,以为出了状况,竟想打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曾祖父大叫一声“退下”,将他们制止了,他们于是心有不甘地站在一旁不敢过来。正在这个时候,刚才骑着跑马出去通报的头领也已经回来了,还在马背上就兴高采烈地喊道:“有请土司老爷,我们沙马老爷已经准备好了美酒和牦牛,招待你们远方到来的客人。”
“都是大凉山的土司,”曾祖父说,“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哪儿有什么远不远近不近的。早就听说过你们沙马家热情好客,不愧是凉山第一大彝族土司,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头人跳下马来,给曾祖父跪下,恭敬地奉上一根精致的马鞭,这是一种迎接贵客的方式:要客人赶着跑马快来,以显示主人家的热情。曾祖父暗中做了安排,要手下好生保护祖孙二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马先行过去。他们骑着跑马到了土司家,沙马土司果然用了最隆重的礼节招待客人,当场椎倒了十头牦牛,次日又杀了二十头牦羊。临走的时候,曾祖父用重金赎出了老人和孩子,朝廷还在四处追剿太平天国的余党,曾祖父便带着他们一起回到了瓜别。而那个想要逃跑的汉子据说正是这孩子的父亲刘半仙,人们找到他时尸体已经僵硬,满身都是猪粪,清洗之后便在回来的路上就地火化了。一年后,老人家在瓜别去世,临终时他告诉孩子:“铭崽啊,你就跟你义父姓刘吧,毋要再返屋了。但是你要永远铭记……你……铭记……”至于铭记什么,老人没有来得及说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