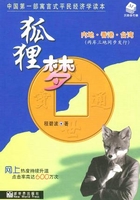在我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时,有人站出来警告日本别因此幻想削减对中国的援助,你对中国的援助那是对历史的补偿。言下之意,钱我还是要的,但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眼里盯着钱,说话就有些不讲理,远赶不上以前我们虽然穷,但还可以硬气地对日本人说,“为了中日世代友好,我们放弃对你们的战争索赔”来得痛快。
放弃索赔,对不对,那是单说,但既然已经放弃,作为后来者就该认这个账,那才是做人的本分。至于日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怎样的一个民族,你睁大眼睛看清楚就行了。超过别人还向别人要援助,这其实就是自陷于困窘。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争什么援助,而是要埋头做,以便今后日本向我们要援助时,懂得怎样礼貌地拒绝,实在拒绝不了,就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多少提供点。
作为新兴大国,别人因此期待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说实话,我们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有点茫然,准备得也不充分,两者之间有些不搭调。这一点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自愿减排,不受“三可”(可报告、可检测、可核实)原则约束,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已是全球第一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应该可以接受可报告、可检测、可核实的原则,应该多做点事情。
虽然最后哥本哈根会议在我们看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外国媒体却普遍对中国在会议上的表现有些微词,英国气候大臣甚至在《卫报》发表公开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会议谈判。对此指责,我们的外交官当然予以了义正词严的反驳,毫不留情。
不可否认,中国已是一个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甚至美国总统也为了避免会议僵局,不得不两次离开会议中心,到中国总理下榻的酒店登门拜访,第二次甚至还在门外等了半个小时,理由是中国总理正在和别人谈话。
这倒不是中国有意要怠慢美国总统,而是大概没想到他会两次不请自来,没想到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就这么重要,而中国却认为自己还没重要到美国总统两次登门拜访的程度,两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导致了中国外交上的“失礼”。
在我们自己看来,中国还不强大,人均国内总产值只有4000多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很远,国内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照联合国标准),脱贫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够忙乎好长一阵子的,在国际上只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两者认知的差距导致了我们对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性。“妾身未分明”,说话就会有些闪烁,行为上就会有些矛盾。虽然我们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但现实却有着很多的阻碍使我们进退两难。
国际上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都掌握在西方人手中,有的我们不太认同,虽然目前还不得不尽量合着西方的音乐节拍跳舞,但内心总希望有一天舞场里会响起京韵大鼓,因此就难免跟错节奏,踩着西方美女的脚。
更麻烦的是,我们踩了西方美女的脚后,有时还不会道歉,因为我们知道用中文说了对方也听不懂,就只好笑笑,笑得多了,对方就以为我们是在“揩油”。
说我们想“揩油”,甚至说我们“傲慢”,那是误解,根本原因是我们还不大会用别人的语言,按照别人的思维方式向其解释为什么会走神、会跟错节奏、会踩着她的脚。我们可以说不,但得以别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而不能一味地生硬。如果以为生硬就是强大的标志,以为国内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那就又落入了天朝帝国的窠臼。
有学者曾指出,日本很早就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理说是一个大国了,但由于日本人成天板着脸,不会说话,要讨好别人时就只知道一个劲地鞠躬,所以外交上很被动,没办法,只好在1985年纽约的“广场”里签订“日元投降协定”,由此进入“失去的年代”。
这种研究,是严肃的也好,不严肃的也好,但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性,那就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想的,今后会怎么样,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就是要“透明”。
我们需要外界听见中国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手机里可以自由切换的假声。输出中国文化,不是单靠政府支持几个“孔子学院”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几个歌唱家到国外大剧院吼几嗓子“主流”歌曲就可以的。我们需要民间广泛的参与,甚至也会需要某些“敌对势力”的噪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外界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
脆弱的社会结构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按照社会财富和权力资源进行的分层早已出现并正在不断强化。
社会主要群体,包括农民,工人,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等群体,他们收入低,生活窘迫,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政治上几乎没有话语权,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作为现代社会“减振器”的社会保障体制远没有完善,无法从制度上给予这些人有尊严的生存权,很大部分弱势群体因此成为或自认即将沦为社会底层,成为“被社会排斥的人”。
根据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日益扩大,低收入、失业半失业、无业等社会弱小群体弱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位居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走向了联合,在大众诉求面前结盟。“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官员博士化”、钱权相连的利益依存是他们结盟的具体表现。
精英结盟导致了垄断利益和以权谋私的大量出现,并形成了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为强化这种结盟,精英群体趋向于精英的自我再生产,上下流动渠道被堵塞。而精英因利益而结成的联盟在各自的利益面前缺乏足够的稳定性,他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大肆获取利益的同时,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大量移居国外,部分官员自己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或者觉得待在国内还可以多捞一点的,就将妻子儿女连同财富先行转移出去,自己在国内“裸着”,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可以溜之大吉。
据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人员高达18000多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长迅速,2008—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的人数出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计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某些移民目的国甚至迫于移民人数不断增长的压力提高了投资门槛。
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推出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新富阶层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主27%已完成投资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一个社会中,甚至连既得利益集团都事实上分崩离析,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在中国所占比例还很小,且面临被消灭的风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新加坡更是高达90%,就是印度也自认为中产阶级比例达到了50%以上。
而在中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占总人口的22%~23%,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也就是说到2013年,乐观估计该比例也仅有28%。而对于中国社科院的这个结论,由于缺乏较为一致的标准,很多人不以为然,以为自己“被中产”的可能性很大。
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而在目前的中国,这两个条件却难以实现。精英的自我再生产导致向上流动渠道堵塞,而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增量”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改革深入已需要某一部分人让渡既得利益,但由于权力垄断导致机会不公,这种让渡很可能变成对大众财富的再掠夺。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受益者,只是多少不同,这也是在目前贫富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社会能保持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以为这种状况可以持续下去,那就是对现状的误读。
曾经的主流日益边缘
在一个明显分层、价值取向多元、贫富悬殊的社会里,要谈“主流”是一件颇有危险的事情。这种危险不仅是你走在路上就可能有莫名其妙的板砖砸过来,更可怕的是当你头破血流时,可能还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同情。
什么是主流?大家都搞不清楚。官方是主流?底层大众是主流?抑或是知识精英?似乎都对,但又都不对。你能说中央电视台宣传的不是主流?当然不能,但这个主流似乎又没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2010年隶属于《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杂志“未来10年10大挑战”课题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有一个就是“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既然自己都承认“边缘化”了,那就很难再说自己是主流。底层公众人数多,似乎该成为主流,但社会上却很难听见他们的声音。知识分子按理说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但社会明显分层却使他们很为难,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站在官方立场吧,似乎被“御用”了,缺乏独立之人格,站在底层吧,似乎又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于是很多时候都“不知所云”。
一般以为搅乱我们思想的是外来文化,大门打开,外资来了,但“苍蝇”也“嗡嗡”地飞了进来,污染了环境。西方价值观异化了我们原来的理想,使我们从“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变成了“拜金主义者”,从一天到晚喝稀饭,像驴一样忙活的人变成了“物欲横流”的“享受主义者”,我们成为了物质的奴隶。如此的不堪,自然该受到“主流”的批判,但那些“主流”、“精英”似乎都高高在上,完全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只是一味地鼓噪,像留声机一样,我们怎么听都很别扭。
正是因为没有彼此认同的东西,大家就难免互相嚷嚷,嚷嚷久了,都觉得乱,都以为现在社会思想五花八门,物欲泛滥,缺乏理想,都不知道人怎么活着。“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世风日下。因此,人们觉得就更需要主流价值观了,以便社会出现困惑的时候,“主流”可以站出来处理分歧。
我们处在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但又是一个激情的年代,社会的种种情绪由于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发出了巨大的和声,身处这个环境,有时已很难分清主流与非主流,谁对谁错。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大众和精英阶层有了直接交锋的可能,在这种交锋中,虽然多数时候壁垒森严,彼此之间常常鸡同鸭讲,你宣传的我不信,我说的你又以为那只是社会的阴暗面,都代表不了主流。
互联网的出现,使底层有了表达自己对社会真实看法、发泄不满的阵地,而由于技术进步,封锁或压制互联网消息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正是有了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底层真实的声音才可以上闻,社会的不公才一定程度上得到重视并纠正。这是曾经“沉默的声音”党报呼吁倾听“沉默的声音”。人民网,2011年6月3日。
在这种时候,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有时候会变得扑朔迷离,昨天的敌人可能今天就转为盟友,而今天的盟友一夜之间又可能成为敌人。正是在这种相互的碰撞、排斥与融合中,我们的社会主流意识才可能渐渐成形。
精英集团和社会大众利用不同的舆论阵地,相互之间争夺舆论的主导权,期望自己的看法可以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乱,是因为彼此之间一时找不到契合点,未能达成共识,社会大众的多元的价值观还只是一些“碎片”,无法得到官方的认可,而官方认可的,事实上又已经“边缘化”。
要成为主流,首先需要有代表性,其次要有导向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深植于国家的传统文化之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外来文化的到来会使其受到一定冲击,并在相互的碰撞中吐故纳新。网络时代,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极为频繁,顽固地坚守原有传统而拒绝变化的文化,不是消亡,便是被其他文化所替代。
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应该是常态,不同文化间的借鉴可以促使文化的共生共荣。在主流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坚持一种既定的标准,凡与这个尺度不合的,均被排斥,那么,“主流”的形成很可能遥遥无期,而“主流”的继续混乱也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集中于先秦时代,秦汉“大一统”后“独尊儒术”,思想被阉割,人性被压制,中国历史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朝换代史。近代五四运动方重启民智,但时日很短,不久就陷入“主义之争”和闭关锁国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