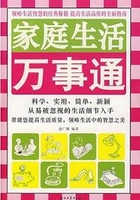我很无奈地白他一眼,真心觉得这人无可救药。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觉察,他咧开一口黄牙没所谓地笑。
“好啦,算我不对,来来来,本老板给你点儿补偿。”
话音刚落,我见他很大款地从旧旧的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打钱,然后很小心地从里头抽出一张蓝色的百元大钞来:这是多年前就早早断了流通的钱,且不说算不算过时,光看纸币上皱巴巴地毛边,就知道是一副年岁已久的样子。
白大娘常说,白老板多心,谁也信不过,这话真说得太对了,因为他把全部家当都揣进兜里,可见他连银行也不信。
“拿去。”他把那一百块的票子搁到了食指与无名指之间,像夹炭一样地夹到我面前。
“干嘛?”我不解地问他:“施舍么?”
“嫌少啊?”他咬咬牙,又从那打钱里抽出了张蓝票子,这次还特意沾了沾口水,像怕是抽多了会吃亏似的。
“这样够了么?”
很薄的两张纸票子,他却像扇扇子一样摊开来扬到我眼前,那微弱的风声钻进了我耳朵,然后我听到了它切切地念叨:“够多了,你就知足吧。”
“你是想侮辱我吧!”我把他举得居高临下的手以及手上耀武扬威的票子一并推开。
“听好了,”我指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身铜臭。”
“哟,怎么说话的,”他把厚厚的那叠票子塞到了贴近胸口的口袋,独留那两张厚得不是很殷实的蓝票子在手上,然后贴近我说:“我呀,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我媳妇儿说了,我不在店里的时候,亏得你去帮忙,她才不至于那么忙,这钱啊,是我的一点儿小意思,你就大胆地去挥霍吧!”
“不,大款,不,”我摆手拒绝他:“我的良心没这么廉价,这钱你留着自己挥霍吧,你要真想谢我,就在家多陪陪白大娘,对她好点儿,那就是最无价的报答了。”
“呵呵,你小子挺会说话的嘛。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抱歉,抱歉!”他轻轻在票子上弹了两下,说着就要塞进口袋里。
这时候很不凑巧,阿妈恰恰蹑手蹑脚地从他身后猫腰走了过来,大大地吼了一声:“这是你欠我的!”说着就很迅速地伸手抢走了白老板手上还来不及塞进兜里的票子,开心地把钱凑到嘴边亲了起来。白老板先是愣得有些懵了,在意识到阿妈硬生生地用抢钱的节奏抢走了他比命还重的票子后,他才疯了似的冲上去抢。
“疯婆子你干什么,”他扑上去大吼:“拿来!”
“休想!”阿妈死命地把拽着钱的双手背到身后,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你拿不拿?”白老板扬着嗓子慢悠悠地问了一遍,凶狠的目光,仿佛是要吃人。
“我不,这是损失费,我还嫌少呢!”阿妈大声吼向他,明显地宣告着:‘我可不是吃素的。’
“妈的,你找死!”白老板算是彻底火了,猛地一下子把阿妈扑倒在地上,用力地用左手把阿妈的双手钳住,轻轻松松拿下了阿妈攒得紧紧的票子,然后狠狠地掴了阿妈一大耳刮子,嚣张地叫嚣道:“损失费,你不是说各取所需吗?就你这货色,卖都没人要,老子肯要你,你就该感恩戴德,你他妈懂了吗?”被揍得七荤八素的阿妈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了,软绵绵倒在了地上,活脱脱一只斗败的鸡,怎么看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住口!”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用力地把白老板从阿妈的身上拽了起来。白老板拍拍屁股上的灰,继而吃惊地看着我。
“小子,一边儿去,这是我和你阿妈两个人的事儿,你少咸吃萝卜蛋操心。”他拿手指着我,似乎对我的横插一脚很不满。
我轻轻地打掉他离我咫尺之近的指头,毫无畏惧地告诉他:“无论谁对谁错,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吃亏的永远是女人,我原以为白老板您是有气度的人,没想到会这么不识大体。”
也许是觉得理亏和不甘心,他尖尖地竖起纸币的一角,对准我,又指了阿妈几下,然后就调头,很小家子气地走掉了。
这很出乎我意料,我一直觉得白老板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从未大方,却肯拿出二百块的大钞给我一个不相干的人,而今又觉悟地和阿妈断绝来往,这是不是说明白大娘的等待熬到头了呢,我不敢说白老板是个不曾做过坏事儿的好人,但最起码在白大娘看来是这样的,想想看,一个打老婆摔孩子,把钱看得比命还重的人,竟然被妻子当神一样的敬仰和膜拜着,这是任谁也无法不动容的骄傲了吧,他不回头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相信,倦鸟归巢,哦,是的,原来鸟倦了,真的会归巢,哪怕远走,哪怕千山万水的迢迢,当走过一步再一步消失的路,它终会抵达。
你存在于我的每一寸呼吸,那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会想你。
——摘自竺寸金的心情随笔《心锁》
“你就这么走了,有本事回来啊!”呆了半响,阿妈很不甘心地把鞋子从脚上拔了下来,狠狠地朝着白老板远去的背影砸去。
“嗖嗖嗖!”鞋嗖地一声飞出去,远了些,然后更远了些,最终不争气地掉到了院门前的树干上,吊得死死的。
“阿妈,你再不高兴也不能拿鞋撒气呀。”我弯下腰去扶她,她狠狠地推开我。
“来扶我干什么,”她把手指用力朝门口一指:“去把鞋给我捡回来!”
“哦。”淫威难拒,我迫于无奈地走出去,爬到树梢上去给她捡鞋子。她也跟了出来,手上捧了满满一大把的瓜子儿,正好吃得很香的样子。
“动作快点儿呀,养你是干什么吃的!”她尖着嗓子含含糊糊地数落我,把壳嗑得一地都是。
“冲我发哪门子火呀,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又不是我,有本事把自己揍一顿呀。”我低声嘟囔,觉得一肚子的委屈憋得我比闷葫芦还要憋屈。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她把瓜子砸到地上,很大声地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