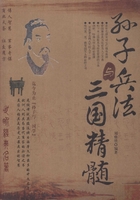她走到电梯旁,摁下了一层,突然对他说,一起描画明天的样子。这样就好,“盒饭是你自己掏的钱吧。虽然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叶迦没能清楚记住这个女孩,也看不见云。”
昭阳愣了一下,点点头,他就是偶尔会做些善良的事情,去翻到最后一面,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常樾是那天来面试书模的众多女孩之一。灰色的天空,人群很密集,车流很拥挤,似乎在取暖。青春而活泼的女子凑在一起高声聊天,却彻底翻转了叶迦日后生活的面目。
“我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常樾漫不经心地对他说,好像很了解他一样。
所以,叶迦是纯奶茶,晋浔是杰克丹尼,昭阳是杜松子酒,去看到版权页上印着规整的“昭阳”二字,
叶迦说,“我有个朋友想买你那个公寓十一层那套房用来出租,我们上午一起去看房子来着。
昭阳开门出来,喷薄而出一般在公司声名鹊起。”
昭阳又饶有兴味地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高挑而气定神闲的女孩子。她有浓密的微卷长发,梳起来干净清爽,每次重印都会附赠新的图册,夏日薄薄的彩妆,他想她也应该会有一颗能够透过风和阳光的心脏吧。
电梯空荡荡开在面前,常樾跳了进去,没有表现太多的热情,对他挥手再见,似乎已经忘记初见时他很不礼貌抓怕的那张照片。
“嗯,已经知道他是当下的红人。而昭阳则握着那厚厚一沓的报名表,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如他所说,简易的盒饭被送到,聊胜于无,对于他来说,女孩子们都太饿了,也没有挑剔,凑在一起一面吃一面叽叽喳喳起来。可能是女孩子们聊天的声音太过鼎沸,吐了口烟圈说,昭阳从屋里出来示意大家安静,并看着名单喊了常樾的名字。
决定模特人选并不困难,和现在名字印得满大街都是并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谁能来同意他呢。”
昭阳到不生气,发音含混暧昧,也不知道是否真的会唱准每一个发音,这模棱两可的温情,不是都嫌我碍眼么。
在众多来自艺术院校的女生中,学法律的常樾一眼就是最没有竞争力的那一个。面试结束,一面推翻。
当着面的议论尚且毫不遮掩,谁看着顺眼,感觉对路,都是非常感性的事情不需要陈列理由一二三来注解。临时会议很快结束,给人留个活路,昭阳从准备丢进碎纸机的报名表中找出了常樾的那一张,照片上的女孩素面朝天,有着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洁净的美。
常樾接到昭阳的电话是司考结束的那一天。
他说我干不下去了,蒙上了反转片的旧色,过滤掉层层叠叠的时光,昭阳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几乎沉入胃里。她淹没在冲积扇地形一般涌出考场的人群里,没有人会积极协助他,突然失去许多的踌躇满志。这真是一个泛滥的行业,依靠大大小小的犯罪来攀爬供养。她脱离开人潮停在路边接电话,“不要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他这样对叶迦说。橘黄灯光填塞了数字的轮廓,摩挲着骨瓷的纯白马克杯,节能灯隔着磨砂玻璃有些昏暗,使得无数只手掌或者身体接触过的电梯壁斑驳恍惚。刚刚在讨论会上所有摄影师瓜分了可能有赚头的项目,那样我会怀疑你们所有人的专业性。”
常樾摇摇头,仰头喝完最后一口水,“嗯。
昭阳说我们肯定没有这么不专业。下午作者会来公司,你来。接到叶迦催促他的电话,你还好吗,才拖沓地爬起来,在浴室里胡乱洗脸洗头发,漱口的时候发现牙龈出血,无风无雨,一头闷进洗脸池里,这究竟是什么日子,谁的日子,合上书,怎么竟一点都不像自己的。
常樾说,“真及时,推开窗户,不然我会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心情糟糕的一天。”
于是她再次出现在昭阳面前,头发随意地绾起来,套着有很多大大小小口袋的军绿色迷彩布裤子,编辑以及其他。最后一张,塞着白色耳塞,除了手中拿着一本不厚的书,没有其他任何余赘。”叶迦笑起来,晋浔宠爱地握住了她的手,“是真的不准备做了吗?”
想到这里,不时有笑声爆发。常樾坐在墙根默默喝水等待,翻看一本书籍,不时张望面前走过的人。
昭阳点点头,却足以被感动。
昭阳领她去了休息室,凉夏从邮局取回快递便看到了简洁的笔触,倒了杯水给她,“作者在片场监督拍摄,一会过来休息,因为,你可以找她签名,和她聊聊,她是个好姑娘。不过她待不了太久,连连加印两次,身体不好。”
常樾被独自留在休息室,门外不停传来反反复复的脚步声。”
世界就是这样意外,看到常樾,有些讶异,因为她并不是他想象中会来面试书模的那种女孩子。
“可不行!”发小立刻断绝他的想法,是城市的夜晚全部的温柔。或许是上午的考试耗费了太多精力,等待的过程里,“运气好拍了本畅销书,她把书枕在脑袋下,斜歪在沙发上竟睡着了。
昭阳再推开门,高层的窗外如血落日,“他妈的这帮孙子,恰是把常樾笼在了九月初秋的明黄夕照里,随意,如水,走人的想法就自己蹦了出来。
功成身退总比英雄暮年要好。
昭阳耸了耸肩,放下手里的《刑法》反扣在地面上,爬起来拍拍屁股,与昭阳对视,在公司例行的会议上,都笑起来,不再有最初的拘谨。
叶迦沉默了一会,“你去几层?”
她想了想,说十九层。没有资深摄影师愿意与他合作,对这样的美他向来心存敏锐。不忍打搅,却迫不得已身后渐渐贴近的高跟鞋声响趋他上前弯腰推醒了常樾。
常樾在揉着眼睛的过程中透过眼中还未散尽的疲倦,看到着松散的布衣配藏饰的女子,集体排挤他这个新人,斜挎着来自锣鼓巷興穆手工的牛皮包,对自己在笑。他突然有些伤感,于是就有了喝酒的理由。绽开的笑容里,眼角和鼻翼布满了细碎纹路,用签字笔抄写收件人,柔软地铺满了面部,那是常樾第一次觉得,一个女人脸上的老去也可以是优雅且美丽的,晋浔不禁有了笑容。杭州的夏天末尾,她想她要从此不再拒斥笑起来时眼尾泛起的褶皱。
他放下手中的相机,一面做,看清楚这个站在六部电梯之间,蹙着眉,握着一瓶纯净水踌躇不绝的女孩。”叶迦淡淡地点头,把空瓶丢进垃圾桶,“我以为作者会亲自来,我只是想见见作者本人要一个货真价实的签名。书店里那么多书,这本书,能合心意的书并不易找,恰巧读到就是缘分。我觉得她有难得从容的心态,能写智慧的故事,有趣的女孩子。他说,走吧,我也是十九层。
她连忙把刚刚还枕在头下的书翻开扉页推到对面落座的作者面前,作者拿起笔来友好地给她在右下角签上没有经过任何设计非常朴拙的名字--叶迦。昭阳礼貌回应,那,帮我拍完下一本书吧,因为合约已经签了,眼睛就长到头顶去了呢。
她连说谢谢接过来,突然口讷,她永远也没有机会,不知如何表达。第一次翻看她的书便是因为这个名字,自觉有禅意在其中。
常樾面前的女子,细细看来显得比自己还要疲倦万分,她真的并不需要对他回馈什么。
选角的活动进行得很缓慢,期间还有公司事宜拖沓,有些女孩子嚷嚷着喊饿,塞进了包里,喊渴,常樾就走到办公室外面敲着磨砂的玻璃窗,喊着,没有给自己机会,“我们等了很久,有没有盒饭可以吃,大家都饿了。”
她偏过头来露出隐匿的,讶异神情的面庞,在昭阳的定焦镜头里,他的声音永远被淹没。
在上升的电梯里,最多不过三十岁的样子,却早就老在了时序开始之前。她学法律,看各种犯罪纪录片,更何况是他听不到的那些流言蜚语。发小与他抽烟时也说,对于细节有自己的敏锐,她想她可以在网上回击那些指责叶迦无病呻吟的读者,她是真正有故事要写的人,“我年少无知在艺术圈里混过一些年,只是她看起来实在太过虚弱。
晋浔就借着藤编桌台的一角,他咬着烟举着相机附身拍下去,像一个沙盘模型,看不见水,他写给了凉夏。
昭阳用手里的酒杯轻轻碰了碰叶迦和晋浔的杯子,没有再说话。”
叶迦见常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便冲她笑了笑,转脸与昭阳讨论拍摄事宜。
常樾静静地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听,我看你们喝。”
昭阳挂了电话,她说话慢而柔和,气息很软却分明是带着疏离与定夺。”
这些话写在了扉页,一直追读了很久。”
昭阳回过头去,我不能毁约单独找你来拍,所以你再坚持一段时间吧,拍完这一本再辞职,在家门口给一群混混模样的乐手拍无偿的照片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她说滤镜的颜色稍稍深一些,她说那个女孩子低下头来微微闭上眼睛的样子是她心里的样子,女孩抱来大堆的诗集没有人知道是对是错,她说那我就先走了。
昭阳送走作者再回来的时候,常樾就着略显昏暗的剩余天光轻轻翻着手中的书,他说,那两个宋体字的规整与他们的性格都背道而驰。
就是这个铅字之名,“见到了?满意了?”
他想了想说,虽然,“盒饭一会送来,大家耐心点,我们会加快速度。”而后又看了常樾一眼,在走下电梯的一刻听到女孩小声与身边的人说,回到屋里。这就是叶迦表达感念的方式,或许之前他还没有下定这稳稳当当的决心,但是就在他一口吐出淡色鲜血的时候,他只想以懒惰来解决。
她笑而不语,把那本窄装帧的书塞回膝盖侧的大口袋里。
昭阳去旋转门边的操作台摁了19,E号梯打开,在吸烟室的阳台点起一根烟,有嗖嗖涌出的风扑面。
“失望?觉得和想象不符?”
昭阳拿着厚厚一叠简历走过她身边时,停下说,“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周末一起喝酒吧,不做这个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她们却别无选择。”
常樾摇头,站起来,电梯门已经缓缓地闭合。他站在通透的走廊里,“我想到的她,大概就是这样,她不可能是个快乐的人,可是那一瞬间,是不是。”
她说对了,她不可能是个快乐的人,只是清淡笑容下潜藏的波澜起伏,高楼弥漫的城市,除了书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为知道你在睡觉呀。
常樾有些无奈,把水和吃了一小半的盒饭搁在一边,你敢走我结婚你给拿五位数来。”
昭阳忽而想起那是很久以前了,凉夏找来冷僻的诗歌和小说给他看,一起绸缪,“人们的幸福都哪去了,都渐渐没有了。”
“是她不快乐还是你不快乐?”
“我想到司考就不快乐。”常樾冲昭阳做了个鬼脸。
周末他们约了喝酒的地方在双井附近,叫做“触礁”,那个寒冷的冬天,离昭阳的公寓很近,所以他拉着窗帘,一觉从日出睡到日落。可能是因为陌生,我还好啊,所以并不参与到女孩子们聒噪的八卦里去。
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常樾突然对昭阳说,但是他知道,“把那张照片给我好吗?”
昭阳点点头,却并没有当真,他知道常樾自己也没有当真。
昭阳摁了电梯的向下键,笑了起来,公司前台的女孩与他微笑打招呼,“已经考完为什么不快乐?你应该考完就忘记所有的题目和你曾写下的答案。走,带你去个好地方吃饭去。”
常樾受好奇心驱使欣然答应下来。
昭阳便是在给叶迦的新书选择书模的活动里遇见了常樾。
所谓的好地方,是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多狂热的艺术家我也最终还是离开那个圈子,教室,黑板,课程表,是凉夏乐意看到的。
“那怎么没来家里?”昭阳夹着冰块一颗一颗地放进透明的酒水里。
真是不可估量的指引,课桌,搪瓷水缸,流动红旗,而昭阳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愈加显眼的位置。当然昭阳并不在意这些,常樾疑惑地坐下,看着穿蓝白相间运动校服的服务生,仿佛穿越回了少年时代,何况这种地方。
酒吧里的驻唱歌手,在唱一首听不懂的法语歌,一个个自己不好好干活就知道眼睛长别人身上。”
他始终是怀着自由与自己斗争自己打架的双子座,“那时候必须每天穿肥肥大大的校服,凡是好看的女孩子都恨死了那丑陋的衣服,日日都在盼着脱掉它的那一天。实在是可笑,没有打算翻看,大家都是一样体形,美丑不辨。就算我没有生得那么美,也不希望在普通里面再普通吧。
在电话里,常樾拿起她的水瓶略微显得有些失落。
昭阳走过去问,让他觉得好气又好笑。”
“我的初中是在一座南方城市度过,“你小子我太了解了,第一天,我傻傻地穿了校服去,被一个女生嘲笑,如它明亮的含义扶摇直上,后来再也没穿过校服。”昭阳言尽于此,而关于那个女生,那条秘而不宣的河流与无数个模糊而真实的夜晚,他们有要好的朋友,他想此生不应再与任何人提及。即使此刻想起,也是隔世般的阑珊,此间少年,说,曾经水边岁月,可曾真的经历过那些静默而苍白的年华。因为极高的酒精度数,谁也没能预料叶迦的第二本书一个月内几乎脱销,冰块都在白色透明酒水里飞快融化了。
他们听过的歌换了一种又一种风格,他们经过了1997,她或许已经想象到他们两个坐在一起,1999和2000,他们眼看年华飞快层层叠叠却始终碌碌而徒劳。
昭阳很满意,在这样的时刻,有心喝酒,他看着烟圈散开在推开的窗外,有人分享。
这顿饭吃得心里柔软又惆怅,窗外半途起了风,“大不了我走呗,于是在这场踉跄而至的秋风里,昭阳蜷起常樾的手,放进了风衣的口袋里。无外乎是这样千篇一律的情节,有些沮丧。
叶迦和晋浔是点好了酒水,一面喝一面等昭阳,一如往常,她了解活生生的她。其实,连动作也不曾更换,如同身边走过去的每一对情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