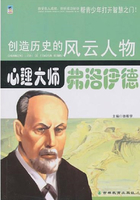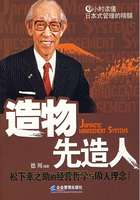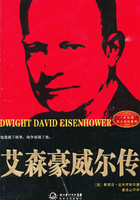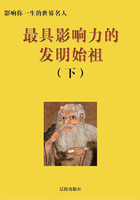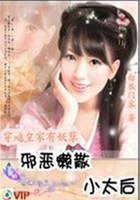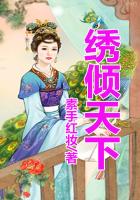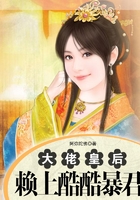一 美国的通才教育
上世纪60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发表题为《谈留美生活》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又回母校执教,因此他与清华的感情特别深厚。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筹备于1909年,起初叫“游美肄业馆”,附属于清政府外交部的“游美学务处”。1912年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以后,仍然归外交部管辖,成为中国教育系统之外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学校。清华学堂实行八年制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两个阶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毕业后派往美国留学。该校1922年起改行“四三一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学一年。1925年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变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的体制。1929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这所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归教育部管辖,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中国教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虽然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乱,但依然弦歌不断,成为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自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学校。潘光旦就是那时候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的。从此,他只有改造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尽管如此,仍然难逃”右派“厄运。我原来以为当时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儿潘乃穆说的那样,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没想到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仍然强调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这说明他不但没有放弃自由主义,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
多少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与它长期坚持通才教育有关。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美国校园文化》的小册子,其中对通才教育有所介绍。
该书作者亨利·罗索夫斯基,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该校文理学院担任院长达11年之久。他说:美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别重视通才教育。他还说,如果你进大学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张职业证书,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话,那就错了;因为“美国的四年大学生活对多数学生来说是接受通才教育的最好机会”。
罗索夫斯基认为,通才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教养的人。为此,他不但为学生安排了“与专业性或技术性课程不同的、以讲授全面知识和发展全面智能为目标的“课程设置,而且还对什么是“有教养的人”提出五条标准:
第一,有教养的人能够清晰准确地使用书面语言,并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第二,他们对宇宙和社会具有判断鉴别的能力,并且不乏自知之明。
第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第四,他们经常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并能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第五,他们在某些知识领域拥有较高的成就。
反之,倘若不能对学生实行通才教育,而是过早地对他们进行专业教育或者职业训练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不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一个缺乏鉴别能力和自知之明的人;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隘、才疏学浅的人;一个不懂得伦理观念、不讲道德的人;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人。
仔细阅读该书,并参看有关资料,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通才教育其实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政府制定了旨在创办农学院和工学院的《毛利法案》,但是主张实行通才教育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一位大学校长就对学生们说:“你们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还不如说是在批判的精神下进行思维活动。……进一所好的学校,最需要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艺术和习惯。”这其实是对专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最好批评。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受德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通才教育在美国有了长足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更是把通才教育视为制止战争的有效途径。战前,有识之士就明确指出:实行通才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谦虚、仁慈和幽默等美德。他们认为,由于谦虚要以知识为先决条件,仁慈是对人性的深刻尊重,幽默需要过人的智慧,所以通才教育对于猖獗一时的***主义是最有效的抵制;对于“把自己吹嘘成神仙,把他们浅薄的想法说成是神圣的启示”的独裁统治之流,是最有效的抵制;对于企图扼杀人性,以便让人民在国家机器中沦为工具和奴隶的阴谋,也是最有效的抵制。战后,一位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指出,通才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生活目标的文明化,情感反应的纯静化,……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他甚至说: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普通教育(即通才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肯定能够免除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陷于专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狭隘境地之时,人格的委琐、思想的委顿和精神的萎靡,恐怕就在所难免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这本书中我又进一步看到,通才教育是守护精神家园、影响社会进步的头等大事。
话说回来,上述潘光旦的话是1965年讲的。鉴于当时语境,他虽然不能直抒胸臆,但还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阐明了通才教育之必要。其实,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说这种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让青少年了解丰富的世界,体验多彩的人生,摆脱”机器“的命运,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潘先生是1967年去世的,可见让清华大学早日恢复通才教育传统,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无独有偶,到了1981年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的时候,也念念不忘通才教育的传统。他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应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始终在探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近年来,尽管我们对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大家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冯友兰这样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实行“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困扰。这就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继续。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传统,应该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二 通才教育的倡导者梅贻琦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
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底才被迫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实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我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33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也把“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同上,第52页)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4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1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同上,第24、25页)。近年来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同上,第52页)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
这种拉郎配式的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是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太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中主张。
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同上,第99页至第109页)难怪有人要说,这篇文章既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对当局“目光短浅”(朱自清语)的教育方针的公开发难。(《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第8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
“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他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