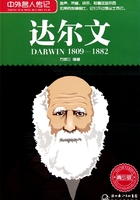悄悄深夜语,悠悠寒月辉。谁云少年别,流泪各沾衣。
府衙西边有一个几十亩宽的湖,湖里尽植莲荷。祈鉴向湖边走去,漱雪也跟了上去。乌云出月,倒映在粼粼的水波里,湖边呈现出一片金色。渡口横着一只小小的乌篷船,祈鉴迈步上去后转身向着漱雪伸出了扇子,漱雪轻扶住扇柄,轻身一跃便跳上了小船。
祈鉴打开绳索,小船顺着微风,慢悠悠地向着湖的远处飘去。可是夜晚就像一剂令人麻醉的药,让人忘记所有的成规。篷中相对坐下,祈鉴仰头望着天上明月,笑道:“我记得蘅冰曾经说过,有人见了天空皓月和湖中舟船后感叹月光虽好却失之遥遥,不如湖中舟楫热闹。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你还这么想吗?”
漱雪一愣,片刻后才模糊记起他所说的是宝元年间她在中秋宫宴那日说过的话。没想到他记性竟然这么好。
漱雪亦向那一轮明月望去,摇头道:“现在不了。如果可以拥有皎洁的月光,我宁愿不要这地面的热闹。”
篷中陈设简陋,只有一张旧木桌和两条长椅。祈鉴将酒放在桌上,挽起衣袖,竟然走到船头划起桨来。双桨激起阵阵水花,卷起荷塘里的水藻和荷叶的气息。小船渐渐穿破清凉而稀薄的空气,驶进细密的芦苇荡和荷叶丛,水道也越来越逼仄,甚至可以听到荷叶盖摩挲乌篷的声音。小船摇摇晃晃了一段路程,在荷花荡中央停下了。
这里是荷花中央一片水塘大小的空地。放眼望去是一片翠绿荷叶,红白荷花掩映其中。祈鉴从篷内的桌上提来那坛酒,在船头坐下。
祈鉴举起酒坛方才忆起没有酒杯酒碗。他环顾四周后欣然一笑,从身后采撷两瓣荷叶卷曲成酒杯,一盏留着,一盏递到漱雪手中。漱雪捧着手心精致而别出心裁的“酒杯”,不禁惊讶地笑了。夜晚、美酒,和一个青年男子独处,在漱雪的生命里都是第一次。但连日来郁积的情绪使她就像一个窒息的人渴望新鲜空气,早顾不得别的。
“雍王殿下,此情此景,你在想什么?”她朗声问他。
祈鉴转头看她,眼波清澈,一袭青衣便装也使她显得简单自然。“不要叫我雍王殿下,就叫我祈鉴吧!”他说着,又举起那坛酒,给漱雪的荷叶盅里斟满一杯。
“你的心情一定很坏。痛痛快快地喝下几杯,将烦恼都抛诸脑后吧!”他抬头看见漱雪的眼里有着疑惑,以为她在防备他,便又道,“放心喝吧,我不会动你的念头。”
认识祈鉴的人都知道他极善自律,他的话自然不假。只是漱雪却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变得轻松,她怔怔看着他片刻后,匆忙把目光避开,气氛似乎反而尴尬了。
“今后你打算怎么办?”祈鉴微微起身,单膝蹲在船舷,音调里带着一丝关切。
“我想成全他们。”漱雪侧脸看他,“我和子泫一起长大,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也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夫婿。即使知道他和玉安公主的事,我也只当那是他人生路上的一个岔口,兜转之后就会回来。没想到我错了,他并不是走上了岔路,而只是走上了他自己的路。”说罢,漱雪拂袖将荷叶里的那盅酒一饮而尽。
“那你的路呢?你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难道你真的愿意像天上的月亮,光亮却孤单地活着吗?如果解除婚约,你的名誉会受到影响,这对你而言是无辜的伤害。”
漱雪伸出手去,一束月光便照耀到她的手心。“其实天上的月亮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孤单,它有着很大很大的世界。”她仰头看祈鉴,嘴角露出一丝坦率的笑容,“或许我以后可以好好照顾梅家,继续学习医术,那样的生活也未必就比我嫁给子泫差很多,对不对?”
祈鉴听罢并不说话,只仰头喝酒。半坛酒下肚,原本束缚的思绪渐渐打散了。“你需要一个依靠,不过却不应该是高子泫,他配不上你。”扔开酒坛,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值得更好的。”
“会有吗?”漱雪凄然一笑。
祈鉴确定地点了点头,“当然会。我若是世间的那些男人,一定会感激高子泫喜欢的不是你。”
一句“我若是世间的那些男人”令漱雪的面庞顷刻飞红。不过,难道他与世间的那些男人有什么不同吗?
正当她恍惚时,不知从哪里跳出一只青蛙,漱雪失声惊叫,祈鉴慌忙扔开两只桨过来拉她。她虽没有跌倒,两只桨却倏地滑落,在水面留下的几个水圈儿。
“怎么办?”漱雪掩口惊呼,“我们没办法回到岸边了!”
祈鉴枕着手,悠闲地向着船头一靠。终于见到沉稳的梅家大小姐惊慌失措的模样,他心里得意极了。“没有办法,只有待到天亮,等附近的农人来救命咯!”他漫不经心地摊摊手。
漱雪沿着船舷张望了一番,又用荷叶梗试探了一下水深,发现捞桨和涉水都无望,便泄气地蜷坐回船舱内。漫漫长夜该如何度过呢?她有些沮丧地看着祈鉴。祈鉴却丝毫不担心,头一偏,又分别为她和自己斟满了两杯酒。乌云四散,月亮升到了空中,小船四周的水塘和荷叶都沐浴着银白色的月光,影影绰绰,似有一番仙境般的朦胧。
“你在想什么?”漱雪看着他问。
祈鉴放下酒坛,语气沉郁而平静,“我想到了张若虚的两句诗: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这样抒情的诗,实在和一向冷静果断的他不相称。祈鉴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常,顿了顿正要岔开话题,漱雪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祈鉴,除了苗妃和福康公主,你还有过别的在乎的人吗?”
祈鉴仿若被闪电击中般,提着酒坛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那位女子的身影如一抹彩虹在脑海晃过,他的眼里顿时闪耀着一丝亮光。但那道光转瞬即逝,随后又是惯常的淡漠。他转身将那酒坛按到水里,湖水便咕咚咕咚装满了空空的酒坛。祈鉴的手突然抬起,酒坛咚的一声便沉入了湖底。
“心若因为盛满东西而变得沉重,放手就是最好的解脱。”他拍了拍手上的水珠。
漱雪震惊地看着他轻描淡写的神情,“若是不能放手呢?”
“那就牢牢握住,死也不放开。”祈鉴的目光投向远处的山山水水,无比认真地说,“这世界上于我而言,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有一样。握住了它,别的就都不重要了。”
乌云遮月,四周突然暗了下来,漱雪再也看不清他的表情。祈鉴见状便起身在篷内找来一盏油灯,几次欲用火折子点燃,却都被风吹灭了。漱雪走过来,背对着船头,双手拢着那半盏油灯,火苗很快跳跃起来。惊讶于她的聪明,祈鉴抬眼看她,却在这一片火光中看到一张举世无双的美丽面庞,柔软的发丝轻轻垂下,淡淡娥眉点缀在明净的眼眸上,樱红的嘴唇如弯弯的月亮……
留意到他的目光,漱雪抬眼看他,他的目光灼热,如同手中的火石,所到之处皆燃成灰烬,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漱雪悄无痕迹地后退一步,伸手抵着额头望一眼天空说:“像是要下雨了!”
祈鉴的目光仍在她身上,烛光也映红了他的脸。顿了顿,他说:“那就进船舱来吧!”
他说这话时,雨点已经落下来了。漱雪走进船舱将油灯放下,任凭火苗在风中忽明忽灭。和祈鉴相对而坐,她却不敢看他。跟他出来本就有些突兀,却又碰上了这样的鬼天气,一切都太糟糕。此刻她只盼着雨快停,天快明。偏偏天不遂人愿,风声越来越急,乌篷船被吹得东倒西歪,在荷塘中央转起圈儿来。祈鉴头上的竹篷破了个洞,吧嗒吧嗒漏水。他却不躲不避,任那雨水淋湿了他一身。许久后漱雪终于咬咬牙说:“你也坐过来吧!”
祈鉴的表情有片刻的停顿,似在体味她的情绪。踟蹰后他起身走过来,与她坐在同一张板凳上,两人之间便只有一只衣袖的距离。冷风灌进来,两人的衣襟都被风吹得鼓鼓的。见漱雪抱紧了双臂,祈鉴褪下披风将她裹紧,双手环绕过她的双肩时,两人的气息皆在彼此间萦绕。
祈鉴的目光落在她的耳垂上,陡然想起什么,双手缩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只银白色的珍珠耳坠。
漱雪错愕地看着他。这是她当日忘记从轿子上带走的那只耳坠,没想到他竟然碰巧带在身上。恍惚中,祈鉴已经轻轻将那只耳坠放在她手中,温暖的指尖在她掌心留下一丝缥缈的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