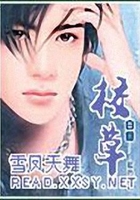嬴女去秦宫,琼箫生碧空。浊世不久住,清都路何穷。
夜里天气并不燥热,玉安坐在窗前,园中的昙花散发出阵阵清香。她手托下巴,静静地等待着窗棂上的月亮藏到那一片浅蓝色的云彩后头去。
有人轻声叩门。笙平开门后发现来人竟然是漱雪。玉安诧异地吩咐笙平备茶,便迎她在床榻边坐下。这么多年来,因为子泫的关系,她们俩对彼此早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却从来没有这样单独聚过。
“梅姑娘怎么有雅兴来这边坐坐?”玉安问道。
漱雪从笙平手中接过茶,却放在了一侧,似忧心忡忡,“我刚刚去看过子泫,他下午应付城外流民时受了伤。”
玉安一惊,“伤得重吗?”
“一乍长的口子,我刚刚为他包扎过了,休息几日便没有大碍。”
“那他试药岂不是有危险?”玉安的心立刻提了起来。
漱雪点点头,“下午子泫突然回来,让大家措手不及,没顾得上细想便答应了他。但如今他身上有刀伤,再让他试药我便没了把握。”
“雍王和荆王知不知道这件事?”
漱雪点点头,“就是他们让我来找你的。子泫受伤不能试药,而现在试药的人里亦没有女子,也怕难以服众。试药的目的是为了向百姓证明这不是毒药。公主先前威服豪强,为百姓赢得了粮食,百姓们也定然愿意相信公主。”
她说的话不无道理。玉安听罢,嘴角却挂着一抹笑意,“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相信你?”
“公主若愿意试药,漱雪愿意签生死状。公主若有任何意外,漱雪自愿领死。”说罢,漱雪从袖中掏出一份帛书递到她手中。
玉安缓缓展开帛书,笔迹娟秀里透出的勇气让玉安暗生佩服。玉安沉默片刻后却将帛书还给了漱雪。迎上漱雪诧异的脸,她缓缓道:“比起生死状,我更相信漱雪姑娘的自尊心。不过我曾经答应过子泫再也不让他担心,所以我必须先说服他。”
自从上次借粮后,子泫一直杯弓蛇影,时刻看着她,生怕她再出任何状况。如今别说可能昏迷两三天,就算是头痛发热,他也断然不会同意的。漱雪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点了点头。自己的未来夫婿如此记挂另一个女子,她的眼底闪过一抹难以言说的尴尬。
“他草木皆兵,一定不会让你去……不过他也不会阻止你的……”漱雪深吸一口气,道出了实情,“子泫的伤口疼痛,为他处理伤口前我便让他服下了山茄花和火麻花末麻醉,明天未时前后才会醒来。”
玉兔东移,清风徐徐,满园花香。玉安轻轻推开子泫的房门,见他躺在床榻上已沉沉睡去。胳膊上的纱布渗着点点猩红的血迹。玉安打开茜纱窗将凉风放进来后在他的床头坐下,用衣袖拭去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熟睡的子泫的眉头依然微微蹙着,似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听笙平说,曾经的他天真中带着一丝狡黠,一皱鼻子就能讲很多趣事和笑话。可是自从认识了她,他便像一根拔节的竹子,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十八岁的少年,眼里却已经有了历经岁月的人才会有的持重。
难道她的爱,竟会使他变得沧桑吗?
“子泫,”她的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为了你,我会努力像漱雪那样过得简单快乐,把他们所说的那个无忧无虑的你找回来……”纤柔的手指缓缓抚过他受伤的胳膊,她颤抖着俯下身,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
翌日晌午,热辣辣的太阳像要把地面烤化,城西戏台前却人山人海。远远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大家议论着,期待着。木材、药材堆积如山,大锅也已经烧了起来。屋檐下的阴凉处,祈鉴、祈钧、玉安、知州和诸位医官依次就座。
烈日中天。漱雪和几位药官戴着斗笠和面纱,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前分拣药材。百姓们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奇怪的药材被他们麻利地拣出,磨碎,放进沸腾的锅里。
大锅汩汩地冒着热气。从配药到熬药乃至盛药,一切都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张医官禀告药已煎好,试药可以开始。同时医官、药官和府衙的差官已经齐备,待众人试药之后,便将第一批药分发给有病征的人们。
祈鉴点点头,从玉安手中接过尚方宝剑后,走到戏台的前端。
“各位乡亲,这把剑是当今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今天,本王在此兑现对乡亲们的诺言,我、荆王、玉安公主,还有你们的父母官储大人将为大家试药!如果乡亲们信得过朝廷,信得过我们几个,待我们试药后也须遵守约定,服从官府指令,共同对抗疫症!”
尚方宝剑在阳光下金光闪闪,众人啧啧惊叹,纷纷凑了过来。
人群里有人高声问:“玉安公主可是前些日子从赵老爷家借来粮食的公主?”
还有人在问:“我听说玉安公主懂得法术,能用一百个士兵变出一千个士兵,可有此事?”
见百姓将玉安说得近乎神仙,台上的人都哈哈笑了。知州作为这一带的父母官,一向清廉有望,见状也站起来说:“玉安公主是官家的女儿,也就是真命天女。真命天女撒豆成兵,点石成金,都没什么奇怪的!”
台下立即响起一片笑声。
祈鉴转身踱步回来,和祈钓、玉安等交换眼神,他们便从屋檐下走出来,从药官手中接过刚刚从药锅里盛起的药。药的酸味和苦味立刻扑鼻而来。众人各自一饮而尽,心中似有热浪升腾。
“乡亲们,”大家展示着手中的空碗,祈鉴道,“现在大家可以相信医官,相信朝廷了吗?病患们的病情刻不容缓,请大家配合官府和医官,尽快为你们的亲人诊治!”
台下的百姓窃窃私语一番后便立刻有人带着一位老人向戏台挤过来,“大人,快救救我的父亲……”
差官立刻帮助来人将老人抬上戏台。医官望闻问切后确诊为瘟疫,便即刻让他服药。其他人见试药人和老人都安然无恙,而药锅里的药却是有限的,便争先恐后地拥挤过来,吵着嚷着要喝药治病。
“先给我吧!我身上的红斑已经两天了!”
“先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已经快不行了……”
知州大人一边示意差官维持秩序,一边道:“大家不要着急,今后每天我们都会在农庄为病患熬药;医官们也将在府衙前设诊。这场瘟疫很快就会过去的!”
焦虑的百姓很快在差官们的组织下排成两队。祈钧见此,欣喜一笑,走到祈鉴和玉安身边道:“玉安妹妹真是神机妙算。这一对父子一带头,百姓们便都热情高涨,唯恐落后了!”
玉安望着涌动的人群,笑道:“这多亏了二哥哥对百姓情绪节奏的准确把握,否则也未见得有这样好的效果。”
见大家都安然无恙,祈鉴如释重负地拍了拍祈钧和玉安的肩膀道:“这次治水多亏了你们。”
玉安笑着摇摇头,指着不远处的漱雪道:“论起来,漱雪才是立了头功。”
祈鉴欣慰地望着漱雪的背影。眼前的一切,也算是对得起她日夜的辛苦了。他无限感慨地叹道:“咱们又能说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呢?即使是未能前来的子泫,付出的心血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尽的?只是子泫醒来后若知道我们给他下了昏睡药,不知道会不会生气呢!”
祈钧看着玉安笑道:“子泫原本就是杞人忧天。现在玉安完完整整地站在这里,他自然也就没话可说了!”
赶回府邸已是下午。漱雪和玉安、祈鉴、祈钧一起前去看望子泫,医官和郎中则在知州的安排下分成两队,一队前往农庄,一队在府邸前为病患诊治。
几个人进府衙后苑时,子泫刚好冲出来和漱雪撞了个满怀,子泫连忙抓住她问道:“玉安呢,她怎么样了?她在哪里?”
漱雪正被他问得不知所措时,玉安已推门进来了。见她安然无恙地站在眼前,子泫原本焦虑的脸上有了愠色,哼了一声便转身回房去了。
祈鉴和祈钧连忙跟上去道:“子泫,你就消消气吧!这都是我们的主意。你看,现在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子泫瞪了他们二人一眼,火气已消了许多。但当他的目光遇上玉安后便迅速移开了,不肯与她说话。玉安知道他是气她参与他们的骗局,忙哄他道:“我瞒着你是我不对,不过你受了伤也不告诉我,我们算不算是扯平了?”
子泫更生气了,“这怎么能一样呢?你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玉安歪了歪头,在他跟前蹲下道:“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很少见到玉安这般俏皮的模样,子泫气消了大半,这才肯正眼看她一眼,“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一切都很顺利。见我们喝了药一点问题也没有后,百姓们肯喝药了,医官们正在外面忙活呢!”玉安心疼地看着他的伤口,“目前最不好的怕就是你了,快让漱雪再好好给你看一看吧!”
子泫看了看漱雪,说:“那就劳烦漱雪妹妹了。”
漱雪静静地在他跟前坐下,一圈一圈退去他胳膊上的纱布后,触目惊心的刀伤便裸露出来,一乍长的口子,血肉模糊。虽然漱雪的动作很轻,子泫还是满头大汗,想必疼得钻心。
玉安将整个过程看在眼里,她只觉得心像在被钝刀凌迟一般疼痛,到了后来,那种疼痛的感觉慢慢变了,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被大锅烹煮,腾腾的热浪在胸腔弥散,她快不能呼吸了。
笙平不经意地一瞥,见玉安的眼神越来越迷离,急切地问:“公主,你怎么了?”
她的话音未落,玉安便向后倒下,祈鉴疾步扶住她。中暑、中毒……祈鉴率想到了各种可能的情况,立刻吩咐人关上了房门。
子泫见状也顾不上胳膊上的伤了,一把推开漱雪的手便扑到床前,声音也因担忧而颤抖起来,“玉安,玉安,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祈钧连忙劝子泫道:“子泫,你别着急,漱雪之前就说了,健康人服药后都会有两三个时辰,甚至两三天的异常反应,这都是正常的……”
但他的话子泫一个字也听不进去,直觉的恐惧包围了他。一旁的漱雪更是比谁都担忧,因为玉安的脸色正由红色慢慢变成暗青,这并不是她所预计的排异反应,而像是引发了某种病症。此时此刻,她也顾不得多想,只能劝子泫道:“让我来替她看看吧!”
漱雪接过玉安的右手诊脉。大家都焦虑地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却见漱雪眉头越锁越紧,脸色越来越坏。
“怎么样了?”祈鉴小心翼翼地探问。
漱雪放下玉安的手,起身道:“公主的体内似有冷热两股气流在窜动,脉象沉涩且瞬息变幻,令人捉摸不透。”她双手抵着额头,愁眉深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脉象,就连医书里也没有记载这样的病例。”
众人的心顿时凉了半截。祈鉴沉着音调问:“你是说,这……这药方有问题吗?”
漱雪摇摇头,“公主的症状虽因汤药而起,但并不见得是汤药的问题,而是和她的体质有关。”
正在这时,子泫见玉安已经满头大汗,眉头紧锁似越来越痛苦,他的心仿佛被撕成碎片,却无计可施,只能一声声疯狂地呼唤:“玉安,玉安!”
天黑时分,外面服过药的人仅有个别人有排异反应,大多数人的症状都减轻了,而屋内的玉安却因发热陷入了昏迷。
众人皆为玉安而担忧,最为难过的要数漱雪了。
子泫虽然心忧如焚,却未失去理智,他走到漱雪的身边安慰她道:“治病的方子不是一时想出来的。你累了一天了,先回去休息吧!”
漱雪抬眼看他。此刻的他,双目无光,憔悴得不成人形。平日里遇到玉安的事,为了顾全她的心情,他多少会有些掩饰,而此刻他连掩饰的力气也没有了。
漱雪“嗯”了一声便向房门外走去。满天星斗,繁乱得如同她此刻的心情。一路小跑到一棵梧桐树下,她终于再也无法压抑,额头抵着树干,泪水疯狂滚落。
她不过是想安安稳稳地治病救人,可是如今却因轻信自己的医术而犯下了错误,玉安若有了差错,不但她活不成了,子泫怕是也活不成了。
她的肩膀不停抽搐着,直到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响起。漱雪知道此刻泪水已经弄花了面庞,也不转身,只幽幽地问了声:“谁?”
“是我。”来人并没有报他的名字,但她听出了他的声音。那声音平日如洪钟般低沉,此刻却带着鼓励和包容的意味,“玉安的事是意外,你别太难过。你必须冷静下来,才能想办法救她。”
“我救不了她,”她的声音战栗着,“她会死的!子泫一定会杀了我的!”
“看你现在的样子,在他杀了你之前,你已经把自己杀死了。医者本就行走在刀尖上,翻手即生,覆手即死。我若是你,就会想此刻的玉安是多么好的病例。”
漱雪简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玉安生死未卜,他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她转过头来,狼狈地收拾好凌乱的发丝,止住眼泪。但那长长的睫毛上仍旧沾满了泪水,因此他的脸在她眼底,也是模糊的。
“你一点儿也不担心她?”
“怎么担心?”祈鉴不以为然地回答她,“像你一样?还是像子泫一样?你们个个六神无主,总得有人脑子清醒点儿吧?”他漫步行至她跟前,仰面一笑,“我若也像你们这样放任自己的感情,只怕我的心早就碎了。这瘟疫前所未有,你不也找到药方了吗?再怪的病症,我相信你也能够找到办法的。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尽管开口。”说完他转身要走。
漱雪擦干了眼泪,张口叫住了他,“喂!我想查看一下《脉经》和《本草经集注》。”
“当然没问题。”祈鉴停下脚步,点点头道,“我们这就去找知州。”
州府里并没有这类医书,他们必须去六七里外的黄员外家里找。这个黄员外的祖父曾是有名的郎中,留下了不少的财富和医书。自己子孙都不学医,那些书便束之高阁。祈鉴见天色已晚,便决定陪漱雪前去。翻身上马后,见漱雪还在下面愣着,他轻笑道:“怎么,还想走过去?”说完便向着她伸出一只手。
漱雪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和男子同乘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将手搭了过去,他一用力,她便飞身上马。策马扬鞭,枣红马向着城门外的苍茫夜色绝尘而去。被祈鉴唤作“星辰”的马是来自西域的良驹,有一日千里的本事。耳畔风声呼啸,混杂着祈鉴的呼吸声,漱雪只觉得心里有如万马奔腾,连日的紧张逐渐释放,恍若展翅待飞的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