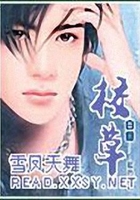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
每月初五,是各殿阁领取月俸的日子,玉安和梅岭海见面那日恰是初五。趁着人多事杂,徐嬷嬷将一包首饰交给侄女金莲,让她通过自己的门道偷运出宫卖掉。徐嬷嬷走后,金莲正要离开,却见到了玉叶桥畔的玉安和梅医官。
金莲在宫中多年,并不敢乱议论是非。但徐嬷嬷给她的那包首饰还未来得及转手便被璎珞发现了。璎珞一口咬定是她偷的,要送她到皇城司问罪,她情急之下便谎称是在破屋附近捡的,还说出玉安可以作证。
璎珞抓住了玉安的把柄,比谁都要兴奋。一阵毒打,金莲把听到的一切都招了。为了避免私运宫物的事情被揭发,金莲只得按照璎珞的吩咐,哆哆嗦嗦地向皇后禀告说玉安指使梅医官谋害杨美人,梅医官良心不安才畏罪自杀的。
这件事关系两条人命,还涉及玉安和梅家,皇后的震惊可想而知。黄昏时分,皇后传唤玉安问话。铜炉中石炭通红,殿阁内温暖如春,皇后端坐在云椅上,高高的凤凰髻流露出一派庄严。
“玉安,今天我不是皇后,你也不是公主,你就只当我们是可以说说贴心话的寻常母女罢了。你年纪尚轻,若是被人利用误入歧途,只要诚心悔改,我也可以保你无虞。杨美人之死你究竟知情不知情?”
“杨美人死于风寒,娘娘早有定论了。玉安确实和梅医官在玉叶桥巧遇,但这件事情和杨美人的死扯不上半点关系。想必是宫内人见我受娘娘恩德,因妒忌而搬弄是非,娘娘明察。”
玉安的分析合情合理。虽然璎珞和金莲言之凿凿,但皇后也知道,如果梅医官想杀害杨美人腹中的胎儿,根本不需要和玉安合谋。
皇后的心里开始打鼓。这时,玉箫匆匆来传:“娘娘,闵淑仪、宝康公主,还有好几位娘子都在殿外求见,说是杨美人和梅医官的死有蹊跷,要求娘娘公开彻查。”
皇后玉手拍案,怒不可遏,“她们是担心我不能秉公办理吗?”
闵淑仪、璎珞和另外几位娘子进殿来了。为了预防皇后偏袒玉安,这两天璎珞已经令人将这件事四处传播。
皇后赐座后,满脸怒容地道:“杨美人的死医官局早有定论,你们今天来兴师问罪,是要造反吗?”
列位虽心里不服,也连忙诚惶诚恐地称不敢。还是璎珞试探着问:“既然证据确凿,娘娘至少应该重新彻查,以免去娘子们的忧虑。否则如果宫里有人想谋杀妃嫔,岂不是人人自危?”闵淑仪和其他几位妃嫔都连声附和。
他们句句有理,皇后一甩衣袖,道:“你们一口咬定杨美人的死另有原因,那倒是说说,玉安为什么要谋害杨美人?”
几位妃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吞吞吐吐,面露难色。
皇后恍然明白,不单是梅妃,连她自己也在她们的怀疑对象之中。
正在这时,延春阁差海棠在外面等候通传。海棠一进来便哭着跪倒在地,“启禀娘娘,尚美人小产了,症状和杨美人一模一样!”
这个消息无疑是杨美人死于谋杀的铁证。皇后和几位娘子都大惊失色。
“人救过来没有?”皇后关切地问。
“丁医官救了一个时辰,总算醒过来了!”
皇后一巴掌打得海棠晕头转向,“该死的奴婢,竟然耽误了一个时辰才来报告!”说罢,她便着玉箫即刻摆驾延春阁。几位娘子和璎珞慌忙跟在身后。
跨过门槛时,皇后突然停住脚步。她回头看着玉安,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即刻起,玉安公主禁足霁月阁。没有我的懿旨,任何人不得近身!”
尚美人小产后身体虚弱,情绪也不好。皇后再次责令医官局彻查,医官很快从药渣中查出了紫蚕花。大理寺迅速介入,很快在玉叶桥附近的枯井中找到那两方手帕。前夜有雨,手帕里的药物已被冲散,查验不出成分,但这已经足以使玉安成为头号嫌犯。
这天清早,便有人来霁月阁带人了。宫眷及内侍犯罪,本应羁押在皇城司的狱中。玉安见来人竟然身着御史台狱的官服,便知这是皇后的授意。她如果被认定为嫌犯,梅妃和皇后就成了重点怀疑对象。为了撇清和此事的关系,皇后便先行了这一步。
玉安起身跟他们走。行至柔仪殿大门,皇后和玉箫正站在路的中央等候她。“去吧!随后我会命人给你们置备衣物和棉被的。这一切只是依例行事,御史台的大人会明察的。”皇后说。
玉安欠身行礼道:“天气苦寒,娘娘早点回屋歇息吧!”说罢,她便带着笙平,跟随御史台的侍丛迈出了大门。
等她们渐行渐远,皇后还停留在原地,叹息道:“遭此变故还能不动声色,她要是本宫的亲生女儿该多好。”
玉箫提醒道:“娘娘,现在不是动情的时候。试想如果玉安公主一口咬定这事和梅妃无关,御史台又找不到别的怀疑对象,您该如何全身而退?”
她一语说中了皇后的心事。宫廷的形势向来瞬息万变,一不留神,便可能从天堂摔到地狱。如果发展到那一步,她必须把一切责任都往梅妃那边推。沉吟片刻后她说:“替我传雍王来见。”
如今祈鉴监国,又是与祈钧争夺皇位的唯一对象,是她最好的盟友。
御史台官署里,御史中丞王拱辰奉命亲自查办此案。王拱辰之名气,朝野可谓无人不知。十三年前,十七岁的他是国朝最年轻的状元,容貌俊逸,为官刚直,一直深得赵祯信任。但他进言罢夏竦、贬滕宗谅,朝中亦有说他是见风使舵的小人的议论。
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玉安决定保持沉默。在幕后黑手露出马脚前,她必须尽量拖延时间。
“玉安公主,现在铁证如山。你若如实说出谋害杨、尚两位美人的动机和幕后主使者,依据大宋律法尚可以从轻处理;如果执迷不悟,所有罪行都将由你担当,你的麻烦就大了。”
玉安轻笑道:“玉安听不懂王中丞的话。您若真心想尽快破案,就应当调查杨、尚二位美人的医官随侍,又何必南辕北辙?”
王拱辰亦笑道:“禀公主,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您这样分辩是无益的。”
“所谓物证不过是我遗落的一方手绢;所谓人证也不过清景殿的梳头宫女。既然宝康公主的侍女是最关键的证人,中丞何不将她传来与我对质?”
王拱辰轻笑,“公主所说的手绢可是粘着药渣的证物。至于人证,闵娘子早上准了金莲去东市买东西,下午御史便会传她前来和公主对质。”
玉安轻哼,长袖轻拂后便坐下喝茶,不再发一言。王拱辰便道:“既然公主无话可说,就先行下去歇息吧!等金莲带到了,本官再向公主请教。”
玉安便按照他所说的“下去歇息”。因目前的证据算不上铁证,皇后特地吩咐不能将玉安收监,而是将她们拘禁在台院西边最僻静的院落中。这里陈设简陋却整洁干净,棉被冬衣都已备齐,铜炉中的石炭也燃得正旺。
万物萧索,寒风呼啸,主仆两人深锁庭院,实在有些凄凉。玉安双手托着下巴沉思,笙平则用火钳拨弄着炭火。
“公主,我们该怎么办?”笙平担忧地问。
玉安苦笑,“宫里的利益纠葛本就错综复杂如蜘蛛网,我只不过是坏运气的小飞虫,恰好撞到了这张网中。”她环顾四周,瞥见帐幔后的八仙桌上陈列着供书写供词的笔墨纸砚,欣然一笑便拉着笙平为她磨墨。
笙平懵懂地看着她在纸上下笔如飞,不到一炷香时间便画出了一幅“以、像、四、时”四格完整的叶子戏牌。这叶子戏是老少皆宜的游戏,以前梅妃和其他妃嫔玩时,偶尔会让笙平替她,因此她也略懂一二。
“和我玩一把叶子戏,如何?”她抬眼问笙平。
笙平叹气道:“两个人怎么玩呢?何况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可没有玩游戏的心情。”
玉安笑道:“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什么时候玩,又有什么分别呢?”说完,她自顾自地抓起两张牌来。
笙平懵懂地接过两张牌,方才发现每张牌上都画着花草暗喻各殿阁妃嫔,而这四格亦越看越像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玉安在火炉边坐下,一扬手中的纸牌,“平时只见闵娘子喜欢玩牌,要知道宫里上头的官家和娘娘,中间的诸娘子,下头的内人内侍,玩牌高手多着呢!平时牌桌上我们这些看牌的人都心如明镜,难道自己入了局,便一下子糊涂了?”
笙平终于会了意,便和她一张一张地摊开算起来。
皇后的牌很快被抽出来了。太子新亡,宫中鼎足之势正是皇后所期待的,她不可能对皇子痛下杀手。
祈鉴奉旨监国,是离太子宝座最近的人,杀害尚未出生的皇子实属犯险。
闵淑仪虽可能与二位美人争宠,但清景殿的人从头至尾没有接近过两位美人半步,何况玉安认定她的智慧不足以想出如此诡谲的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