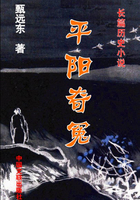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当然不是,人的恶性就是那么存在着,那种恶性欲望在寻求场所发泄,而你给出这个场所来,你就是帮凶,是刽子手!”林宇愤怒地撑起身体,一扭头,气鼓鼓地坐回到墙边的椅子上。
“我问你,那些恶终归是要发泄出来的,如果没了场所,他们那些恶会衍生在哪里呢?”郑叔这话让林宇惊颤了一下,这他倒的确没有想过,他沉默着,找不到话辩驳反击,大脑却在飞速地运转着,他确实不知道该让那些东西在哪里宣泄为好。“不错,到那时候,那些人会在更宽广的外面恃强凌弱,欺男霸女,勾搭姘夫,那外面是更宽广无边的世界,是西界下面那小小世界的不知道多少倍,到那个时候,这凡世间的无数不平,无数怨愤之事你如何才能收拾得了,难道就是耸耸肩膀,高喊爱莫能助吗?”郑叔的话让林宇哑口无言,他已经无可辩驳了,此时的郑叔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林宇只是一个无知的学生,伟大的哲学家措辞极其温和平缓,可林宇听到的却是惊涛拍岸,雪卷千堆,他感受到郑叔平静外表下一个极其活跃的灵魂,正在和他的浅薄无知发生着强有力的碰撞,“我建造了那个奢华的糜烂之所,可是在我看来那里就是一个监狱,可别人都称呼那里是天堂,这里的一切都是自愿的,那里出卖肉体的女人也都是自甘堕落,我曾经给我她们无数次的机会让她们自己创造生活,有些人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们多有悲惨的人生,有人给她们崭新的开始,她们就牢牢抓住,但是,在这个时代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救赎,那里剩下的女人都是自愿在那里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她们并不是可怜虫,愿意洗涤灵魂的早已经被我救赎出去,我不可能每一个都救赎,我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财力,更没有卞福汝主教那样伟大的灵魂。这里沉沦的赌徒,嫖客,酒鬼都是自甘沉沦的,我给他们最大的赌注,最美丽的风流女人,最名贵的烈酒,我建造这个监狱囚禁他们,他们竟然也渐渐地爱上这座牢笼,并且交口称赞,呼朋引伴,资源得被锁进来,你可知道这可以避免他们到外面祸害多少人?”原本,这些话本应该慷慨激昂的从一个愤怒而不理智的小青年口中读出来,但郑叔平和沉稳的声音给林宇造成的强大冲击是远远高于前个的,他听到了惊雷,听到了宇宙间的轰鸣。他不禁埋怨起自己来,甚至讽刺自己的无知,渺小和浅薄,虽然他并不赞成郑叔的做法,但是他由抵制变成了理解最后深深钦佩起来。
“你认为我的做法是善是恶?”
“我不知道,有恶的感觉,但却怀着善念,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林宇不知道该怎么讲了,郑叔的一席话给了他很深刻的反思。
“我自己有时候也在思考,自己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可是苦苦思索,总是没有结果。”
“您的行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我知道,您这个人是善的。”
“哦--”,郑叔这个字音拖得很长,“你这么认为?”
“是的。”
事实可以看出来郑泽世的确算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仁义君子,那个西界湖底下的豪华会所每周可以给他带来一千多万的纯利润。可是当初建造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建造成本,装修成本累计花费了他三十个亿的积蓄,这里面的一切服务,设备,食品,烟草,名酒加起来又得价值十几个亿,这里近五十亿仅仅是建造和装饰会所的价钱,但是还有很多价钱我们并没有提到,比如说这里会所上面原本也是树林,郑泽世把目光放在这片幽静的西界树林中,出了高价买下这块地皮,动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砍树,挖坑,建造,最后再往里面灌水,形成很大的一个人造湖,他还花了巨款入股西界高中才有了这个权利,他个人也是西界最大的股东。可是建造到完工他所有的花费接近七十个亿,这样算来郑叔需要十几年才能开始盈利,这世上有几个商人会花巨资等待十几年后的利润呢?这样违背商人本质的亏本生意只有郑泽世做了,并不是出于商人的身份,而是出于他日复一日忧世伤生思索得来的硕果,他完全没有打算在这项工程中赚钱,甚至根本没有在乎自己在里面会赔掉多少,他只是凭着良心,良知在做事,一丝不苟。每周一千多万的利润,他几乎会拿出一半来去救济社会,他干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自己一直是那么低调沉稳一个人,怪不得林宇经常在家见不到郑叔,原来他并不光光是公司有事,更有更加伟大和神圣的事情等待他去做。前面我们说到愿意得到救赎和解放的女人,郑叔都给了她们机会,他把她们送到自己工厂,亲自写推荐信介绍女人到她们自己感兴趣的单位,他每月会定时汇小笔款项到那些女人的卡上,改善她们的生活,他自己也修建了孤儿院和敬老院,除了他自己,很多社会名流,商贾也会给这些地方捐款捐物,他把账目公开到人人皆知,这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组织的袒露,而是一个干净的灵魂对自己的坦白。他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社会上的老弱病残,这么多年的努力以及他日日夜夜的忧思让他变得更加消瘦和衰老了,白发总在一夜后就又多出来不少,这是一个愚鲁的智者,一个留恋尘世的教徒。可是他的这些善行从不让人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慈善家,主持人也好,演员也好,商人也好,作家也好,统统都是爱慕虚荣的皮囊,人人都喜欢打着慈善的幌子来展现自己的良心,这种展现本身就是一种丑陋。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就和当官的到处做作,到处乱搞PS一样,他们都喜欢上了PS,喜欢PS各种对他们有利的称谓,于是我们可敬可爱的屎壳郎大军又出现了,他们在比粪球的长度,一样长,他们再比谁的宽,宽也一样,他们再比谁的臭。郑叔做了什么呢?这个真正的超越神只存在的凡人,他曾经独自一人背着一大包急需药品攀爬大山把这些送给几千米高峰上被人类遗忘的人们,那些慈善家呢?他们不会来,因为轿车开不了这样的路,直升机找不到停机坪,他们慈善家某某某的条幅挂不起来,因为那里穷得连木头桩子也没有,更何况那些人也还不认识字,最最最关键的是什么?没有记者,没有报道,他们怎么乐意干这费搬山之力却连一根毛都讨要不得的善事?这群蠢货有钱,好吧,他们去捐钱,捐的钱不知道流到了哪里,一层层的盘剥,变成了某些人的包,变成了某些人的表,变成了某些人的车,变成了某些人的洋房,变成了某些被包养的大奶子的女人。慈善家有了慈善的名声,他们唯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说他们毫无损失,收钱的机构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票票,他们乐呵呵地和慈善家们相互吹捧,自吹自擂。真正得益的是他们这两个蠢货,最惨的莫过于那些被慈善的对象,他们在人格上已经被侮辱了一次,现在他们又被利用了一次,成了那些贱货提高声望的垫脚石,别人会问:“你们接受慈善后生活怎么样啊?”
“我们什么也没收到。”
“住嘴,下贱坯子,得了好处还卖乖是吗?”
“我们真没收到。”
“去你妈的,这段掐了别播。”
郑叔在笑,笑这些下贱的人。
林宇不能发一言,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拜倒在一个伟大又清寂的灵魂面前,他为自己先前所说的一切而忏悔自责。
“对不起!”
“以后你接管了我的事业,这些都需要你继承的。”
林宇离开书房,关上门,再回到院子锁好铁门,关上厅门,悄悄地上楼。他这一次同样是轻轻的,但并不是做贼的感觉,他更像是怕打扰到素净单纯的灵魂。这其间,他思考了很多,他很佩服郑叔,以后肯定还会知道他越来越多的事迹,“多崇高的灵魂啊!”他自言自语道,此刻他心里这样想:郑叔一生勤俭,要不这么富庶的家庭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如何连空调暖气都不曾开。接着,他又转念一想,突然间被某个一闪而过的意识击溃了,心里酸溜溜的--这屋子里哪里装了空调暖气?
他静静地上了楼,房门却开着,他走进去,却发现诗诗披着毯子,缩在沙发上,床头的小灯蒙蒙的光趴在她身上。
“你去了哪里?”她的声音轻柔,疲倦。
“没,哪也没去。”
“骗人,为什么要骗我。”她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声音里夹杂着哀伤。
“我……我。”他不知道说些什么。
“好了,我不问了,这样好没道理,让你难受又让我心烦,多不值当啊!以后不要乱跑了啊,再不见了,我会去找你的。”
这话竟然是这么耳熟啊,林宇离开郑叔房间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对他说:“以后有什么事,您不要再瞒着我了。”将心比心,他拉起诗诗的手。
“好,我不再瞒你了。”诗诗笑笑,拿巴掌在林宇肩膀和脖子之间丈了丈。
“干嘛?”
“给你织条围巾。”
“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