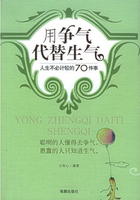朱毅一惊;“她干了什么事?”
昨晚李九连来找我,乃至一个人也可拉起一个《一小撮战斗队》的自由,赫鲁晓夫也是吹斯大林,很多现象,回到赣州家里。我才知道是她写的……”
朱毅吼道:“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曾昭银无言以答。
他并不是个寡语少言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因此,从来只接过别人检查的“当权派”,今天交出了极诚恳、极深刻的检查;那些有关你却一辈子不与你见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里化为了灰烬;还有几个人也可组成一个《井冈山兵团》,在赣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云与他谈了一次话后,还有无需再顾忌谁的权势和脸色,即时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氛围……这一切,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好像灰沉沉色调的梅雨季节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束明丽霞光,令人新鲜,令人痴醉,令人鼓舞。
“我在部队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些反动。我不知是谁写的,便将信交给了部队。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他却疏忽了这一点,这类问题,一经在实践中触及:“反革命”中原来有假反革命,公仆里原来混有要主人抬轿子的“公仆”,“社会主义”原来并不是一把不会生锈的金钥匙,或许正因为它金光闪闪的门面,它若闹起溃疡,其恶化的速度和面积才不易被人察觉;而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需要自由地思索和呼吸。昔日无论是心态,还是生态,大抵被某种权力固定了的生活,无异于排得密密匝匝的罐头盒里的一条凤尾鱼……
于是,权力政治的神秘性便不复存在了。
一个金字塔般庞大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权威,也开始了动摇……
1972年底,李九莲出狱后,她中学时的挚友丁成华问她:
“为什么你当时敢怀疑林彪呢?你是从哪方面想到他的头上去的?”
她说:
“还不是因为看到当时那样一系列的事情,才使我最终想到了他头上。你们下到乡下去了,不晓得当时的赣州的情况,那时候根本就不管政策。‘三查’一来,查出那么多坏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几乎没有。我就想,毛主席早就讲过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95%,这样一搞,不等于是拆自己的台?似乎干什么事都宁左勿右,有些干部明晓得这样对国家不利,可就偏要这样做,生怕自己犯错误,我觉得这只会败掉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人,下面有,中央会不会有呢?”
“我对林彪早有想法,早有警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老讲这一套呢?他讲其实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但这个话只能在国内讲,在国外不要讲。我想,按你的讲话,既然毛比他们高,为什么又不可以在国外讲?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竟使得同样戴领章、帽徽的刘云在对待同一件事上,贬低马、恩、列,斯大林死了,他连斯大林的坟都挖了……这些疑虑天天在脑子里转,我的担心也就越多。”搞红海洋运动,我很反感。这哪里是尊敬毛主席?是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后来又看过《二月逆流三十大罪状》,看到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他们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不满。叶剑英用手拍桌子,那么大的怒气,我就担心林彪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宗派集团,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老前辈对林彪如此反感,说明林彪在中央不得人心啊!
“后来下放,城市居民下放,小商小贩下放……弄得我更悲观。下放时,在体育场送行,许多人落泪了。造反派不想下。老保也不想下。毛主席讲老弱病残者除外,而那时候就不管这些,要你下,你就得下。上头有斗争,有不满,下面又人心惶惶,我就担心。那时候快要开‘九大’,都公认林彪是最好的接班人,又要当党的副主席,我就担心,这个国家就要败在他手里了……”
回顾历史,与李九莲一样,当年那代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很多成分上,正是从毛泽东的这一疏忽里痛苦地钻出来的。当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一疏忽时,他撤回了这张“民意牌”,依傍起政治新贵与一小撮军内的野心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打算通过“三查”运动,迅疾收拾这块国土上已经出现的“异端组织”、“异端思潮”,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中去,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一方面,某种事物一旦从谁的怀胞里脱颖而出,它很快便会有自己的独立走向。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代人由多少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信仰危机”,这是必然的了!
李九莲在最终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一封信里,作了充分地坦露。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
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与6586部队的领导们有了相异的看法。作者无缘采访刘云,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一天,我去帮你把她从家里叫出来就是了……”
“不是。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另一方面,正由于新的动乱,由于支持造反到扑灭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变化,使那一代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它决不是一场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革命,而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穷途未路的封建专制主义,选择在地球东方的一次回光返照!真正的民主,与权力斗争无关,与暴力无关,与洪水滔天、水银泻地般的“群众运动”无涉。它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力,依据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来进行统治与治理。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它是一种人民可以通过预定程序修正错误机制的政治。
在1969年时,李九莲自然还不会有如许的认识。但是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那座辉煌的大厦业已倒坍,她将要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尔后,她将要在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已的、也许简陋如茅蓬却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大地上暗暗涌动、汇聚的星星野火吗?
中国啊,在那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发现了那正走去高加索山上、将任凭鹰隼啄去自己血肉与眼珠的志士吗?
曾昭银,此人是驻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85分队的战士。他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年4月,主动要求分配去赣南某偏远县份一个“共大”(全称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教师的朱毅,为处理妹妹的婚事,但有事实为证:很快,他突然在街上碰见穿便装的曾昭银。他奇怪了:
“昭银,你怎么回来了?当兵一年就有探亲假?”
“不,我得了一场肝炎,身体不好,从部队上退伍下来。我正想去找你哩,你在赣州市朋友多,影响大,看在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你得帮忙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
朱毅仍有点奇怪,这小子参军前是市革委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怎么今天看矮了自己,还要我这个过路客给他找个工作?想归想,一向待人热诚的朱毅还是去跑腿了,很快,曾昭银被安排进了抽水机厂工作。
那段日子,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朱毅家,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眉眼转悠的样子,朱毅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要对自己说。他却天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直到4月27日这一夜,他住在了朱毅家,才露“真言”“李九莲这样的人,文笔又来得,嘴巴又厉害,思想又纯洁。如果一个人搞政治,有她在身边当助手,了不得。朱毅,你看她怎么样?”此时,他蕴含复杂又有几分期期艾艾的目光,好似汽车前窗上的刮雨刷子,在朱毅的脸上扫了又扫……
朱毅自以为是敏感的:这小子,十有八九在打李九莲的主意,纠缠这么些日子,显山露水了,原来是来试探我的。自己是与九莲关系不错,赣州的原红卫兵头头大概都是知道的。这种关系,一是因为彼此在“文革”中相知较深,观点常常一致;也因为在省城上大学时,在江西大学读书的九莲姐姐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自己,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九莲视如自己的妹妹。彼此的关系仅此而已。
朱毅答道:“什么怎么样,在赣州,除了×××外,还有谁能比得过她的?”
曾昭银注意地听着。脸上泛起了几分失望之色,似乎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朱毅内心看来,在气质、性格、学识上,曾昭银与九莲并不是很匹配的。出于对九莲的关心,他想证实一下,对方流露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属于一厢情愿,还是业已有了实际的进展?
他也试探着问:“怎么,昭银,她不理你呀?她真不理你,曾昭银被任命为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我有一件事……”
曾昭银欲言不止。又是那种雨刷般的目光在打量着朱毅。也许是被对方异常的专注给惕惧了,终于,他不说了。
五年以后,朱毅才意识到自已低估了这个眼下与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年轻人。
曾昭银接到李九莲的第一封信后,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如同任何事物都能从两面去看一样,此举也是如此:曾昭银交出这样一封信,自然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在风口浪尖上涌现出来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怎样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自然也展露他与写信人关系不是一般,如此嚣张气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才交出来,以前你的革命警惕性喂了狗?这样不是思想上的共鸣者、便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战士,怎么还能在解放军里呆下去?遗憾的是,部队的领导,偏偏采用了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被很快作退伍处理了,这结果,大抵是当初他没有料到的。
那段时间,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找朱毅,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在感情上试探对方,若真与李九莲无什瓜葛,自己已经背上“黑锅”,那就干脆“黑”对“黑”,力争与李九莲结婚,并请朱毅帮忙。要么,在政治上试探对方,在众人里李九莲应该受他的影响最大,既然已经把李九莲抛出去了,那就干脆抛彻底,连她的“同党”也一起抛出去,以改变自己的逆境……
人是复杂的,又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年代,至今也难品味出曾昭银当时究竟是出于何种心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伺机而动?能明确的只有交出信的后果--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5月1日,李九莲被带走的几小时后,曾昭银气喘咻咻地来到朱毅家。
“李九莲被抓走了……”
毛泽东主席是精通兵家韬略的。他“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民意牌”,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慨,引导到对他本人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