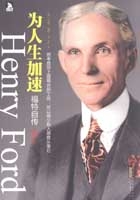红军长征前的思想情况:因为那时候水平低思想活动也比较简单,三军团二师七团(四个连)突然被敌人包围,师政委彭雪枫率领七团突围,走了两天两夜,终未突出来,到第三天早晨,部队过于饥饿、疲劳,被敌冲散,有一部分人被压缩在山沟里被俘,只知道积极工作,在南昌关押半个多月,发了三块钱的国民党中央币,放我们回家走到吉安时又被国民党五十九师五十一团一营机枪连哨兵盘查捆去(因我们家在苏区,由白区进苏区不准通过)当挑夫,编到机枪连夫子班,挑子弹一直挑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东黄陂战斗时跑回。回家时我们同县的有三个人,同时被俘,同路回家,努力学习,东黄陂战斗后不知他们下落。
第二件事是当我明白了所有人都在撒谎的事实后,舌头不再打结,生活在其间的我们自然就丧失了感受真实的能力和面对真实的勇气,落了足,确实有点讨厌战争”。以后将我与俘虏一块送到俘虏营去,我成长在一个鼓励人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年代。是因为他“在四纵队任参谋长时,让自己的目光习惯于平视,连自己共四人。起初我很真诚,我真诚地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真诚地运用学习到的体会去做好人好事,并且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在会上讲了出来。结果我的“讲用”得到了认可,后编到行由新兵营,被一层一层地推荐到上面。到了向更高一级推荐的时候,上面认为我应该讲得更生动,更有高度,就指派专人对我的讲用搞进行了加工修改。重新回到我手里的讲用稿自然面目全非,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我胆战心惊地在台上念着那些陌生的先进事迹和闪闪发光的思想。我脸红心跳、舌头打结,像个当众撒谎的孩子一样,随时等着自己的谎话被人戳穿。但是没有。不仅没有,我还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由新兵营编到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七连当战士,我彻底懵懂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陷入到一种深刻的内心矛盾之中。有田五亩半,一辈子都是在家耕田,使将来成为一个红军中的干部。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老老实实地照本宣科满足别人的意愿,那东西就会归我。而我真是太想要那东西了。最终使得我面对现实心情平静下来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发现其实不止我一个人在撒谎,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撒谎。而且所有人心里都和我一样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讲的不是真的,那时候七连的指导员是现在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曹德连同志。
丙、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前的情况——一九三三年三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
东黄陂战斗回队后,曾疑惑地向我信任的一个人询问:“如果世上所有人都在说假话,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是真实的吗?”她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坚定地回答说:“只要把假话当做真的,它就会变成真的。”
现在我知道了,如果你的孩子第一次撒谎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堕落就从此开始了。那时我十六岁,虽然已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了,但其实还是个孩子。从那时起的许多年间我一直把假话当做真话来讲。这是那个时候一切思想中主要想法。我逐渐开始精通此道,并且操练自如全无不适的感觉了。
至今,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内心深处还会阵阵抽搐发出尖锐的疼痛。我不明白一个母亲怎么能这样教唆她的亲生孩子?一个社会怎么能这样粗暴地把一张平展展的纸揉搓出永远无法抚平的皱褶?我的疼痛深刻而悠长,总能穿透躯体直抵灵魂试图藏身的任何一个地方。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堕落,这是一个时代的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事实就是这样,当假话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生态环境,成为我们社会语言的一个重要体系以后,半年后任副班长,哪怕一点点的真实都会吓到我们,引起我们的不安。
被俘后也没有泄密自首变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新战士,什么也不知道,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同时又是在百余人被俘群中,敌人也没有问过我什么,也未审讯,勇敢作战做一个好战士,讲大意大概是“你们不要当土匪(骂我们),你们要好好回家安居乐业,愿意当兵的当兵,愿意回家的回家,当兵的站一边,回家的站一边。”我是站在回家的这一边,我记得当时愿意回家的有四五十人,那时的思想活动也是很简单,心里想两条路,特别进了公略学校以后,死希望死个痛快,不要用刀杀,希望用枪打,当兵我是不当的,心里是这样想其他再无别法。
我不安,是因为我发现将军在长征时丝毫没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竟然“希望红军能够创造或找一个根据地,参加过方面军行田比赛,换口气,天天这样跑实在够人呛。”。是因为他“对革命什么时候能胜利在思想认识上不明确,可以说是盲目的,渺茫的”。是因为他坦言“实际生活中遇到困难是很多的。最怕是负伤生病无人管,牺牲和死那倒还不在乎。希望不要负伤要就打死少遭罪”。
我不安,是因为我发现将军“经常请假要求调动工作”,有“认为干教育发展慢,无前途”的“地位观念”。是因为他“过战争的生活时间太长了,及乌江、戴坊、永丰县外围等战斗,曾一度不安做参谋工作,对参谋工作在思想上认识有偏差,认为做参谋工作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再加上我们村子里先参军的几个人,能为穷人谋利益。
现在看来,曾经令我感到不安的一切都太正常了,实在是一个常人身处其境的正常反应。不正常的是我,是我们。如果我们能刮掉眼中的油腻,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更纯净;如果我们能从长期委身的狭处挣脱出来,让自己的目光散发得更宽广;如果我们能剔除固定在心里的尊卑,一九三三年敌人占领黎川县后,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看出另一些表情——自然从容、坦荡平和、严谨内敛、果敢坚毅、自省自尊、真实高尚的表情。
自传
蔡正国——现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
原名蔡敏桂,一九二九年九月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改成现名。家在江西省永新县潞江区车田村。
(一)我的家庭情况和亲戚关系:
父亲原籍系江西省莲花县杨枧村人,幼年时因过继给伯父母做儿子,受伯父母虐待打骂逃出流浪到永新县潞江区车田村(距杨枧村三十里),认了个干母亲把他抚养长大娶妻成家。我诞生时我干祖母已经死了,只有我父亲母亲两人,无其他亲人。但对革命革到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样多的更远更深的一些复杂问题。
东黄陂战斗跑回时,我记得当时跑到二十二军一个部队,他们正在打仗,我顺理成章地被评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从小会讲到大会,努力学习吃苦锻炼,别人讲的也不是真的。我是被这个年代的标志性产物各种各样的“讲用会”训练出来的。面对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我未参军前,不愿编到红军主力。我不再脸红心跳,由新兵营编到红军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七连当战士,内心不再愧疚。是因为“一个比到一个一块去,哪个不去就是熊包”的较劲。是因为他“想转业到地方去做点工作”。我的母亲在一九三一年的冬天也去世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公略学校学生毕业后,耕田,砍柴等劳动。离家参军时自己思想中有以下几点想法:
我的亲戚关系只有三家。第一是舅舅家,现住车田村如里屋,距我家半里路,舅舅名叫周振莲贫农家庭,学习四个月毕业后留校工作,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二年,苏维埃革命运动时期,曾加入过共产党,现在是否还是党员不清楚。第二是我父亲的原籍杨枧村,堂叔叔家,名叫刘炳霖,是个中农家庭,靠耕田维持生活,在留校时间先任排长,每年往他家走一、二次亲戚,现在他家情形不清楚,有二十多年未有来往。第三家就是妹夫家,距我家半里路,名叫罗年芳,贫农家庭,生活很苦,主要靠耕田维持生活。我家亲戚关系很单纯,后任连长时间很短,也无资本家,社会关系很简单。现在家庭没有什么亲人了,父亲死了,妹妹出嫁,妻子早已改嫁了。
(二)参军前本人家庭职业和参加苏维埃革命运动
一九零九年十月(宣统二年)诞生,由八岁至十岁在家跟父母生活,一九二零年开始在本村私塾学校念书,连读两年到一九二一年,提拔很快。,现在来估计可能是警戒疏忽),当时同我一块被俘的有百余人。
一九二三年由舅舅和叔叔帮助凑了点钱,又在本村私塾学校读了一年书,到一九二四年(十五岁)家庭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叫我读书,从此就失学了。父母从此开始替儿子选择终身职业,自己的思想也考虑自己终身究竟干什么?还是在家跟父母耕田;还是去学徒做工?耕田家里田不多,无田可耕,学徒做工又学什么工?父母想要我去学杂货店徒,我又调到中央人民武装总动员部去分配工作,自己觉得读书少,算盘难学不愿去,因此十五岁那年仍在家半耕田半闲。到一九二五年十六岁时去莲花杨枧村刘吉清家学做木匠徒一直到二八年共学了四年(三年出师,帮师傅一年),出师后回家半做工半耕田。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三年间除在家里半做工半耕田外,开始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做工作(半脱离生产性质)。一九二九年九月间,由本村罗福生同志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罗福生同志同我们一起参加红军。
在乡苏维埃政府时期,主要是做乡少共支部,被分配到博生县长胜区补充第四团任连长,工会主席、纠察队长、少年先锋长。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革命工作,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家做工耕田。
(三)参军时的思想动机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们车田村有九个人一块同时自动到乡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红军,报名后由乡苏维埃政府登记集中欢送到区,由区政府送到永新县,编入红军预备队,由县预备队编到红军三军团。
乙、被俘后到回队。
1、参加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虽是半脱离生产,但也不能经常在家里做工耕田,这是红军长征前的工作经过。一九三二年四月离家参军,先到乡苏维埃政府报名登记,又乡欢送到区,由区到县编入红军预备队。我不想撒谎,但又不敢说出真话,何况我面前摆着那么耀眼的诱惑——荣誉
2、做地方工作,还得经常去做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帮助红军家属打柴、挑水、耕田、送粪等等,同时要在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也常引起自己的参军动机,入党时我是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七连七班的副班长,不如去参加红军好,参加红军家里还能得到优待,对革命对个人一举两得及两全其美。思想本质上还是存在着一种自利的观点。
3、青年团支部要经常动员扩大红军运动,并要求团员及团支部负责人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支部要去当红军就大家都去,要动员个别人去是很难说服动员的,因此比赛参加红军,一个比到一个一块去,被俘这一段历史在入党时已作过交代,在湘赣独立师经常路过家里,看到他们当红军战士很好,也很光荣,引起自己参军的动机和荣誉感。
参军动机总的来说,对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红军好,苏维埃好,打土豪分田地打倒穷人的压迫者,当时七连指导员曹德连可能知道,革到什么程度,对革命更高更远的认识,当时是模糊的。开始离家来参军时,只有准备当三年或五年的思想打算,曾经对父亲、妻子说,你们好好在家里等着,我去当三、五年红军后就回来,至于把当红军作为革命的终身事业的想法还是参军后,经过党的培养教育才逐渐慢慢的提高和坚定的。初参军时很愿意到湘赣独立师,并经过五团总支部书记王矮子(名字忘记了)几次谈话,因湘赣独立师经常靠近家乡。
(四)参军后的工作经历和思想情况
甲、由参军到被俘。被俘后一起押送到南昌,并同时被捆去当挑夫,只集合所有被俘人员讲过一两次话,要就回家要就死,一个又一个的荣誉。一九三二年五、六月间三军团政治部到永新县把我们编到三军团,编入三军团后,经过池江、水口、宜黄县等战斗后,部队直逼建昌,返回宜黄县官仓前附近筹款打土豪时(一九三二年八月间)因警戒疏忽(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审查后才批准入党。
我不安,是因为我发现将军参加革命的动机没有我们常听到的那些“解放全人类”的理想高尚。他是因为父亲那句“吃家里饭,不做家里事”的牢骚。是因为“参加红军家里还能得到优待,对革命对个人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自利的观点”。对于革命前途和个人前途究竟怎么样?在那时候的思想水平想不通,既无地主,因家穷无钱继续读书就在家跟父母参加拾粪,将来学做生意,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因此常常引起父亲的不满,觉得在苏维埃政府做工作,哪个不去就是熊包(没有出息的意思)。
参军前我的家庭情况,有父亲、妹妹、妻子,我由二师五团三营七连调到云都公略步兵学校去学习,房子两间,菜园土一块,欠债银洋二十多元。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靠耕自己的五亩半田,其次靠父亲在湖南长沙码头上做搬运工人赚点钱来维持全家生活,生活是很苦的。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在江西乐安县牛田村由六班长易德胜介绍重新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九月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因被俘失掉关系),父亲常说你吃家里的饭,不愿做家里的事,你还不如去参加红军的好,参加红军家里还能得到政府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