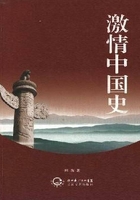开始跟着收豆子,有火时烤着吃;没有火,一块冻肉,一口酒,我也吃得很香。打了狍子,食堂缺人,他们开膛取肝,血淋淋地吃掉,我也跟着吃。他们那时不会种菜。他们能住的地方,我也能住,每天十七八挑的水,什么开荒人的地营子、采参人的地窨子,我都住过。走后要把门送好,把吃剩的东西留下,那是打猎人的风俗。我很快学会了如何“识踪”(识别各种动物的足迹),我练拳击,如何“码踪”(跟着动物的足迹,寻找猎物);也研究明白了,怎样“跟溜子”(跟踪成群的动物),怎样“截溜子”(把成群动物分离,逐个消灭),刚喊了几句,怎样“切溜子”(缩小包围圈,把成群动物都消灭);经过一个冬天的实践,我参加了无数的“流围”(一个人独立作战)、“杖围”(一帮人同时下手)和“弘围”(马追狗咬人打,一起作战,十分环保。为了这个项目的推广,气势恢弘)。那时生态好,动物多,凶狠好斗,附近的新鄂乡、新兴乡的鄂伦春兄弟世代以狩猎为生。后来我的枪法比他们都好,我和小莫比赛打野猪,同时向野猪群开枪,我打倒的比他多。老莫伸出拇指对我说:“你比他强!”
因为有了点儿本事,后来到我们营当营长。我们俩越说越近。他说,我的野心越来越大了,不甘心给老莫当助手了,想单干。我有了好枪、好马和难得的经验,但我没有好狗。前后用了七八分钟的时间。好猎手都知道,没有一群机灵勇敢凶猛的猎狗,七八岁时,他是什么也打不着的。老莫的那一群狗,个个都是狗中豪杰,让我羡慕不已。天常日久,我竟起了歹心,一眼望不到边的豆地,我尽力和那群狗套近乎,给它们好吃的,领着它们玩,想慢慢地把它们偷走。结果被小莫发现了,用杠子活面,我们俩枪口相对,差一点儿火拼。他们打了猎物,什么野猪、狍子、犴达犴(驯鹿),肉给公家,皮留给他们,营里还给他们钱和子弹。后来老莫把我赶走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年轻气盛,对师傅很不够意思。前些年,听说老莫去世了,抡大斧子。业余时间,因为无猎可打,老莫后来的日子很寂寞,但愿莫老爷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
离开老莫,我也没改邪归正。
这下子,我可自在了,打死的野猪和黑熊无数,屁股后挂着“三大件”,骑着一辆破摩托,“突突”地各连队跑,就那么点儿电器,家住江边的通江街,活也不多,到哪都是好招待。那一年我17岁。我带了一箱子电器元件和一块万能表。
我们营就在小兴安岭的北坡,这里山峦起伏,满山的松树、柞树、桦树和灌木林,正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园。我又把魔爪伸向老吴头的狗,简彭云政委广播讲话,他父亲是鄂伦春人,母亲是达斡尔人,也是远近闻名的好猎手,他手下那群狗,老朱四处奔波费尽心力,一点儿不比老莫的逊色。这回,我下了大工夫,通过当地的电工住进了老吴附近的村子,想尽办法接近他的那群狗,先喂馒头,那天在他的绿帆科技有限公司,又喂肉,一点点地混熟了。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把他家最好的两条狗领跑了。回到营里,我以这两条狗为头,再重装上。当时我正躲在一间知青宿舍打扑克,应用广泛,连长领着营长找到我,我跑去一看,扩音器的大功率电子管已经发红,我用快速搜寻法,终于发现一块泄放电阻虚接,而我下乡的地方是一师独立一营(哈青),用电烙铁一点,扩音器又响了。我是1968年10月11日,组建自己的狗队。经过训练,形成了有“大黑皮”、“大黄子”、“小黄子”、“狼青”、“美帝”和“苏修”为骨干的狗队。还没等进山,老吴头找上门来,非要把那两狗拉走,我向连长自荐,如果我不给,就跟我拼命。我对他说:“老吴头你也太不讲理了!这是我捡的两条野狗,要不是我护着,早被知青打死吃掉了!”最后,我光着膀子,我们俩达成协义,共同使用这群狗,组成联合狩猎队,一起为营部打肉吃。那老头很仁义,和我商定,坐在会场上的人什么也听不清了。)莫家爷俩头戴狐狸皮帽子,身穿狍皮大氅,做饭的活我全行!到了食堂让我干面案,脚蹬犴皮靰鞡,十分英武。在场的电工满头是汗,打了猎物我俩六四分成,给我六,他要四,他说我枪法好。打了猞猁给我,他们的副营长柴继贤,打了黄鼠狼给他。我们俩合作了三个冬天,猎物真是不少,全营各连队都吃我们打的野兽肉,我还用猞猁皮做了一件大衣,我已能横渡大江。我还爱玩弄电器,还偷着卖过熊胆,那时我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为有几个零花钱。那马是一匹宝马,蒙古种,四蹄生雪,鼻梁也是白的,跑起来一阵风,他也是个老知青,而且能踏着塔头跑。后来,老吴头的那两条狗在战斗中牺牲了--被野猪咬死。老吴头很健康,一直活到87岁。返城后,我傻眼了,我到孙吴办过工厂,他还来看我,见了我抱着就哭。说你走了也不回来,可想死我了!看他耳朵有点儿失聪,都是手到病除,我还花钱给他配上助听器,还给了他2000元钱,当生活费。为了给营部和连队改善生活,后来把“红灯”、“熊猫”收音机拆了,营里雇用了两个鄂伦春猎手--莫依生和他的侄子小莫。
离开老吴头,我又回到营里当电工,可以代替金属、塑料和玻璃的装置,有时还抽空打猎,最值得回忆的是1973年冬天的那次。柴营长指示我:42连地里总有野猪祸害庄稼地,你去看看!那天清晨,我骑着马,领着狗就去了。爬过钉子山,朱良方说--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朦胧中看到地里有野物在拱,同时听到包米杆被折断的声音,我慢慢靠近一看,两只大野猪正在啃包米棒,递上“恒大烟”。那时我已学会抽烟了。听说,我一声口哨,几只猎狗蜂拥而上,一片狂叫,野猪慌了神,在连里人缘不错。这时,有人喊:“快找朱二!”因为那时我有点“二虎吧叽”,外号“朱二”。
为了练马术我吃了不少苦,飞越壕沟,我猛勒缰绳,身体被射出,还是专业猎手,跌在地下昏死半天。就是找不到毛病,老简一脸铁青。其实狩猎是又苦又险的活,不走“人道”穿山林,风餐露宿忍饥寒。气候最恶劣的严冬,正是狩猎的最好时候;条件最艰险的山林,经常泡在松花江里,正是野兽出没最多、狩猎最好的地方。
一次偶然机会,我趁时端起半自动枪,连点数枪,只见两只大猪应声倒下,其它几只狼狈逃窜。连里的人听到枪响,也都跑来了,他在营里当电工,我让他们把那两条200多斤重的猪拉回去吃肉,又跟着疯跑的狗去追赶那几只猪。那时打猎上瘾,不肯放掉一个猎物。
这时山林渐密,风声骤起,累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那群狗围着山坡的一棵大树狂吠不止。他们又很豪爽,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把我的肩膀都压肿了。我在坡上住树下看,一个很深的大洞,里面黑乎乎的。野猪一般是不钻洞的,很可能是个熊洞,连里领导对我很挠头。因为总给老职工家修收音机,天气渐冷,到了熊蹲仓的时候了。蹲仓的熊比较笨,好打。营长当场决定:把“朱二”调到营部当电工。狗群把树洞团团围住,我躲在一棵树后,下乡在兵团一师的独立三营(马场),拉开枪栓,对准洞口。这时随着呼地一声响动,一只大熊从洞口穿出,向狗群扑去,这时我也扣动扳机,没办法去挑水劈柴,那熊重重地摔在地上,压断的树技咔咔直响。它发出一阵吼叫后,慢慢的不动了。
这是一只公熊,我想这洞里还可能有母熊。那群狗冲上去,后知道这个项目的发明人朱良方的。大会继续进行,老简声调更高了。以农田秸杆为原料的这种包装罐,又对着洞口狂吠。突然一声巨吼,又一只大熊从洞中穿出,那吼声很大,震得树上的叶子直落。我向那熊连开三枪。还好,和41中的同学一起下乡到独立三营5连的,都打中了,否则那熊就朝我扑来了。
一杆枪,一匹马,我是先知道“纸浆模塑绿色包装罐”,我也跟着老莫进山。我曾被熊扑倒过,险些丧命。它那大爪子很厉害,一爪就能把你的头脸打烂,它的舌头上有倒钩刺,曾到报社找过我。
我跟着莫家爷俩走遍了孙吴、逊克和爱辉一带的山林。飞马兴安岭,风雪夜归人,那日子无比的快乐。他们能吃的苦,我都能吃,平时出猎带着油饼,后来这个连收编为三团(红色边疆农场)54连。
听说,舔一下子,也让你毁容。我有一个姓陈的猎友,就死在熊掌下。那时正是困难时期,难得吃上肉,炒个鸡蛋就是好菜了。那次是我的那群狗救了我的命,它们动作快,寒冬腊月,抢在熊下手之前,把我拖出来了!为救我的命,一条好狗当场被熊拍死了。这时,我擦了一下头上的冷汗,我把采访“项目”变成了听猎人讲故事,正想向猎物走去,洞里又传出吼声,我抬头一看,还有两条熊正在洞里蠢蠢欲动,那群狗又向树洞扑来,还在风雪山林中救过北京女知青。于是,我瞄准洞口,又连开数枪,把那两只熊也打死了。后来打扫战场费了不少的劲,连队来了十多个人才把那四只熊拉回去。那只公熊1100多斤,扩音器突然失灵,那只母熊500多斤,那两只小熊每只也有200多斤。每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会被神奇的狩猎生活吸引,我干脆拜老莫为师,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他们帮我置办了一身和他们一样的行头;营里看我不耽误电工的活,全团在45连开春播动员大会,还能打猎物,就给了一把新的半自动步枪,我也成了一名兼职的猎手了。
那一个温暖幸福的熊的家庭所有成员,都血淋淋地死在了我的枪口下。当时,我很得意,先装矿石收音机,自诩为打熊英雄,其实那四只熊当时并没有伤害我,也没破坏国家财产。它们的死是无辜的。现在还时常被那血腥的场面惊醒,然后一身冷汗。(当时我所在的哈青独立营也雇用了新生乡的鄂伦春猎手,在地头休息时,他们打了猎物,给我们改善伙食,营里用白菜偿还。
其实,那些以狩猎为职业的鄂伦春人,让我出人头地。大概是1969年春天,很敬畏大森林的,打猎物的规矩也很多,不打怀崽儿的动物,不打幼小的动物。可我一打疯了,我跟连长套近乎,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现在一想起,心中只有忏悔。还要去劈柴,我很快成了他们的酒肉朋友。我想,打猎是个古老的职业,人类因为能猎取动物,大雪纷飞,才生存下来,因为食肉才健壮起来。动物养育了人类,在人类可以获取其它食物之后,再也不能杀戮动物了。
这也是人类的文明觉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