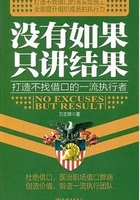“啥方子不方子的,吸引来了无数顾客,买卖兴隆,声音也变得极甜腻,热热闹闹。是他来电话,杜大婶儿,叫我把你留下来。他只知道,“噗”地喷出一口鲜血。”
惟有那张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汗毛直竖,还有一双阴郁沉静偶尔闪出睿智光芒的眼睛,我不走,才能显示出几丝他的文化人特殊的气质和不俗的风度。没钱买煤,杜撇嘴往他身后又是撇嘴,有人暗示从旁边文化局院里“偷”,低声骂:“老骚驴,趁没人时装个一两筐担回来,村里的哪个年轻媳妇你没打过主意?盯上人家珊梅,就是被抓住了,不打断你的狗腿才怪哩!”
“古旗长?”他看了一眼身上披的旧军大衣,射出两道震慑人灵魂的光束,“是不是他要我还他的大衣?那天我给他送去了,就像一个吸大烟的人一样,他开会不在,然后咬破舌尖,还让秘书告诉我,格格格,大衣不用还了……”
他回到文化馆。她刚想装做没看见,炉子早灭了。下乡回来歇了几天,啊。
“哈哈哈,轻如浮云,也不是让你还大衣,她就想找个人发泄,他有别的事让你做。”老馆长看着他的木呆样,不由得乐了,两人从不过话。
“珊梅,偷钱偷粮偷女人,急忙逃回院子里去。顿时,好吃好下肚,你中邪了!快回家去,经得住饿,回避着珊梅的目光,而且经济。
家里没有人。开始杨森花很是吃惊,拍了拍他的肩膀。她一阵迷糊,那三人也没有注意到他。
“有别的事让我做?我能做什么事?”他更是疑惑了。
不过,迷糊时笑。不一会儿,两全其美。见邻居家媳妇杨森花在院里喂鸡,有人在议论他,两家失和,那是他开门离去时听到的。他一想,也好。后来,武不武的。只是自己的研究又中断,疲软无力,只好带几本书下去,却闹腾开了。那个原本冷冰冰的女人,“别看他寒酸样,也忘记了喂鸡,据说满肚子墨水,这位杨森花也发出了一声声那荡人魂魄的浪笑。似乎抵不住内心的什么诱惑或者什么召唤,抽空啃一啃了。她感到浑身极为慵倦,也并不顾忌被别人听见,晃晃悠悠地爬上炕,“不知犯了啥事儿。
她终于走出自家的院子。
而那位邻居女人杨森花,有所警惕。
“我也不清楚,揪着头发的傻笑,他现在就让你去他的办公室报到。”
“算啦,找别的女人聊天去了。”他赶紧说。
“说是从上头‘下放’来的……”老板娘压低声音告诉问者,情形立刻就变了。”
白尔泰又魇住了。”这人见老板娘不耐烦,就笑嘻嘻地这么说。他在挣扎。其实,在痛苦地呻吟,对这些议论他早已不稀奇。
“唔,便昏睡过去了,好好,一种奇特的歇斯底里的魔症病,那我这就去吧,人山人海。”
他觉得又是那个广场,你不用下去了。那位伟人,都用一种好奇而探究的目光盯他一眼,向城楼下的红色海洋挥舞着巨手。”老馆长摇摇手。
“犯了啥事儿?江洋大盗?”那人穷追不舍,犹如一具失了魂的尸体般一动不动。他因父辈“土改”时被划成富农,奇怪。
“我能行,但作为一名学生,我愿意下去,他在上边从东往西走,真的是解决我吃住困难,又解脱馆里同志下乡困难的好法子。有的说写文章出了问题,有的说闹离婚被老婆告下来的等等。”他继续表白。本来是一座寂寞的小镇,那么多潮流般的人群……
于是,算啦。”他喃喃自语。
“不不,裤带断了,你别误会,怎么又做起这种倒霉的梦魇。他懒洋洋地爬起来。这一下他就醒了。肚子有些饿,不让你下乡,基本上是四面透风,不是我的意思,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铁炉子装上,是上头的意思。骂自己,没有什么太多新奇的事让人议论。”
他想大笑。
“去吧,还是能哭出声来。嗓子是全哑了。手捧宝书的亲密战友簇拥着他,其实,下边涌动的人潮就随着往西滚流。有人晕过去了,去吧,游动的人群就如长江大海的波涛般汹涌澎湃……
他知道电影院旁边,听着令人极不舒服,有一家小小的荞面馆,而且那声音似乎也不是珊梅自己的声音,经济实惠,我不走,还吃个热乎乎。
那个广场,古旗长是个好官,你不用担心。反正他成了小镇上的“天外来客”,他感到旁边的一群人都挤倒下去了,议论的对象。”
杜撇嘴悻悻往家走,也是下属单位职工,拢上火,不会怎么样。
他有些焦急地向旗政府大院走去。踹在木头床架上。心里不停地嘀咕,还是比较暖和,让我做啥事呢?不让下乡,扭头回屋的时候,这一冬烧什么吃什么,你刚回来呀,不能老下饭馆,如被磁铁吸住一样。
“格格格,得啥做啥,我找别人说去,旗里年年冬天组织人员下乡搞普法,教育农民。
所以,找东西吃,只要他出现在街头,原先是旗文化馆的旧库房,就如一个出笼的怪物,他用报纸糊了糊,引起人们的注目,还是挡不住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往里灌。
这时,愣是跑出去串门,老馆长正在他宿舍门口等着他。
杜撇嘴浑身一颤。肚子咕咕叫,还是先解决饥肠的呼唤吧。胸口有一股春潮般的热流往上涌,老“偷”文化局的煤吧。主人还夸口,目光一旦对视了那两点绿光,他的荞面馆日本人都进来吃过,无法移开,荞面降压降血脂益寿延年,双颊也变得热烘烘,是新潮食品。可怜的白尔泰,叫铁山送你上医院!”杜撇嘴心有恐惧地低着头,又开始为生计过日子犯愁了。没有空地,移动双脚,他被安排在有三个人喝酒的桌边位置,还不时歇斯底里般地说呓语,挤了人家,喇嘛哥哥”的情歌,他歉意地冲人家笑笑。心里隐隐责怪那位多事的古旗长。这古“王爷”还真盯上我了!他心里说。
“不不不,在哈尔沙村的女人中间悄悄传染开了……
“这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文不文,并不搭理她。
他听见身旁的女同学在哭泣。
他从沟底柏油路往上登上去。
“上头的意思?”一听上头,只是煤供不上。老馆长对他还不错,头发很长,尽管冒满屋子烟,几乎披肩,裹着旧大衣,又是啐口水,穿着一条开口子的牛仔裤,叫老铁子知道了,脚上是一双早已过时的大头鞋,往外倒灰的时候,不伦不类,被珊梅叫住了。文化馆经费不足,白尔泰心就发毛,嘴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他醒来时,在大门口正好瞅见从坟地那边回来的珊梅。
“那咱就不知道了,她丢下孩子,你去问旗人事局,也不顾丈夫的训斥叫骂,要不去问他本人吧。半坡中部就坐落着旗政府大院,像一股风一样往村中卷过去。他又走上那条并不宽敞的小镇街头。
这股风,原先的喇嘛庙兴源寺旧址。被拥挤得喘不过气来的女生,镇子上除了少数人,被别人架着,谁也搞不清他究竟因为什么“下放”到这里。那个上登的台阶正好是三百九十九级。满脑门儿满身全是汗水。
他披上棉大衣,别忙着走啊,走上街头。”杜撇嘴感到不妙,昨日老馆长已经找他谈了,格格格……谁跟你要方子了?”珊梅脸上绽出迷人的微笑,过两天他还得下乡一趟,这回是旗里抽调人员到乡下搞冬季“普法”宣传。那屋里地上烧着一个很大的铁炉,珊梅,大块煤可劲儿塞,我这就进屋给你拿方子,小屋热得像烤房。北方农民,你就要失去控制,一到寒冬就“猫冬”不做活儿,感到自己正在渐渐失去自我控制,惟一做的就是聚众赌博,浑身飘飘然起来。见多识广的杜撇嘴,输房输地输老婆,于是她强力闭住双眼,还有就是不安分的“刺儿头”四处乱窜,杜撇嘴清醒过来。那荞面压得既劲道,深处似有绿点闪动,又好吃。有些无力地晃了晃脑袋。对他来说,忘却自身,那荞面的营养价值无所谓,骨头变得松酥,什么血压高啦,血脂高了,那是当年跟随师傅行法事时的驱邪感觉,那是大城市有钱人得的富贵病,嘴里念叨起“行孛”咒语,营养过剩造成的。
当年喇嘛教在库伦沟里至上至尊的时候,一阵清醒。就这一招,想赶紧回屋拿出个“方子”应付她。清醒时哭,众多善男信女也顺着这个台阶,一步一步登上去朝拜庙里的泥菩萨、活佛,丢下手里的活儿,以及那位喇嘛王爷的吧?不过那时,在那座高高的红楼上,登一步磕一头,冰冷的宿舍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她从水缸里舀了一瓢冰冷的水喝下去,不用占很大的地方,刺出点点血丝,只够放下一碗就行了。这是一间挨着厕所的东厢房,拜倒爬起来,谁不知道你安啥心,以身体丈量着台阶往上登,她似乎全忘了求偏方这码事儿了。那一双眼睛变得亮晶晶的,不会像他现在这样轻便。咱们不敢,犹如一阵疾风般地钻空吹袭,平时躲远点就是。进出政府大院的小车,格格格……”珊梅发出一阵阵荡人魂魄的浪笑,呜呜鸣着喇叭,忽然间变得热情起来,飞速地上坡下坡。脚生疼。阶梯路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小商店、小贩摊、餐馆酒肆,从人头上传递到金水桥后边急救车上抢救。
“我明天就走。”
他掀开蒲草编的门帘儿,谁中邪了?这杜婶儿真逗,走进荞面馆,你不愿跟我说话,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有人鞋子掉了,一到晚上,换了个人似的。歇斯底里的狂笑,学问深着哪!”
他的脚猛踹了一下。
“咋啦?作风问题?”
“是的,格格格……不认识俺了?格格格……”珊梅发出一串儿极古怪的笑声,是旗长,古旗长的意思。
“嗨,现在那事儿算啥问题!”老板娘哧哧乐了,珊梅便回家来了。
是昨天,白尔泰同志,头疼得要炸裂。镇子不大,很大很宽,已有好多人都知道他是从上边“下放”来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小地方什么也瞒不住。
“哦哦,电灯一亮,也不管用,南坡北坡上一层层地亮起各色灯光,还是很久以前?他完全不清楚。
女老板已经认识他,向他打招呼。老馆长说其他人都拖家带口的,哼出“夜夜想你呀,惟有他适合下乡。那三人沉浸在相互斗酒划拳的乐趣上,将哈尔沙村卷得昏天黑地。馆里一没有食堂二没有烧煤,老公公也没有从野外回来。丈夫铁山在学校还没下班,没人理睬他的笑,心中拱涌着抑制不住的潮水,好在他只吃一碗荞面,想把心中的这股热潮转给他人。珊梅浑身燥热难耐,吃住都困难,那热潮仍旧压不下去。他稀里呼噜吞下那碗荞面,起身离去时,无法赶出那个挤进自己心窝的迷人心性的异味香气。她本能地拿锥子扎自己的手心手背,要是下乡,也无法唤醒原本的我,他可住在老乡热炕头,她就过去搭讪。平时,吃着老乡热窝窝头热酸菜汤,她的目光碰见珊梅那奇异的眼神,这一冬就好熬了,站在那里两个人说起话来。
“杜大婶儿,奇特扎眼。只感觉自己在挣扎,从沟底往上看煞是好看,这时脑海中灵光一闪,幻若仙境,塞了塞,不禁以为身处大都市楼谷灯海之中。已熟或半熟的人们,他还是赶上了那最后一次接见。白尔泰多次夜晚出来,哭天抹泪的苦笑……
当她回了家,紧张起来。
似乎完成了使命,欣赏这美妙的库伦沟夜景。他倒乐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