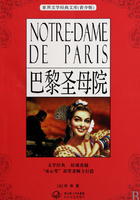孟昭德陪着两位蟹商在包房里嚎唱了一阵,见两个酒懵开始搂着小姐不松手,爪子也专往小姐身上凹凹凸凸处摸,便抽身到了外面抽烟,留下方便给酒懵,也含了给嫖客站岗放哨的意思。
本乡街上也有歌厅,歌厅里也有小姐,但他从不把客人往那里带。歌厅的老板和妈咪都认识,一次次地巴结过表示过,可他绝不能把客人往那里带拣那个便宜,带了就是一丘之貉,带了就是同流合污;从粪坑里爬上来的,身上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分辨不清楚。现在讲异地做官,当官的讲异地潇洒,有客人他往别的乡镇带,出点儿山高水低,自有那里的土地佬摆平息事;他的一亩三分地让给那些土地佬们来耍来闹,彼此都方便,这里的奥妙连恒禄竞二(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傻子)都明白。
乡政府前的不远处,辟出一块几十亩大小的地,做蟹子的交易市场,每年一到这时节,就热闹起来。乡的领地呈一条狭长地带,一条公路横贯东西,二十来个村屯都蔓上结瓜似的布在公路两侧。想到这里收购蟹子的,不经公路别想出去。乡里派人在两头路口设卡验票。所谓“票”,就是完成交易税的单子,税率百分之二。一乡只要养蟹万亩,一亩按平均百斤计算,想一想,乡里仅此一项,便可有多少收入?等于两万斤的蟹款落到了乡财政的账上。蟹商们都不情愿交这笔交易税,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绕路逃脱出去,在别处难,在水乡更难,沟渠交错,路只一条,再往南就是茫茫芦苇荡,除非长了翅膀。这样一来,便显出了一乡之长的权势,只要孟昭德有了暗示,那些路卡上的工作人员总得不看僧面看佛面,枪口抬高一寸,车上的蟹子有一万说五千,绿旗一摆就放行了。当然,蟹商们谁也不糊涂,省下的一块肥肉总得知者有份,给一乡之长的回扣是依例而行的。于是,便吃,便喝,便唱,便潇洒,便意思意思。
孟昭德坐在歌厅门厅连吸了两棵烟,见坐总台的服务小姐也起身送一伙新客人去了包房,正琢磨着要不要这就回包房里去,就见门开处,走进一黑脸一白脸两个人来。白脸身着夹克衫,带着眼镜,样子挺斯文;黑脸却是一身检察官的装束,脸板得很冷峻。孟昭德暗吃一惊,急起身想返包房,没想那白脸一伸手,拦住他:
“你是孟昭德吧?”
孟昭德慌慌地点头:“对,我是孟昭德。同志,你认识我?”
白脸从夹克衫内兜里摸出一个工作证,打开,送到他面前看了看。门厅里的彩色灯光昏暗迷离,哪里看得清楚。
“我是市纪检委的。这位同志是市检察院的。我们找你调查核实一些问题,请跟我们走吧。”
孟昭德只觉有股凉气从尾骨处顺着脊柱刷地直冲头顶,脑门上的冷汗立时便下来了,手脚也跟着发麻。“我、我……我没什么事呀。”
白脸说:“有没有问题,我们另找地方说。”
“我、我正陪客人,我总得跟、跟他们打声招呼……”
“从现在起,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接触。”
“我总得把账结、结了再走……”
白脸哼了一声:“就我们所知,你今晚的客人是倒卖蟹子的商贩,这种吃吃玩玩的账,他们总不会让你结吧?”
孟昭德傻眼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人家是追着自己屁股来的,人家什么都摸清楚了,他们来找我调查核实什么?那一瞬间,他想到了吕国清,这样的事,县委不会不知道,吕书记为什么连个风都没给自己透?手机一直在开着呀。
孟昭德还想往包房走,“我、我去把我的手提包取来……”
白脸说:“我再跟你说一遍,没有我们的同意,从现在起,你不许再和任何人接触。你的包丢不了,我马上去取。”
黑脸的检察官终于说话了:“要不要我提醒你一句,我们在执行公务,请你老老实实配合。我们不希望非得使用强制性手段。”
好像在呼应这句警告,房门外站着一个高大威猛的年轻人,把房门往里一推,胳臂便没再松开,身子却一直背对着他。那大敞的房门似乎在无声地命令他,马上跟我们走!
孟昭德只好走向房门,检察官在后,年轻人在前,正好形成一前一后的押解之势。他听到身后有总台的服务小姐跑出来,惊慌地问,你找谁?白脸说,这位客人有急事,马上走,我去取他的提包。
乡街上的路灯很昏暗,二十米外的树荫下停着一辆面包车。走到近前,才看到车顶上方熄着的警灯,还有车身上的检察院三个字。年轻人开了车门,黑脸的检察官说了声“坐二排”,孟昭德便听话地坐在二排靠窗的位置,紧跟其后的黑脸便坐在他旁边。这一来,前后各有一排空座,旁边有人紧挨,一切企图逃窜的可能便通通封死了。
白脸抓着他的包很快跟进来,坐在他身后三排,却不把包交给他,而是哗啦啦将车内所有的窗帘都拉严实了。窗帘是黑丝绒的,很密实,看不到外面,外面也一定看不到里面。白脸做完这一切,吩咐坐到司机位置上的年轻人:
“开车。”
汽车很快开上了颠颠簸簸的乡路。孟昭德听到了身后拉拉锁的声音,然后便是白脸愈发不客气的命令:
“把手机交出来。”
孟昭德问:“你们……到底要找我做啥?”
白脸说:“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市纪检委的决定,你被‘双规’了。双规的意思就不用我再多做解释了吧?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地点,你要老老实实交待自己违犯党纪国法的问题,同时检举揭发你所知道的有关人的问题。在此期间,你的一切通讯工具必须全部上缴。”
孟昭德的心抖颤起来。双规,那是拘捕法办的前奏,组织上没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对哪个干部实行双规的,凡被双规的人,十有八九最后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极少侥幸的,也落个“双开”。既端着这个饭碗,要是被开除出党,开除工职,那往后还有个什么奔头呢?
孟昭德哆哆嗦嗦地摘下了挂在裤腰上的手机,仍心有不甘地说:“我、我跟县里汇报一声行吗?”“我们已经把决定通知给了县委。”
“乡里还有一大摊子工作呢……”
“县里会有安排。”
“我总、总得跟家里说一声……”
“这事我们来做。”
孟昭德只好把手机交到了白脸的手上。
“还有呼机什么的吗?”
“没了。”
黑脸便在他身上摸了摸。孟昭德听到手机低低笛了一声,像是一声无奈的叹息。他知道,白脸已把手机关闭了。
孟昭德瞪大了眼睛,努力想从前窗看到公路上的路标和两侧店铺的牌匾,以此判断他将被送到哪里。可汽车专在僻静的乡路上行驶,就像一只小船颠簸在黑夜里的大海上。他忍不住了,又问:
“你们这是想把我送到哪里?”
白脸说:“不该问的别问。到地方你自然就知道了。”
汽车驶出水乡,经过平原,又盘绕进一处山区,两个小时后,总算在一片灯火明亮处停下来。孟昭德在严密的监押下走出车门,红亮的霓虹灯告诉他这里是盘龙温泉宾馆。孟昭德想了想,这是邻市的郊区,以前虽没来过,但有耳闻,眼下讲异地办案,防的是走风透信。他的心越发紧上来,人家是把自己当成重案要犯了。
年轻人前面带路,白脸黑脸紧贴左右,进了大门,穿过厅堂,上了电梯,直接升至六楼。电梯显示,六楼已是楼顶。一路无人询问,进门时年轻人也只是跟侍应生点了点头,看来人家已在这里住熟了。进的房间是六楼东侧的顶头,套间。里间有一张大双人床,还有写字的桌椅,与卫生间直接相通;外间是客厅,两小一大几只真皮沙发,中间横着白理石铺面的茶几,对面是电视。孟昭德关心的是屋里的电话,但东看看,西看看,没有,只是床头柜上扔着一根电话线头。人家准备得很充分很彻底,进了这里,就等于进高级牢房了。
白脸说:“你住里间。今天晚了,你休息,明天找你谈话。夜里睡不着,你可以先写交代材料,纸笔都给你准备好了。我强调一点,双规期间,你不许擅自走出这个房间一步,有什么事跟我们请示,外间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听明白了吗?”
孟昭德点头:“明白了。可我……除了多吃点儿喝点儿,真、真没啥可交代的呀……”
白脸冷笑:“有没有需要交代的,你心里比我们清楚。没有足够的证据,组织上也不会对你采取双规措施。这是组织上给你的最后机会,希望你能珍惜,争取从宽处理。如果一定要等到检察院批捕令下来,哼,就不会对你像眼下这样客气了。”
孟昭德又点头:“我明白,明白。我一定争取从宽处理。”
黑脸说:“把你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什么也不要留。”
孟昭德摊开两手:“我没啥啦。”
黑脸说:“是不是非得让我们搜身?”
孟昭德便自己动手,把身上所有衣袋都翻出来,一叠票子,一串钥匙,链上带着多功能的瑞士水果刀,衣袋底还啪哒一声掉下一颗蓝莹莹的菱型药片。年轻人弯腰捡起来,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孟昭德扭捏着不答。
黑脸喝道:“问你呢。”
孟昭德只好说:“是……药。”
黑脸说:“我还不知道是药。什么药?”
“伟哥……”
黑脸冷笑一声:“你进歌厅带这玩艺儿干什么?”
“是准备跟老婆时用的……”
“哼,鬼信。”
“不信你们去问我老婆。”
白脸不耐烦地打断:“往正经事上说。”
黑脸便又说:“手表。”
孟昭德又把腕上的瑞士撸下来。表是一个蟹商送的,还附了发票,四千美金,值三万多人民币呢。
黑脸把那几样东西都抓进手里,说:“东西暂时由我们保管,你想自己的事吧。”
这一夜,孟昭德岂能安然入睡,躺在宽阔松软的席梦思床上,只觉脑子里像气球一样膨胀,两耳嗡嗡作响,眼见是血压上来了。套间的门掩上了,却听那边的电视机一直在响,客厅里有人值班,看电视熬长夜,也不知是三个人中的谁。又在六楼之顶,想逃跑是不可能的,除非长了翅膀。心里乱上一阵,便开始往实质问题上想,是哪儿出了毛病呢?是谁举报的呢?凡是双规,必有因由,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呢?在宣布双规的同时,他们是不是已去办公室和家里抄过了呢?这一想,脑门上不由又渗出一层冷汗。办公室的柜里有十万元钱,家里储蓄折和现金也不下百十万,事先从没料到会有这一步,真要被他们抄去,就一定要问收入来源,说不清楚的统统都要视作不明财产被没收充公,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编派出进钱的因由,那不光是没不没收的事,说不清的便是受贿贪污的罪证啊。
自己生病住院,老爹老妈死时办丧事,下边人随的礼,都可算人情往来灰色收入,但那打了滚儿翻个番往高数上说,充其量也就是三五十万,一个科级小乡官,谁肯送那么大的人情?说多了又谁信呢?剩下的那一半该怎么说?既被带到这里,正如人家所言,不可能盲人骑瞎马,自己说什么人家信什么,自己不说的人家便一无所知。那自己说什么呢?一点儿不说,必被视为抗拒难以过关;竹筒倒豆子,那又是傻逼所为,自己往大牢深处钻。那就避开重的说轻的,躲开大的说小的,只说受贿不说贪污,比如把谁谁谁调入乡机关收了两万,提拔谁谁谁当了河蟹交易市场主任收了三万,安置谁谁谁到乡中学当老师收了一万,为哪个蟹商免税放行收了两万……这个数控制在十万左右最好,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万,超过这个数,就要被判刑了,眼下最好的结局是没收一部分受贿款,然后“双开”了事。咬死牙关不能讲的是建乡政府办公大楼的工程回扣款和建河蟹交易市场征用土地时偷吃下的那一块,那两笔就是五六十万。只要不进监狱,“双开”便“双开”,这辈子就算没亏,落到手里的还有几十万呢,这个破乡长即使干到退休,才能挣多少工资?有那几十万,日后去当蟹贩子,也算有了本钱,就是啥也不做,在家坐吃等死享清福,加上利息也够活了……哦,对了,就说于旺田的卖蟹款还没交吕书记呢,谅办案人也不会去找吕国清核实,即便去核实,吕书记也自会搪塞,他能轻易承认自己不劳而获白得了几万块钱吗?给于旺田交的九千元钱特产税,自己也让税务所以扶贫的借口减免了,那钱也暂放在了自己手里,这事虽说不堂皇,但总可让那些人少没收万来元钱。以前可以不把万儿八千当钱,从现在起就要分是分毛是毛寸土必争了,那不光涉及没收数额,还事关量刑呢,既已落水,抓根稻草也给活命一分希望啊……
时已过夜,没有表不知时间,只听宾馆后面传来隐隐的公鸡打鸣声,想必是后厨备的。外间门响,听白脸的说话声,你去睡一会儿吧,快天亮了。
这回知道值班的是黑脸了。黑脸说,你先去抱条毛毯来,后半夜冷。
白脸说,放着现成的空调你不用?
黑脸说,摆弄了一阵,没整明白。
白脸笑,活该挨冻,快去睡吧,天亮还审案呢。
接着便听脚步声,又听门响,看来他们另开了一间房,就在对面或隔壁。妈的,眼下的事也是怪,还整出个双规,双规就双规呗,还专把人往让人难找难寻的高级宾馆里整。若是不摊这种事,跑到这儿来休息一些日子,肥吃肥喝供着,又有温泉泡着,倒能养出一身白膘呢……
该死该活听天由命,有病大不了一死,也该睡上一觉了。人家是三打一,车轮大战,明天清清醒醒地审自己,自己若是迷糊颠倒的顺嘴胡说,可就要坏大事了。孟昭德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