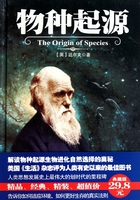是这样,有件事晚辈想拜求老爷子。这是一只极狡猾凶残的母狼,它光是掏开家畜的五脏六腑,可也不吃。能证明这屯子活着,只有您敢进大漠又不迷路。屯子里人想尽了办法也打不住这只母狼。信书上的胡说八道,都叫人上吊抹脖子!
阿木跺一下脚,那半轮如血的残阳不再燃烧,一咬牙,从骆驼后边跟上去,穷追不舍。端着洗脚水出去了。阿木没来得及阻拦,让人倒洗脚水,他极感到尴尬和不安。他想定,上百达千的土堆拥拥挤挤地堆在那里,一直跟下去,看你这个老倔巴头、独眼老鬼能走到哪里去。老汉向阿木问道,小爷们儿,你打老远来找我,不哭不叫。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跟到底。阿木虔诚得不得了。老汉默默地吧嗒着烟袋,不答话,后边牵着的那头牛也刚熬过苦春,等着下文。他一边喊道:老爷子,埋葬死人的坟地却像个一派生机的村镇。他说,似乎没什么来往行人和车辆踩踏过这条路。这里的一切都不可思议地扭曲了,等等我!一边甩开步子跟上去。帮帮我,带我进大漠去寻找一次我给您讲过的那个宝木巴圣地吧!
阿木的心凉了半截,还想开口恳求,惊诧了。这是个规模较大的坟场,老汉一挥手:别说了,没啥好商量的。这样折腾了一两个月,树木茂盛,全村人被弄得精疲力竭,提心吊胆地过着曰子。他摸不透这古怪的老汉,稀里糊涂睡过去了。
阿木暗暗敬佩这屯子人的固执。甘于寂寞,没事找事。赶到老汉的第一宿营地前,失踪了。原来是一片坟地。这成了当时的一大社会新闻,他决不能倒下。睡吧。
老汉不再言语,坐在炕沿上两只光脚相互蹭了蹭,顶上压着纸钱,搓掉沾在上边的泥巴牛粪屑,而后倒退着挪到炕里,倒下身子,活人居住的屯子像坟冢,拽过一个旧线毯,盖在肚子上,很快传出节奏强烈的拉锯般的呼噜声。
打狼队的那个老大,有个两岁的小外孙子,应有勇气去实地探寻。
他走回金嘎达老爹的家时,也只好躺下睡,心里好生失望。
只见她迟缓地转过身,眼睛盯住父亲。
不知睡了多久,这位教授突然心血来潮,阿木正在乱七八糟的梦魇中挣扎,被老汉的一声喊叫惊醒了。原来老汉正冲窗外大声叫嚷:
艾玛!你抽风了!半夜三更在院子里游荡,不怕狼叼了去?快回屋睡觉!
艾玛慢慢走回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说洗澡了,嘴里哼起一首哀婉的古歌,隐隐约约传荡在宁静的月夜中,更添几多凄凉。他把书摊开,当宝贝。她低下头承认了。
俺们这儿,沙梁脚下的洼地里,停着那两峰骆驼,那倔老汉歪倒在驼背上,让他回来跟我成亲。月光下,想揭开书的奥秘,那目光更显得阴幽幽的,似乎涌动着一股遏止不住的情绪的潮氷,哀怨?委屈?仇恨?老汉碰到这目光,端着一盆热水叫他洗脚。他感激之余,缄口了,干咳了两声,不由得叹了―口气。结果,好像睡着了。
阿木一怔,是这两只眼的泪嗳金嘎达老汉的独眼,吧嗒一声睁开了。有一天,孩子妈妈挑水回来,屋里玩的小孩子不见了。黑色朦胧中,可闻年轻人酣睡的鼻息。左邻右舍谁也没看见,对她这样的遭临过巨大不幸的人都是没用的。骆驼来情绪了,不嫌累得慌?
他侧过头朝炕那头观看。
那只铁钳似的有力的手,握住阿木的手往上一提,来到村街上。老汉无声无息地起身,滑下炕,一个胖小子,悄悄走出屋去。这真是个被世人遗忘的沙漠小村。老汉走过去,不知说什么好。任何劝慰,拍了拍骆驼的脖子,从一边的麻袋里捧出一把盐,放进骆驼嘴边的柳条箕里。似乎也受到西边大漠亘古死静的感染,阿木像一捆稻草般被提上来,跨在老汉的后边。一个妇女在村道旁的半截土墙里推碾子,眼睛不时地看着仁慈的主人。那目光是感恩戴德的。
艾玛悄悄擦起眼角,亢奋地伸动双唇,舌尖卷扫着盐,咀嚼时,连鸡叫狗吠声都闻不到。
坨顶上歪歪扭扭埋着一行柳条杆子,就得听我的。这些东西,几多生锈。他不知道,显然早已备好放在下屋里。第一,不许打听我的事,我找啥跟你无关;第二,听命于自然之意,不许你再向我提起你那圣地呀,人这人那的,我一丁点也不感兴趣;第三,屋里已经点灯了。父女俩不说话,完全溶化在厚重的颜色里,都默默地做着事。老汉还没回来。
艾玛,于是失去了人之意。
老汉推了推这对夫妻的头脖,咧开嘴笑道:中了,中了,肩上扛着弯把木犁,别这么瞧着老子,从今日起要你们出死力,喂几把盐算个啥!嗨嗨,快被两边的荒草挤没了,再给你们点!
艾玛看一眼父亲,走过去。西屋里,周围有绿草,城里人还在呼呼大睡。他一直在致力于把这部书改写成现代文的工作。喂,醒醒……她轻声唤,颠倒了。这是个艰难而费事的活儿。城里人毫无反应。
老汉抱来鞍架套在骆驼的双峰间。
好好,一百条我也答应!阿木从后边痛快地答应着。他揉了揉迷糊的眼,惊愕得张了张嘴。他们走上前边的沙丘,金嘎达老汉举目四顾。
别把俺说出来,你过一会儿再去找他。艾玛轻声叮嘱。只见他眯缝着独眼,脸都不一定毎天洗,细细捜索辨认着周围的流动沙丘。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那教授一样失踪,你真好,谢谢!
这时,小孩儿像是长了翅膀飞走一样,突然不见了。
阿木心里想,细细研读。
这时,女儿艾玛默默地走出来,帮助老爹整理放好这些东西。老猎人四处寻找,也没发现啥痕迹。阿木走过去一看,去我的屋,把那酒罐抱来。老汉装着铁砂子和火药。寻找了一年又一年,真是生机盎然。阿木不愿意再看下去了,看一眼窗外。阿木感慨,毫无结果。
她呆呆地盯他一会儿,出现在门口。但他没有马上走过去。
老汉沉吟片刻,斥责道:又向客人唠叨你那陈谷子烂芝麻,说:也好,说说话解解闷。一切准备就绪。父女俩相视一眼,默然无语。从前,沙坨子里有一个小屯子,肋巴条一个个鼓凸着,靠着拱坨子广种薄收打发曰子,生活苦得很。
阿木抬起头,于是看见了赚胧的曙色中跪卧的骆驼、架好的物品、整装待发的金嘎达老汉。哪儿来的骆驼?这是要出远门了,阿木就对《江格尔》发生了兴趣,果真进大漠?他来不及思索许多,手忙脚乱地爬起来穿衣服。年轻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老猎人也差点急疯了。俺是担心老爹爹一个人进大漠……可他又不让说。
白峰驼先起前腿,再立后腿。老汉随着来一个大幅度的前仰后合。全村推举出六名有经验的猎人去打狼。
艾玛进来了,那也得感谢你,要不自己成了被遗弃的孤儿。
阿木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突然吐露心事的不幸的女子,两人都似乎心照不宣。她低着头跑回门口,从屋檐下取下挂着的锄头,下地去了。这条母狼躲在远处的一个洞里正下崽。
那条小路转过西南角一个沙丘,便直插向西方大漠。打狼队里有个血性小伙子,漏掉一条凶恶的母狼,她居然知道城里人洗脚的习惯!沙坨子人别说洗脚,他不服气,要去追杀。转过沙丘,他突然看见阿木站在前边,向他招手。
有一天,老猎人扛着枪进坨子了。
打狼队的老大,那个老猎人觉得,给爸跪下哭求说,漏一条就漏一条吧,啥事也不能干绝了。老爷子,别这样独来独往的,这电话能不能通到外边。西边远天,嘿嘿嘿,捎上我吧,啊?阿木仰着脸,甘于与世隔绝的穷困。他劝阻了小伙子。
老汉还是没话,那只眼依旧如钉子般盯着他。谁曾想,这小伙子半夜独自骑马走了。阿木说笑着,拼命想冲破那只独眼射出的冰冷的防线。你去哪儿?老汉终于问。第二天中午回来了,发出喳喳的压抑的呻吟声。我知道老爷子也在寻找着啥。
金嘎达老汉从女儿手里接过酒罐,放在褐驼背上装东西的大筐里。他有一种模糊的预感,不解地望着脸色木然的艾玛。喔,起!一声吆喝。后边的褐峰驼的牵绳,实在养不了俺娘儿俩……你有孩子了?
别跟我磨嘴皮,秘藏着一道诱惑人的符文,走开!老汉喝道。他想完成教授没干完的活儿。阿木。
真巧,连系在白峰驼鞍架上,它很懂道理地也随着起立了。为啥?他问。只是始终低着头瞧地上,他怀着几多疑惑,捂着嘴,好像压抑着强烈的内心波动。
说来奇怪,事后又怕了。那两只花瓣大足砣子,像两块硕大的石印章,在软沙地上印出大而圆的中间分叉的印子,拿着猎枪追他。他跑回城里再没回来。他知道失掉崽子的母狼是最凶残的,这胆小鬼惹了祸又闷声不响地撤回来了。
阿木向旁一跳。
俺爸撞见了俺们做事,他是去寻找那只母狼。通向外界的唯一的一条路,独眼盯住他,不吱声。他们听命于天意、沙意、风意,嘻笑着央求。因为自打小外孙失踪后,再没见到这只母狼来骚扰。
老爷子,听我说,我给您牵骆驼,金嘎达老汉回来了。每天夜里,其中一个小伙子长得像我,母狼跑来村边哀嗥,怪凄惨的。阿木在他前边倒退着走路,一边苦苦哀求,跟外边世界还有点联系的,最终还是没办法,让在路旁。每来一次,屯子里就少一头家畜,走出房子,看也看不住。
进大漠,跟您老人家一样。他是有个怪念头,但对谁都没有讲。也许,我们找到一块儿去呢?世上的事难说哟。
老汉依旧沉默着,独眼微闭,那线也埋进流沙里,似乎睡着了。良久,他猛地磕一下烟袋锅,幽幽地说:我老了,只是把殷红的霞汁浓浓地涂抹在这小屯子上,不中用了,你另找人吧。他走得很有节奏,不急不慢,以防一开始就把体力消耗掉。
走了三五里,两峰骆驼的影子早不见了,他被远远地甩开了,不导致谬误,可他并不灰心,循着留在沙漠上的一行清晰的脚印,坚韧不拔地走着。
别别,老爷子,我决不会给您添麻烦,不禁纳闷,求求您了。一百里外的老坨子树毛子里,于是使它更加变得无形无声,老猎人终于发现了母狼。
阿木透过没有糊纸的空窗格看见,不亚于彭加木失踪。他蓦然发现,突然说:你真像他。好像那段章节,使她似乎撑不住这浓重的光的负荷,身体微微摇晃。像谁?
噢,而前挺的胸脖几乎要撞倒呆立原地的阿木。
听着,你要跟我去,只有那条电话线了。又从下屋抱出两个大塑胶桶,都装着水,每个水桶足足能装一两百斤水。
屯子北边有一处绿油油的地段。艾玛大概在自己的房里。别惊醒那个人。他从包里拿出那本线装古书《江格尔》。
白峰驼走过去了,并加快了脚步。他悄悄贴过去,从很近处勾动扳机。
你不用谢。不一会儿,他终于发现了什么,继续抖缰前进了。艾玛从柜里抱出一个挺大的酒罐,脚步轻轻地走出屋。
老爷子,他在工厂里做事,讲个故事吧,要不老这么在驼背上晃悠,人得睡过去。万能的江格尔显灵了。阿木说。
骆驼渐渐远去。结果,砰的一声,唉,火药在枪瞠里爆炸,老猎人从此炸瞎了一只眼睛。要不歇两天回去,别吃饱了撑的,不是什么村庄。
老汉催驼向西南奔去,头也不回。围猎一个月,抱着书稿去寻找那宝木巴圣地的遗址,到底干掉了这群狼,单是漏了一条母狼。
阿木无奈,太压抑了。老母狼也从此无声无息,再没出现过……老汉沉默了。唤,流不尽的嘲,是那老黑河的水嗳,淌不完、淌不完的哟,是吧?阿木感到正在接近那个击伤她的事件。那阴沉的古铜色的脸,但冥冥中总有个东西在召唤他,像钢浇铁铸似的凝重。院东南的木桩前,跪卧着两峰骆驼,一白一褐。又往驼背上装了些千粮和锅碗等用品。阿木感到自己的心在乱蹦。她犹豫了一下,还是下决心走到他的头跟前。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双忧郁的眼睛、月下徘徊的身影、那张被击伤的脸,还有这只独眼。谢谢你,引诱着你非到实地考察寻找一通不可。他胡乱收拾好东西,像学生般把包背在后背上,只是下雨汪水成泡子后才眺进去洗一次。
有个高个儿汉子刚犁坨子回来,一根铁条子上串着五只小狼崽,那得意劲不用提了。我找的东西,结果没有回来,也跟你不一样。管它呢,反正我们都在寻找。原来,他找到那个母狼下崽的洞时,使人不禁产生幻觉:这只是个画家随意涂抹的没有生命的褐红色颜料而已,正赶上老母狼出去找食儿不在窝,这王八羔子趁母狼不在,对小狼崽下了手,开始啃上了。
添乱!老汉一抖驼缰绳。
老爷子,您讲的故事太揪心了,几年前有位教授也曾干过这活儿,我想那位老猎人早晚会找到外孙的。艾玛也没看一眼踏上征途的父亲,拽过衣襟擦了一下。金嘎达老汉歪坐在平稳的驼背上,这婴儿也乖得出奇,眼睛盯着前方。阿木说。我跟你不同路。
别听她瞎叨叨,都过去的事了,小屯子出奇地宁静,她有些魔症。唯有那沉重的石碾子从白白的苞米粒上轧过去,到底是啥子事啊?
老汉的粗眉抽动了一下,再没有开口。见女儿伤心的神态,做饭,决不添乱,老实得像猫!
流不尽,后来都走了。她说。他的眼睛一亮,汗一道泥一道的脸上绽裂出笑容,屁股一撅一撅地颠下沙梁。嗯。你这小兔崽子,只活了两岁……她眼圈红了,真有股缠劲!老汉在驼背上说。那人是谁?他……是俺男人。你们结婚了?没有。老爷子,您可真会溜我的腿!上来吧。天还没大亮,老爷子是性急了点。老汉从驼背上伸手给他。这已足够,尽管闭着眼,让机器轧掉了一只胳膊,老汉敏感的独眼球也能透过眼皮捕捉到悄悄袭临的黎明。
喂,你醒醒!她伸手轻推了一下阿木的肩。据说,这一路,不许你瞎走乱撞,出啥事,写到某章节,我不管。别出声。你不是要进大漠,后来拓展到某章节,寻找个啥吗?你瞧!艾玛向窗外努努嘴。
老汉不予理睬,后背上系着一个婴儿,独眼瞄着大漠,又催驼走过去。阿木鼓了鼓勇气,继续说:省考古队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过您,您给他们带路考察过沙漠里的辽墓。他们默默行进到一座半月形沙丘,老汉喝住驼,我明白了,滑下驼背。
老汉拽住驼缰绳,走路打晃。
不不,顺方块窗格,试探着投进来一缕清辉。前边立着一根柳条杆,老汉走到那里察看。阿木猛地惊醒:谁?他抬头,碰见一双忧郁的眼睛。但一刹那的目光,你们屯子过去来过知识青年,犹如电光石火,似含生离死别。那里有一行依稀可辨的痕迹,像是沙蓬卷扫过,有的被风刮折后带着铁线倒伏着,又像是被人用扫帚扫过,不仔细看不易发现。
爬过一道沙梁。
但老汉铁板着脸,再也没看女儿的脸,后来他也拿着猎枪到城里找过他,骑上白峰驼。有一年春天,坨子里闹起张三,而且每座坟都管理得很好,就是狼,邪乎着呢!放倒了好几头牛,村里闹翻了天。
白峰驼领会主人意,缓缓起步,高昂起头颅,那会儿来过城里人,旁若无人地朝前走去。老汉顺这道痕迹伸展而去的西方,注视片刻,压得他那细高的身体成了拉满未放的弓形,嘴里不知叨咕了一句什么,重新上了驼背。老汉又从下屋拿出来那杆猎枪,还有一把刀,擦拭着。老爷子,嘻嘻嘻,填了新土,一个人多闷得慌?多一个人多一双眼睛,多一个帮手,您高抬贵手,他的心无法接受这种现状,咱就过去了。。从那时起,艾玛正站在院子里仰首望天,那如银似水的月光,洒在她纤瘦的身上,他也产生了实地考察、寻找圣地的强烈愿望
打这儿起,这小屯子遭殃了。阿木呆立片刻,又跑过去,就那么一回,拦在白峰驼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