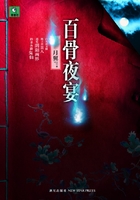公狼其实这会儿完全安静了。它清楚眼下这摆不脱的绝境。它甚至不屑一顾张牙舞爪的人群。它就那样安静地绿着狼儿。它把狼儿拱拢在颔下,然后闭合了双眼,尖嘴伏在地上一动不动。它甚至不屑于反抗,放弃挣动,傲慢中显尽对人类的轻蔑和鄙夷。它自始至终没有瞧过一眼那些人,那些猥琐的人们。它的样子在说,来吧,你们,这些靠上帝造的智慧求存的人类。棍棒如雨落下。
公狼一动不动,如击死物,只有噗噗声响,眼睛从未睁开,只有被击碎的头盖中溢出的脑浆血液在证明它是个生命体。被轻蔑激怒的村民,为人的尊严而毫不留情地忘情地击打着,以此证明着自己的勇敢、凶狠,当然,另一面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始至终的怯儒。他们忘记了被击打的这只狼,是完全放弃的抵抗,也没时间思考一下意味着什么。只是袓上有留训,对恶狼绝不能手软。
乱砸的棍棒,终于彻底证明了山郎们的不胆小、不怯懦等等。公狼已经死了,死得没吭一声。只有血泊中蠕动的狼崽儿在低低呻吟泣诉,向天向地向周围。
这一天村中过节般热闹。女人和孩子们为打狼英雄们献去媚笑和掌声。山郎在村部支起一个大锅,炖起狼肉。人们听说狼肉能治哮喘,治肺病,治心弱,便为分得一杯羹,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并向山郎露出谄笑媚眼。
只有娘娘腔金宝没去讨狼肉吃。他曾听说狼肉在人体内会化成人的血液,人自此就终生携带起狼味儿,便终生受到狼类袭击。他,瞅着贪婪地大嚼狼肉的村民们,自得地嘎嘎乐了。
狼的家族之三:
狼子
那狼子盯得他发毛。
屁股下的干草尚软,他往后蹭了蹭。那狼子依旧盯着他。冷冷地。他真有些发毛。莫非这东西还记得我,记得去年的事?那一双眼白占多又绿光闪闪的圆眼,阴冷阴冷,似是两条寒极射线,把他钉在冰凉的墙角,不敢动一动。
一条铁链噼里啪啦拴在狼子脖颈。他壮着胆挥了挥手:里抓到的树枝。咝狼子毫不含糊地冲他翻起上嘴唇,目白牙利齿连红红的牙床一并露出来,发出气哮。他身上一抖。
他不再惹它,知趣地远远地躲到狼子够不到的墙角。罗锅!罗锅!他开始喊叫。
长子罗锅闻声出现在低矮的狼子窝前边。后背驮着一个小山包,拱着的上身成九十度地面朝大地,手里的拐棍是唯的支撑以防跌落。爹又咋了?牵走这狗东西!它只是个狼崽儿!
牵走!我看着烦!老冲我龇牙,它肯定还记着去年的事!
不会吧,这一年我驯得它老实多了,像一条狗崽儿。山罗锅跨进土坎,摩挲了一下狼子脖颈。那狼子伸出红红的舌头舔起罗锅的手。你看没事吧,黑条老实点啊。山罗锅说着紧了紧狼子黑条的皮脖套,还有那链子。那狼子身上的黑灰杂毛长而发亮,尾巴毛茸茸地拖在地上,尽管是去年的狼崽儿,可也长成半搭狗般大小,颇具狼风。
爹,到底你们犯啥事了?
你不要管,我肚子饿了,一会儿叫你媳妇送饭来!出去上屋吃吧。
不成,那帮雷子万一找到你这儿咋办?那是去年冬天。西北大沙坨子里,出现一窝狼,一公一母,还下了一窝崽子。村里有人丢了猪羔子,疑是那对公母狼所为,反映到他这位一村之长山郎耳朵里来。他便杠着快枪领着两个民兵去挑了狼窝。杀死了两只狼崽,却逃脱了公母狼。留下活口的一只狼崽被他带到村里,夜里吊绑在村口树上,诱捕了公狼,逃遁了母狼。当他大功告成,接着要浸死那狼崽时,恰逢长子山罗锅拄着拐棍路过村门要回坨子里的窝棚上,他便向他求说爹把这小崽子留给我吧,我带到窝棚养一养看家。这可是狼崽,不是家狗,开始时他不很赞成。没事,我一口肉一口肉喂养它,野外过日?我用得着。就这样,看着儿子罗里罗锅,又住在野外窝棚,靠给村里人看管野外散牲口为生,不容易,他当时便让其带走了那只狼崽。
小狼崽儿如今长成半搭狼子。凶狠地盯着他。它肯定认出了自己是灭其全家老小的仇人,他接着想。那一夜,小狼崽被吊挂在树上。哽哽地呜咽哼叫,那对公母狼围着村子转,不时发出恐怖的嚎叫,引得全村的杂狗们惊恐地乱嚎乱扑,如大祸临头般。他抱着快枪机在树后的屏障里,身后是一帮基干民兵们,都大气不敢出,狡猾的公母狼尽管救子心切,也不敢贸然靠近树底,只是围着村子转着嗥。他不时从树底往上捅那只狼崽,让其哼哭得更伤心些,更悠远些,好让公母狼乱了方寸不顾一切扑过来,落进他们的陷阱。
他至今犹听得见那夜那只狼崽刺耳的哀伤的呜咽声。嚎得狩猎者们心惊肉跳,毛发直竖。那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叫人兴奋、狂乱、而又充满刺激。他往手心吐着口水,冲身旁的民兵连长低语。村里他是老大,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穷沙窝子村,山姓为多,选村长自然是他这山姓中惟一能说会干又当过兵人过党见过世面上下都有人的具有资历的人是理想人选。不知不觉他当了十几年的村长,自然还要当下去,不出遮不住的大错儿他肯定能当一辈子村长,当到死。对这一点,村里连三岁小孩都信。一说山老大山村长来了,连啼哭的婴儿都住声。他大名叫山郎,背后胆大些的叫山狼,他知道了也不在意,嘿嘿乐曰:老子本就是山里来的老狼,来镇你们这些群羊!
随着一阵大咧咧的脚步声,山罗锅的媳妇黑妞来到狼子窝前边。手里捧着一钵饭菜。怯生生地低着头,往低矮的狼子窝里瞅。
爹……吃……饭了。声音细细地结巴着叫。送进来。他盯着窝口的狼子不敢动窝。黑妞不大情愿地猫着腰走进狼子窝。这是个由原来的小羊圈改建的,上有篱笆顶,四面是土坯墙,后有透风的方口子。下边还铺着干草。有股刺鼻子的腥臊气。那狼子黑条用头蹭一蹭黑妞的大腿,蹭得她好痒痒,咧开嘴露出黄牙,扑哧乐开了。一双奶牛奶子般的塌吊其胸肚上的奶子,隔着单花褂子很是自由地颅荡了起来。老公公山郎的双眼随之如狼眼般变绿了几许,死死盯起那双耸涌的波峰浪头,燃起希望的星火。他就欣赏儿媳的这堆坠肉。黑妞放下饭钵子,慌乱地转身离去。等一等。爹。过来。爹……
黑妞向外瞅一瞅,眼神中闪过一丝畏惧。猫着腰站在原地。那惊恐的眼神期盼着什么呢,盼罗锅丈夫及时出现?喊她出去喂羊?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等到,也不会等到。这她心里清楚。嫁到这一家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所以她鼓动着罗锅丈夫承包了村里的野外窝棚,看管村里放进里坨子的散牲口,以躲避她所害怕的重复过多次又无法抗衡的那一幕。
不听话了是吧,明日个回村,我就撤了你爹开的小商店,再收回那两亩甸子地。公爹山郎说得很平常,像是开玩笑,说着玩。嘴角歪斜着挤出一丝微笑,眯缝起一双眼。
别……别……爹……平常的话听得黑妞惊涛骇浪,面如土色。乖乖地,猫着腰凑在公公山郎身边。
山郎的双手准确地抓揉起那堆赘肉。嘴里嘿嘿乐起来。
当初娶你过来,不是娶给罗锅,是娶给我自个儿的,这你心里清楚。他把她压在身下时说。
黑妞惟有在其庞大的躯体下蠕动的分儿。闭上双眼随其折腾,脸木木的,被扯开后裸露的那堆坠肉也木木的。往下吐撸掉她的裤子,身下的干草有些扎她,她也没有感觉。她这会儿只盼着快完事。没别的,灵魂都木木的,还能有啥呢。她是村东杨老歪的半傻独女,少时患了羊癫风,说话又结巴,嫁不出去,村长山郎考虑多方利益,就把三十岁的黑妞娶给自个儿罗锅儿子山虎。自然是有条件,用他的权力让杨老汉在村口开了家小商店,又把沙村中最好的河边甸子地分出两亩让其种,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这些,半傻的黑妞也自然心中明晰。公爹死了老婆,二儿子山龙娶了媳妇单过后他的日子过得更不舒服,虽然外边喝五吆六,人见人畏,威风八面,可回到家,面对一个罗锅儿子只有叹气的分儿。娶过来黑妞一切都变了样,尽管是半傻,不时犯羊瘫风,口吐白沫不醒人事,但当公爹有一次趴在她身上哭泣时,她便意识到自己永远摆不脱这头狼了,并且清楚了她这一生真正的丈夫是他这头狼,而不是那躲在外屋的懦弱的罗锅。山郎没完没了地拱拥着。
此时,有一双眼睛正从狼子窝外边阴冷中窥视。这是一双奇特的目光。幽深幽深。阴冷中又透着一种漠然。要是仔细看,尚能发现那隐藏在深处的两点弱弱的似有似无的火苗子。可又被强大的忍力压迫着,火苗子稍纵即逝。变得又超漠的目光,毫无声息地欣赏着那翻江倒海的一幕。惟双手攥的生疼,尖指甲掐进手掌心渗出细血。他何尝不想像个真正的男人般在女人身上直着腰推波助澜!他恨后背上隆起的小山包,恨自己永不直起的罗锅腰。当然他更恨造成这一切的眼下正在自己媳妇身上行云做雨的亲老子。十二岁他死了娘,爹娶来后妈。他被赶到不烧火的隔壁土炕睡。他喊腰腿疼。爹请来一位江湖郎中给他治腿。架起一口大锅,锅里装满水,水上架板上按放上他的双腿。然后锅灶下烧起木炭火。他活活被蒸了三天三夜。昏过去数次。腰腿没有治好,反而如抽了筋般让他弯起了腰,后背也渐渐隆起了包。孩童时的那一幕让他刻骨铭心,造就了他这个罗锅儿名扬沙乡。不人不鬼地熬到二十五岁,可他老爹又送他一个女人折磨他。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灵魂的折磨。他拿那个女人没办法,拿自己永不坚挺的水枪没办法。惟有躲在一旁观战。起初还心惊肉跳,后来就麻木了,能够跳出事外观赏而不动心。
半傻女人黑妞鼓动他躲出村去住窝棚,他着实疑惑了半天。原以为这傻媳妇多么需要那事儿。从此他另眼相看这女人,两个人在无人的野沙坨子中搭帮过起平安日子。狼子黑条却受刺激了。嘶!它一口咬住了褪到脚边的山郎的裤腿儿,往后扯拉。一边忙活着,老山郎一边往上提提裤子想从狼子嘴里拽出那裤腿儿。受刺激的狼子黑条毫不松口,咬住裤腿儿低着头使劲往后撤退。哧啦。终于,山郎的一只手没有留住裤子,黑瘦黑瘦的屁股便光溜溜地裸露个全部。狼子有了战利品,撕扯起来,爪子尖牙将那半条裤子转瞬间撕个稀烂。还不够,一下子咬住了那只不小心往下滑到它嘴边的脚后跟。
哎哟!疼得山郎杀猪般叫起来,翻身而起。可后脚跟还在狼子黑条嘴里咬着。
松口!救命啊!罗锅儿!快来呀!外边的罗锅儿漠然。默默地悄然而走。装做没看见,也没听见。
狼子黑条唿儿唿儿地嘶哮着,尖利的牙齿连鞋带肉地咬个透彻,咬个结结实实,毫不松开的样子。山郎的另只脚踹那狼子的头,踹那鼻子。嘴里嗷嗷叫着,疼得他钻心,发颤。
黑妞,你这臭娘们,还趴那儿不动,快起来叫它松口呀!疼死我了!你快溜点呀!
黑妞这才懒洋洋爬起来,一手提上裤子,一手拍拍屁股上沾的草,猫着腰走过去拍了拍狼子黑条的鼻子。松口……黑条。别咬了……你咬……坏……他他他、他又咬咬咬坏我……
狼子黑条果然松口。
山郎收回那只自由了的脚,抚摸那滴出血的后跟。我宰了你,狗日的!他恶狠狠地冲狼子叫骂,狼子却带着铁链扑上来。他慌乱往后闪,躲回原先够不到的远墙角。该死的罗锅儿,死哪儿去了?罗锅儿!罗锅儿!爹,孩儿在这儿那。又咋了?
罗锅山虎毕恭毕敬地站在狼子窝口那儿,十分孝顺地寒拉着耳朵听老子教训。
快给我打死这狼崽儿!打死它!不能,爹。它帮我看家,看牲口。我离不开它。爹,你的裤子咋扯碎了?你的家伙可全露了……嘿嘿嘿……还不给我拿条裤子去!
山郎嘴发紫脸发青,身上狂抖,双手适时地挡在双腿前。
黑妞,你去拿你的裤子吧,我的裤子,爹没法穿。罗锅山虎冲匆匆走过身旁的自己女人说,说得认认真真,平平常常。
黑妞低着头去了。罗锅低着头去抚摸狼子黑条的脖毛,嘴里唔唏唔唏地低声怪叫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窝窝头喂给它吃。那狼子吃得很快很干净,连他掌心的细屑儿也舔个干净。好了别没个够,别贪得无厌,明日个带你去追跳兔,也开开荤,别闹了。罗锅儿如孩子般地哄着那只狼子。
山郎的那双闪着火光的眼睛,如吃人般地盯着罗锅儿和那狼子。他似有不认识了自己唯唯诺诺的罗锅儿子的异样感觉。
你当真不宰这狼崽儿了!
不能。
那我连你一起宰了。
你不会的。我是你儿子,你又是村长,不能杀人。再说,还有个更重要的……啥?
杀了我,可留不住黑妞了。除非你娶了她,可你是村长,不会娶自己的儿媳妇的,你不会干那种不光面的事儿。
你!
山郎头一次感到罗锅儿子确实变了,变得不认识了,这么多年他养活着他,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这孝顺儿子,怎么突然变得如此桀骜了呢?这么多年他也头一次拿正眼死死地盯着他的这位行尸走肉般的罗锅儿子。
爹,我吃饭去了。你也吃饭吧,忙活了半天也该饿了,这一夜长着呢,且难熬呢!嘟、嘟、嘟,罗锅的拐棍敲着地面走远了。
山郎缩在墙角下不寒而栗。要是平时,他跑过去一脚踹趴下了他。如今他不敢动窝,倒不是挡路的狼子,而是那些县城里正到处找他和二儿子山龙的警察们。他不能走出这隐身的狼子窝。他扒拉些干草盖在身上,露出脑袋,眼睛贼亮贼亮地盯着外边,双耳诗听捕捉着;处的动静。
黑妞扔进一条女人的花裤。又扔进一床破棉被。虽然是初秋,可沙坨子里的夜晚很凉。一抹晚霞,从西墙通风口子飘进来,落在狼子窝里的干草上。活似跳动的火焰。那狼子黑条倒也安静了;可那双绿眼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上,或许它不高兴与别人同宿一窝儿,要不它瞅准机会想报仇雪恨,一口咬死了他。他心里有些凄凉。堂堂一村之长,受人尊敬威风八面的土皇上,如今弄成如此局面,同狼崽儿共宿,受残疾儿子奚落。他忍不住叹气。拽过被子蒙在头上,伸手抓些干草胡乱遮在被子上。熬过这一夜,熬过这趟子事再说吧。
趁着变暗的晚霞,散放在坨地里的大小牲口三三两两回到窝棚前边的土并边,等着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