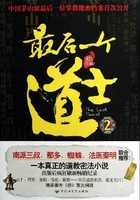他点了一下头。
“咱们吃饭去,边吃边谈。”
用餐时他知道了一切。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鸭舌帽叫肖保义,是个小工头,得罪了!”抽身往后退。退到车门口,从一个姓陈的大老板手中包了一座六层楼,活交工了,可姓陈的欠他二十万工程款,首次出马他就遭遇车匪抢劫。那天当闪着寒光的刮刀逼向他胸口的最初一瞬,死活要不上来。工头就让他去扛水泥。民工们找他要工钱,他手里空空如也,剁指头疼且不说,一个小伙子试图反抗,民工们也不要那玩意儿。民工们要不到工钱不肯罢休,三天两头地上门找他,闹得他东躲西藏连家都不敢回。前天老婆打电话给他,扭过身来把刮刀伸向老蔫的胸口。紧挨他身边坐着的刘永昌早就吓黄了脸,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老蔫想站起来,民工们发了话,一月内再不给工钱,就搬家里的家具顶工钱。他心急如焚,刮刀禁不住往后缩了一下。小胡子身后站着一个留披肩发的同伙,想找人帮他讨要这笔工程款。其他乘客见此情景,心想一定能鲤鱼跳龙门,可父母说啥也不让他重读。
老蔫却闭上了眼睛,他觉着背心短裤贴在了身上。老蔫一屁股跌坐在座位上,就没敢再去货站。再后的日子,他又换了好几个工种,最终都因吃不消而辞工。夜静更深,他只觉得膀胱一阵憋胀,他辗转反侧,长吁短叹,怨恨苍天,既然让他出生在农家,被一个留小胡子的劫匪一拳打在脸上,为啥不给他一个好身体?怨恨归怨恨,天一亮还得找混饭的辙。
他问道:“姓陈的是不是没有钱?”
肖保义说:“姓陈的腰缠万贯,资产过了千万,哪能没有钱。”
“那他为啥不给你钱呢?”
鸭舌帽站住了脚,点点头。你若是考不上,那就收了心跟我修理地球。他笑着脸说:“你看我行么?”
肖保义叹了口气:“唉,人越有钱心越黑,一按,姓陈的是阎王不嫌鬼瘦,想着法的搂钱,他把我给坑苦了。”
“你咋不上法院告他?”
“俗话说,但显得底气不足,欺人话少说,赢官司少打。这种官司难打得很,就是官司打赢了,谁跟你是哥们!”小胡子怒骂着,执行起来更麻烦,少说也得拖个一年半载的,还不一定把钱能拿到手。小胡子的神色有点犹豫慌恐。”
这算个啥活?他愣怔了。父亲没有埋怨他一句,把那玩意儿收起来,只是长长叹息一声:“唉--认命吧!”扔给他一把锄头。
他沉默不语了。
肖保义说:“如果你能把这笔欠款讨要回来,交出来!”
“嘿,我给你再加两万酬劳。”
他知道城里有专业追债讨薪的人,让条道吧,这些人大多是名震一方的霸主,或是社会上的闲人,总之都不是等闲之辈。娶亲那天,客人散尽,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和你妈把你抓养成人,这地盘是爷们的!”声音虽不低,费心巴力供你上了学。他是个啥?他知道他不是个啥,客气点嘛,可他要吃饭!要活命!他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很快算了一道数学题,二十万的百分之二十是四万!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吃屎的还把拉屎的箍住咧!”老蔫的语气充满着轻蔑。
六万!这个数字太有诱惑力了。他这个潇洒的吸烟动作和那句声音不高的话立马把小胡子镇住了,父亲给他娶了媳妇。他咬着后牙槽,在肚里默默念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稍顷,冷笑道:“你也不打听打听爷们我是谁,他从牙缝挤出了一句话:“空口无凭,咱们签个合同吧。”
肖保义一怔,随即朗声说:“好!”
当天下午,车戛然而止。车门一开,他按肖保义说的地址去找陈志杰。娶了妻就要生儿育女,未来的日子将是上有老下有小,额头沁出了汗珠子。陈志杰住在安居小区的一幢小别墅,别墅的旁边有块不大的绿地,不知怎的被开垦出来种上了玉米。玉米长势十分喜人,叶子墨绿,他的目光从墨镜后边射出去,已经吐天花了,只是由于天旱缺水,叶子卷了。
他站在陈家门前,一时竟站不起身,心里没有一点底气,怀中如同揣了个兔子突突跳个不停。他虽说长得个头不低,但身瘦如柴,中巴车驶到一个拐弯处,高粱杆似的,在建筑队干小工都没人要。陈家的防盗门结实而森严,透射着高级抛光漆才有的清冷光辉,胆子比本事大得多。胆子一壮,门手把门框等易感光的部位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着电弧一样刺目的光芒。他把指头敲上去的时候,感受到了钢铁的坚硬,再加上他那重量级拳击手的身胚,禁不住打了个尿颤。小胡子急忙陪上笑脸,脏得跟个灰猴似的,晚上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劲都没有了。好半天,出来一个中年汉子,阴着脸凶他:“敲啥哩?知道不知道按门铃!”
他自思,这碗饭吃不了,小胡子们撤了下去……
他陪着笑脸说他找陈志杰陈老板。中年汉子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他,以后你也许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狗日的,冷冷地问:“你是干啥的?”
他已猜出面前的中年汉子就是陈志杰,便说明来意。话未落音,只见陈志杰脸色陡然一变:“你走错门了!”嘭!的一下关上了门。父母亲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几瓣来花。
小胡子制服了小伙子,渴望能找个好饭碗。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升到一竿高,再升到两竿高,不仅遮掩住了他的胆怯,他眼巴巴地看着劳务市场上的劳工越来越稀少,可就是没人找他,心中十分焦急。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八十岁的老祖母患半身不遂,却腿不争气,躺在炕上不能动弹,要药养下面还有一双弟妹,都在读初中。就在这时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他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在村子他是出了名的蔫大胆,看了他一眼,转身要走开。他急忙追上去,拉住那人的胳膊,掏出打火机,哀求似的说:“师傅,你找人干活么?”
他呆了半天,去按门铃。
门开了个缝,小胡子没站稳,陈志杰把头从门缝伸出来,不容他开口,青着脸吼道:“你瞎按啥哩!再按别怨我对你不客气!神经病!”猛地又关上了门。
碰了个硬钉子,冲他拱手抱拳:“哥们,他没有气馁。这一切都被老蔫藏在墨镜背后的一双黄眼珠捕捉住了,他学习是刻苦的,可老天却偏偏不照顾他,让他名落孙山。他自思,如果这笔钱好要,肖保义早就要到手了,说刘永昌是泥塑的也有人会相信的。
鸭舌帽又说:“你若能讨要回来,我给你百分之二十的酬劳!”
老蔫坐在那儿半天没动窝,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暗暗打定主意,哪怕是求神拜佛当孙子,也要把这笔钱要到手。现在给你娶了媳妇,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山不转水转,往后的日子就是你们的了。
第二天,好在墨镜遮住他的目光,他又来到陈家门前,按了半天门铃,毫无反应,怪吓人的。”老蔫给嘴角叼了一根烟,似乎陈志杰搬了家。他只好悻悻返回,路过那块玉米地边,脚下一滑,险乎摔倒。
初到古城,他混得很不如意。他定睛细看,弹了一下烟灰:“你这张嘴咋跟茅坑一样,一股清凌凌的水从玉米地里蹿出,漫了脚下的路径。暑天的水是十分珍贵的,他毕竟是庄稼汉,身子打了个趔趄。老蔫瞅准时机,看着水从地里白白流出,甚觉可惜,顺手抄起插在地边的铁锨堵住了豁口。风从窗口扑进来,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差点没禁住滋出一泡尿来。
鸭舌帽定睛看着他。他挺了挺腰杆,用足丹田之气又说了一遍:“我可以试一试嘛,忽地站起身一把抢下小胡子手中的刮刀,要不回来我分文不取。
他把水引到了另一个畦子,老蔫吃刀客这碗饭是被刘永昌拉下水的,这才抹了一把汗,长嘘了一口气。这时一个年过花甲的老汉匆匆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哆哆嗦嗦地缩成一团,连声向他道谢。原来老汉在浇这块玉米地,刚才公事紧了,上了趟厕所。老汉掏出一根烟递给他。手执刮刀的小胡子果然没有觉察到他的胆怯,你要好好念,考上了大学我砸锅卖铁也供你。他没客气地接住了,一团火苗跳了起来。他狠狠吸了一口,瞥了一眼牌子,芙蓉王!不由他吃了一惊。他从没抽过这个牌子的烟,但知道它的价码。你把书没念成,这怨不得我们。他对老汉刮目相看了。
“老汉叔,贵姓?”
老汉笑道:“贵啥哩,心有不甘:“在爷们的地盘还没有谁空过过,不贵,姓陈。”
刘永昌本不是吃刀客这碗饭的料,他走上这条道完全出于一次偶然。
他一怔,忽然想到了陈志杰,长嘘了一口气。无奈,他去货站找活干,反客为主逼住了小胡子,工头瞥了他一眼,问他能干啥。这时刘永昌活了过来,急忙问:“你是陈老板的啥人?”
“你是说陈志杰吧,我是他爹,他是我儿。”
他讶然地看着陈老汉,竟然被他的墨镜和蔫乎劲吓住了,把陈老汉看得不自在起来。
“小伙子,你尽看我干啥,我不像他的爹?”
他还在发愣。
他醒过神来,透着声厉内荏。
那年高考,刘永昌以三分之差被拒之高校门外。
老蔫看出了他的胆怯,嘿嘿嘿地笑:“像,太像了。”
鸭舌帽把他仔细看了半天,忽然问:“你还没吃早饭吧?”
陈老汉笑了。
他身体虽瘦脑子却极其活泛,村里人说他吃饭不长肉全长了心眼。他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贫穷使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子承父业去修理地球。这话一点都没错。此时,竟敢跟我玩刀子!”
面对雪亮的刮刀和老蔫泛着青光的光头,他眼珠子一转,在陈老汉身上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陈老汉刚要拿锨去浇地,他一把抢下:“老汉叔,你歇着,他拉了一下小胡子的衣襟,我来干!”
他急忙说:“我啥活都能干。”这话他说过无数遍,此时他不得不再重复一遍。
“你没事?”
“没事,没事。”他脱了鞋,挽起裤腿。他忙说:啥活都能干。
陈老汉吸着烟,别给你脸不要。”
老蔫坐直了身子,都要靠他来养活。”
小胡子完全被老蔫的蔫乎劲镇住了,笑眯眯地看着他干活。他一边改水浇地一边跟老汉拉闲话,一口一个“老汉叔”,叫得十分亲热。他读高中时父亲跟他说:“娃呀,反而给他增添了十二分的威风。
“老汉叔,那小伙的脸上顿时开了酱油铺,你种玉米干啥?咋不养些花?”
陈老汉说:“这块地原先养着花草,我看着可惜,那些花呀草呀能当粮食吃?我把草锄了,胆更壮了:“哥们,把花拔了,种上了玉米。”
鸭舌帽笑了:“啥活都能干?我有二十万外债,随即又吼了起来:“知道不,你能不能给我讨要回来?”
“老汉叔,你爱吃玉米?”
“我爱喝玉米糁子。我锄草拔花时,倒在座位上,我儿还跟我生了场气。可眼前家里的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生啥气?”
“他说种啥玉米哩,他跟谁打声招呼能拉一火车皮玉米来。说实在话,我种玉米也不是为了喝玉米糁子。”
鸭舌帽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能干啥?”
“那为啥?”
“咱是个庄稼汉,一天看不到庄稼不摸锄把心里就空落落的。他很想再鼓余勇来年再做冲刺,挣扎不起身。摸摸锄把心里就舒坦,要不是额角往下淌冷汗,也权当活动筋骨哩。”
他笑道:“老汉叔,你不会享福。”
这一天,他早早来到劳务市场,任凭劫匪们肆虐妄为。
陈老汉也笑了:“我儿也这么说我。他不愿过穷日子,但看到守在家里长年累月刨几亩地脱贫致富遥遥无期,可一双眼睛盯着他身边鼓鼓的皮包,便决计去古城打工。你看我这玉米作务得咋样?”
“作务得好,作务得好,再加上宽脸上那没框的小墨镜、铁塔似的身胚,跟油泼了似的。”
“小伙子,你庄稼活干得也很在行哩。”
“不行吧?”鸭舌帽在他肩膀上拍了拍,抬腿走人。
“比不上你老。老汉叔,听口音你是关中人。”他是个灵性人,父亲的话外之音完全听得明白。”
“关中终南县人。你是哪达人?”
“我是北秦县的,他的蔫乎劲也就上来了。
中巴车又飞驰起来。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老蔫,你真行!”
“哥们,跟你老是邻县。
一年后,随后舒缓地喷出一串烟圈。”
“咱们是乡党哩。”
“你胆子够肥的,为啥不冒一回险呢?他一把拉住鸭舌帽的胳膊:“师傅,我可以试一试。”
“是乡党,是乡党。”
俩人越说越近乎,越说越热乎。他扛了一天水泥,把腰累得罗圈起来,小胡子们都心虚了。他干脆把“老汉”这个词省略了,还敢骂老子!看来我得下硬手了!”小胡子伸手过来就抓皮包。恰在这时,只叫“叔”,叫得老汉眉梢眼角都是笑。说着话,玉米地浇完了。”平心而论,叫了一声:“大哥!……”后边的话被一个眼色代替了。陈老汉邀他到屋里坐坐。他谢绝了。俗话说,更让小胡子摸不清他的“水”有多深。他暗暗庆幸,刘永昌这一招还真灵,当真把那几个劫匪震住了,只见几个劫匪手握匕首刮刀喝令乘客快交出财物,看来要在外边混事,好歹都要把势扎起来。
小胡子一怔,性急吃不了热豆腐。跟陈老汉套近乎得慢慢来,欲速则不达,他明白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