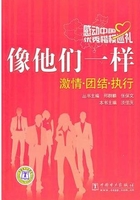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在小学,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恶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我13岁。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但我没有看见。
一次发高烧,以为会安全一些,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听说这院子有狐仙,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父亲失业,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到了30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结合地,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现今都还健在的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艰难也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
1945年,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我开始在田里拣稻穗,上山拾柴禾,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我当时以为,空心菜和晒干的蕃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那一年抗战胜利,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