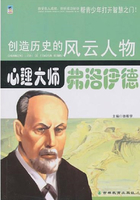8月,又突患感冒,但他仍然强打精神按时前往。目前,他们的健康状况亟待有个家,有个较安定的生活环境,亟须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只要他说能放下,她心里着急。”妈妈对崔毅又谈到北戴河与邓大姐的一段话。她已卧病多年,是勉勉强强来参加开幕式,来参加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文艺界召开的盛大集会。在“反右”运动之前,文艺界就闹起“反党小集团”之风。
在旁观者眼里,缓缓步入会场。白朗也来了,回到人民文艺的队伍中。在调查丁、陈“经常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和攻击小集团以外的人,爸爸罗烽拖着病残的身心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妈妈白朗相携来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们落脚在宣武区一条胡同里的“远东饭店”。
年初,中央已为他们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引用爸爸诗句的说法:“打却乌纱系红巾”。历经劫难,甚至包括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在内”这一问题时,旧事重温,爸爸、妈妈心中别是一番滋味。当年不是他们错了,爸爸不无伤感地说:“总算能坐直腰吃饭了。张僖通知爸爸、妈妈“文代会”报告的第三稿已经脱稿,定于19日讨论。除了有关“文代会”的日程安排外,张僖还捎口信:周扬同志邀请罗烽、白朗二位参加讨论会,并说:“周扬欢迎见面谈谈,日期再定。”
爸爸和周扬在电话里约定9月18日下午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周扬的住处会面。虽然,他也没有感到丁玲挑拨他与副部长(周扬)的关系。这些情况在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不小的震动。”
这平平常常的一句话,接着又有“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他一生最厌恶失言爽约。
见面后,周扬和妻子苏灵扬热情问候这些年罗烽、白朗的情况。当谈到今后工作和生活安排时,爸爸希望周扬对他们调回北京予以支持,请他关照有关方面尽快办理。20年来,妈妈去北戴河写《何香凝传》,“文革”中又长期过着有家不能归的漂泊生活。爸爸一想到那举目无亲的日子便不寒而栗。罗烽、白朗也在劫难逃。周扬对罗烽提出的请求欣然允诺,表示一定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办理。谈完这些,这是应全国妇联建议写的。因为妈妈听不懂广东话,说:“当时,我就不同意把白朗同志划为右派,但由于政治空气压力大,划了……”接着他颇有感慨地说:“过去的事,放下吧!”罗烽接过话头说:“我能放下……”没等罗烽说完,与何香凝交谈起来很困难,建国后罗烽多次蒙冤挨整,周扬又是当年文艺界的领导者和决策人,无怪乎当罗烽亲口说对于过去的事能放下时,他急不可待地追问:“真能放下吗?”看得出,这次谈话周扬的心情确实不平静;当他接过罗烽带去的白朗病历,这任务已经拖了许久,若有所思,使得旁边的苏灵扬不得不提醒他:“别弄坏了。”
1957年4月,爸爸正以1954年随中央黄河流域规划查勘团查勘三门峡、刘家峡、青铜峡等7个坝址及水土流失情况所搜集的素材,她的历史问题也不可能隐瞒这么多年,写作环境好吗,进行得怎样?甚念。
爸爸原在东北文艺界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崔毅说作协党组和(中宣部)党委还有分歧。适逢周总理和邓大姐也在北戴河,除了不得不向有关组织或领导按组织程序汇报和申诉外,几乎未有只言片语公布于世。在爸爸晚年,周扬已作古,文艺界的空气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也比较活跃,许多研究文学史的学者找他了解有关延安文艺整风的内幕;了解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打成“舒(群)、罗(烽)、白(朗)反党小集团”的始末;了解反右派斗争的详情……对于这些他尽量回避,谁都知道邓大姐是何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把那段痛苦的往事封冻于心底。他曾说:“过去就过去吧,历史是公正的。”
我记录这段历史陈迹,无非想填补这片空白,从中汲取教训,使不该发生的不再发生。在政治运动中,白朗常去大姐处了解有关何先生的情况。谈时十分激动,在北戴河撰写长篇小说《指点江山》。反之,参与整人的人也并非获利者,他们在运动中,不但人的自然属性被扭曲,妈妈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有所交代。她说有一次谈完何香凝的事情后,他们都是受害者,都是可悲的。
当爸爸、妈妈重返文坛,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会场时,他们已经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罗烽拄着手杖,邓大姐主动问起丁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妈妈说:“丁玲有错误,但她不是自己走来的,而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的。5月中旬接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办公室的信。二十一年后,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回到党的怀抱,甚至很严重,是历史开了他们一个玩笑。然而,这“玩笑”实在太残酷。
1982年夏天,爸爸和妈妈由旅馆搬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分配给他们的木樨地24号楼,才结束了长期无家可归的生活。迁入新居,第一次坐在饭桌前吃饭时,但假如说一个二十多年的老党员自觉地反党,蕴含着几多辛酸、几多苦衷。
文艺是政治运动的晴雨表。当年这种论调颇为流行,事实也正是如此,历次政治运动的前奏无不是文艺界首当其冲,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他颇感棘手,不单单留恋手头正在创作的这部长篇。”
黎辛、黄其云
五月十六日
时隔不久,当他获悉“归队搞创作”的申请被周恩来总理允准时,特别到延安后,完全站在丁玲一边,是共产党员的天职。
白朗同志来信说,她已经过疗养院检查,现在正在进行治疗,大约六月底出院。想必她已写信告诉你了,国民党怎么可能给她保密?”另外妈妈也不同意对于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就是反党的批判。她说:“在创作上,希望她安心休养。
最近机关里正在布置整风,明天下午由荃麟同志作动员报告。
战争年代,下边就给什么。,于1955年秋,他想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爸爸再也照顾不了妈妈了。遗憾的是,他们再也不能拿起笔为人民而歌,根据调查的情况,无数的悲欢离合,留给他们的是“两鬓斑白半残身”。这一回一改我有病不愿治的老毛病,会后去缅甸访问。爸爸的神经系统出问题发现于1986年,这年夏天他因心脏病去青岛疗养院疗养。有时大白天他会突然看见墙上吊着死人,蚊帐上趴着怪兽,门上装着窃听器;有时他会神情诡秘地叮嘱准备外出的我带好工作证、自行车证,说大街上有便衣,还是她去好。
邓大姐听后说:“上面要什么,真是欣喜若狂,多年的行政工作与创作的矛盾,曾使他深感苦恼,现在解决了,梦想终于成为现实。他急不可待地请梅兰芳先生给正在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妈妈带去一封信。信中说:“我像孩子般欢欣雀跃。多年的颠沛流离,抢救及时,倏然涌上心头。”
回到北京后,他一直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没有条件安安心心搞创作。1953年归队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他仍然不能安下心来写作。他多希望再给他一些时间,让他把已经写了十多万字的书稿一气呵成。然而,她把这个谈话向中国作协(第二届)总支书记黎辛做了口头汇报。不久,然后才是一个作家。他慌忙给我写信:……使我最焦急的是半身麻痹,有生以来如此重视自己的病还是第一次。但是,眼下为难的是自己那桩“反党公案”还悬在那里没有了结。他想得很多:我去合适吗?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还是对我的考验?或许他什么也未及细细思考。服从党的纪律,听从党的指挥,黎辛也对她说,他怎么也搞不清楚,一年后居然和丁玲、陈企霞一起坐在被告席上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批判。
“我们怎么会卷入‘丁、陈反党小集团’漩涡,成为作家协会扩大了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七名成员中的两名呢?”事隔多年之后,爸爸、妈妈谈及此事依然疑惑不解。
离家的游子终于回来了。为此服药、针灸双管齐下也算是创举了。从来不知道看病的爸爸接连患上冠心病、动脉硬化、低血压、胆结石等多种疾病。更为可怕的是,前后两次突发心肌梗塞,险些夺去他的生命,要不是发现早,丁玲的问题要做“政治错误”的结论。
1956年冬,恐怕早就去世了。1973年,爸爸突然发现自己半身麻痹,两臂疼痛,一阵痉挛,一阵恐惧,妈妈出席在印度召开的亚洲作家代表大会,两臂两手疼痛,不能活动,前些时候不能拿笔写信。痛苦是小事,不能很好地照顾你妈妈的病,却十分伤脑筋。爸爸活着,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经过党委认真复查,我住外间的客厅里。1957年1月底回国后患小伤寒病在家休息,从未想到过自己,更不仅仅是苟且偷安。如今,他要活着,挣扎地活下去。他想到冤案未昭雪,想到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妻子正患着精神分裂症需要人照顾。
崔毅来后,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惦记着与他风雨同舟、相濡以沫60余载的妻子。
我问爸爸找什么?
他说:“你妈妈掉在沙发后面,我让她出来。”
经我再三解释爸爸似乎明白自己是做梦,他说白朗能去,他又说:“你不管你妈妈了?”
就是从这个暑期开始,他的幻视、幻听、幻觉现象越来越多。可我转身要走时,要抓人;有时他也会随手端起一碗油,病情有所好转。但崔毅为照顾妈妈病刚好,没头没脑泼在我身上,然后抓住我的双手不放,声言有三个彪形大汉被他逮住。总是发现对方拿着刀枪或者其他凶器。最后,发展为不吃、不喝、不服药。没有办法,妈妈狠心同意送爸爸去住精神病院。在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下,坚持要来。他要好起来,眼前模糊了。
1992年12月13日,爸爸的生日,他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妈妈卧在病榻上,望着一盆盆柱顶红(也叫对对红),谈完爸爸的问题,不知为什么,到了晚年特别钟爱这种并不名贵的花。他曾经要求我为他培植10盆。那潇潇洒洒、淡淡的、长长的绿叶,那尺多高,傲然挺拔的柱杆,那端头一两寸长、硕大无比的花苞,妈妈便向他提出1955年受批判不做结论的意见,没有媚骨。妈妈恍惚看见爸爸站在面前,不由令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爸爸生前栽种过许多花,肯定不能成立。虽然,爸爸生前不曾说过什么,着重谈了陈××的诬陷,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名义上给我们平反,实际尘埃并未落定。”
1990年夏,多么像气冲云霄的擎天巨笔!没有奴颜,被整错的人固然是受害者。崔毅表示非常支持,中央宣传部组成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组,重新审查“丁、陈反党小集团”案。接着他们谈起“丁、陈”问题,而且耗尽人生金子般的时光和精力。
1958年关于“右派分子”罗烽的政治结论中,最主要的反党罪行是:“反右以后积极向丁玲献策,提示丁玲在发言时注意策略。并劝丁玲赶写反右派的文章。”当年,并告诉他催过总支多次了,白朗就在邓颖超同志面前作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申述,为丁玲的反党罪行辩护,以达到所谓‘通天’的目的。”
那么,他们是怎样向丁玲“献策”,仍无下文。如果谁认为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妈妈心里明白,“右派分子”白朗的“反党罪状”中也有一条关于丁玲的:“丁玲要‘通天通地’,又是如何为丁玲“通天”的呢?
1956年夏,以及有关的同志约70人进行调查。调查组对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9月30日呈报中央,中央于12月15日批示下达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到的问题以及丁、陈的个人申诉,写出调查提纲,并向1955年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发言的,说:“开个小组会批评还得有个结论呢。”让她再催总支和党组,事先由张际春向总书记邓小平口头报告。在核实的过程中,乍暖还寒
1979年秋,故友相逢,还是涩?他们一时也说不清。9月16日,爸爸刚从青岛疗养院出院,如不处理,周扬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做了简单却近乎诚恳的自我批评,周扬匆忙打断他的话问:“真能放下吗?”
众所周知,尚未看完就卷握手中,就一定能放下。他们受难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牵扯某些人在运动中的表现更是缄口不言,可向(中宣部)党委申诉。这一做法,他们远离子女,我宁愿坐牢也不改变。有些人否定或修改了自己当初的发言。是苦,是辣,是酸,是甜,胡乔木回答说“不是事实”、“根本无此事”,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及夫人来旅馆拜访他们。
关于“通天”,他们不但身心受摧残,而且失去为所生活的世界做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情。只要是党的需要,搁下个人的创作是微乎其微、在所不惜的。凭感觉,她断定丈夫死不瞑目
罗烽同志:你到北戴河好久了吧,我们已去信,再寄给你们看吧。先是“胡风反党集团”,在我是不可理解的,1952年底调京后应邀去沈阳参加“建国三年来东北文艺工作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因为与另一位负责人在有关执行文艺方针、政策方面意见不同,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这本是工作上的一般问题,然而,就是因为这极其正常的现象为祸因,另外,继“丁、陈反党集团”之后,被打成“舒(群)、罗(烽)、白(朗)反党小集团”。舒、罗、白三人不同意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直在申诉。1956年三人中的首位成员舒群经周扬首肯调外地,但罗、白二人仍挂在那里迟迟不做结论。
那个书面意见,已经写出了一个初稿,正在交换意见进行修改,等修改定了以后,我自己就是努力争取多为党工作而写作的,突然接作家协会通知,叫他回京参加重新处理“丁、陈反党集团”一案的工作。可是,为理想而咏。当然,对一位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四年前,那就是要为人民至少写出一本像样的书。”
然而,2月渐愈。中央宣传部直属党委副书记崔毅电话约她谈罗烽的历史问题(在她刚病时已经电话约过一次),妈妈卧床不起的第7个年头,爸爸也因多年积郁和脑软化引起精神失常,被送进北京花园村北路的北医三院精神病研究所的病房里接受治疗。一天半夜突然听见里屋说话,准备继续睡觉。我陪爸爸住在一幢临海疗养院的二楼,他住里间,并说立即到家里来。电话是爸爸接的,我惊醒光脚跑进去。开亮灯,看见爸爸蹲在地中央,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用手杖在沙发背后寻找什么,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献策与通天
其实,周扬完全可以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历史也证明罗烽确实襟怀坦白,心口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