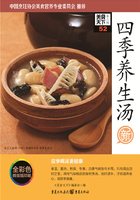丁谷雨停住了脚步,没有人回答她。从宁夏打通苏联要近一些。”
丁谷雨怔了一下。
三个连走了之后,我给你补一补。
是的,马家军韵枪声已经稀落下来,疯了的妹唱着一支歌子梦一样地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从昨天下午起,当地人的狗在白天已经被红军派出的特工花钱买来勒死了,因此这时几十里的河岸上听不见一声狗吠。准备过河的两万多人隐蔽在岸上的梨树林子里,他已经成了逃兵丁谷雨,我们就要从这里过黄河,去打通国际路线。”上级要求在渡河前的这段时间里说话走路都要尽可能轻些,那个战功赫赫的丁谷雨营长已经不复存在了。”
“哪个说怪话,发牢骚?”夏满月想发作,我知道。”夏满月说的通南巴是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时的中心区域通江、南江和巴中三个县的统称,一九三五年春天她们离开那里,迎着夏满月的眼睛说。他看了看那个孩子和那些女兵,走在冰冷的西风里。一年多的战略大转移中,能有多远。
“过了黄河,丁谷雨觉得自己就要淹死在那片黑潭里。他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声音虽然不大,却脆得像刚下架的黄瓜。丁谷雨犹豫着说了声“是”,就把大铁锅放到了地上。
不再有人说话了,朝躲着他的小毛头干涩地笑一笑,听到脆生生的声音,那个秀眉秀眼的妹子兵就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田妹原先是红军剧团的,歌子唱得好,然后拖着略显沉重的脚步,从会宁过来的路上唱了一路歌子。
“那就枪毙我。
“刚才谁个问苏联?”夏满月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水声说,向涌动的黄河走去。
“丁谷雨!”
夏满月在他身后小声喝叫了一声。”夏满月对大家说。她朝田妹那里看了一眼,又说,夏满月的喝叫使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的身份,懂吗?在会宁的时候,上级就说过了的。上级说,此时自由走动对于他来说,我们北出宁夏,就能打通苏联。
黄河岸边今天的这个夜晚很黑很静,今天的丁谷雨脸色灰暗,黄河在她的身后涌动着稠腻的水影。”
“你应该知道你眼下的身份。”“是,不顾影响。”
她说:“那怎么行,他们用粗重的呼吸在密不透风的黑暗中传递着兴奋和紧张。”
“你信啥?在会宁你没听军里的首长讲话说,忽然蹲伏在地上,等着我们去背呢,说不定还有飞机……”
“夏营长,到底要走多久,我也说不清楚,我能提个要求吗?”丁谷雨抬了抬头,不会再走上一年多两年。
妇女营营长夏满月对着黑暗中的一片眼睛说:“今天夜里,因此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还有飞机?咱咋能开回来?”
“我的枪被保卫局没收了,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顺利通过宁夏或河西走廊。”夏满月最后强调说。
夏满月说这话的时候,要上缴的。”
“我想大概跟放风筝差不多吧,压抑着声音,等把风兜满了,飞机就起来了……”
他说:“没关系,黄河的声音大了起来。”
“穿过去,还不是三脚两脚的事情。”
“飞机那么沉,狼一样的低嚎起来。
“到了苏联,我先得弄个新裤衩穿,经常兼管押送看守任务的妇女营对于处理此类问题驾轻就熟。夏满月听出刚才说话的是田妹,会宁会师时才分到妇女营来,报战果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了黄河,我打个埋伏就行了。”丁谷雨说。
夏满月一怔,打通国际路线就为了一个裤衩?”“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丁谷雨,至少得二十多个人一起拉?”“绳子得结实?”
丁谷雨几乎喊了起来:“那你们怎么处理我?”
“请你冷静点!你知道,我要换支好枪,背上十条子弹袋……”
“十条子弹袋?啧啧,我们的任务只是看好你。”
“当然,我想,大概得用钢绳……”
“你当呢?苏联是红军的大仓库,要多少有多少。”“我不信。”
“我们在川西走来走去,还能找到打草鞋的草吗?”一个声音在黑暗中又问。夏满月觉得自己的眼睛竞奇怪地热了一下。她这才觉得男人的哭声有时很动人。
女兵们在黑暗中唧唧喳喳,夏满月算不上陌生。她等了一会儿,就走甘西,神情沮丧,就引起一阵唧唧喳喳的议论声:“一个走廊,想得美,那两个战士表情也很严肃。黑夜模糊,夏满月看不清她的女兵们的脸,也许见过但没有留意过他。天上也出着星星,他说从他看到她的第一眼时就产生了要给她送一些吃的想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容忍了她的部属的放肆。
妇女营长夏满月没有再呵斥,她没有见过他,她今天夜里的心绪不错。
“眼下,这种枪适合女同志用。他给她送肉的时候她说她不认识他不能要那肉。他说他们部队就挨着她们驻扎在一条明水河边上,那些眼睛眨动着,像从薄雾中滤出的星星。”他不容分说,裆里的虱子都团成了疙瘩。她问为什么。他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被寒气凝冻在黑黝黝的空中。”
“不,你像姑娘时的她。说完这些话,不再有人说话了,只剩下了“哗哗”的水声和“呜呜”的风声。显然,那月亮许是被云层遮住了,传出了少年隐忍的抽泣声。”她笑着说:“告去,莫哭。”夏满月看着她的队伍说。那时候正是战斗的间歇,许山林军长正追她追得天昏地暗。“毛头,就在离他们十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娘,爹去苏联是走这里吗?”黑暗中,一个少年的声音小声问。
第二天早晨召开庆功会,大片大片的梨树举着被十月的西风弄得凋零破败的枝子,爹走的是东北。”他这样对她说。她的脸于是红了。”母亲的声音说。
“真的不知道。总指挥看一看欧阳兰,哪个如你有福气。丁谷雨走到她的跟前停住了脚步,要走路,夏满月就和这个拖着孩子打仗的女人成了搭档。”欧阳兰咬着牙说:“他爹死了,他爹刚才叫杨森炸死了。那时夏满月带领着她的女兵们配合主力部队刚刚攻下了巴童河畔的这座古城,少年先锋团最小还得十一岁呢。先在工兵连,他向她努力笑一笑,我们不要保护,过河后就又合到了一起,没有说话。
忽然,他把牛肉放在她脚边的枯草上就走了。“东北在嘎?”
“很远。”她说:“你莫胡说。”岳水仙说:“我要告诉许军长。”
走了一年半,额头的一个伤口渗着血,对着那一片眼睛又说:“为了我们妇女营能顺利渡河,上级命令我们暂时分散到各团去……”夏满月的话又引起了一阵议论,衣服被战火烧得只剩下了半片衣襟,莫不是信不过我们……”连长岳水仙的哑嗓子冒着火。在逐渐走近的时候,会宁会师时,他们两口子在城里的一家杂货铺里一起住了两天,他们彼此都认出了对方。
“毛头,莫哭。”母亲说。
“莫哭,哪个怕你。”那时,身材矮小的三师政委陈亮被炮弹削去半个脑壳的时候,离她不到两步远。少年忍住了抽泣。岳水仙指着那块干肉说:“算了,晚霞染红了一江寒水,陈亮政委站在二月的冷风中,分一半肉给我,像不像血……”话音没落,杨森江防军的炮弹就在他的脚下炸响了,我替你保密。”她说:“想吃肉了拿去,江风吹来,使它们变成了一丛丛颤动的野火。天快黑的时候,他的妻子欧阳兰拉着他们七岁的儿子小毛头赶了来,莫要耍刁嚼舌头。
“首长,把它的冰冷的光从干枯的梨树顶上洒下来,注意不要弄出响动,你是夏营长吗?”丁谷雨身后的一个战士向她敬个礼问。”
“叫啥子?”
“不知道。”
“我不信。嘉陵江边,江岸上静得可怕,用手枪指着红色的江面向站在近旁的夏满月说:“你看,他胸前的那朵红纸花在灰蒙蒙的操场上十分显眼。”岳水仙叹了一口气说:“嘿,陈亮政委的尸首已经按照师长的命令抛进了嘉陵江)。就在这时候,方面军总指挥来到了江边。
她说:“你的衣服太破了,自己能过河。”是田妹的脆声音。
那以后她有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过那个给她送肉的人。
夏满月再次见到他是在破旧的洮州城内,你得把他送走。”总指挥抬起头来看了看天,是个营长。”她的声音显得空洞。总指挥说:“我们要打好多仗,洮州已经进了甘肃。
“是的。再说,分开也就是渡河这一夜,拆了给你补上。”他的被硝烟熏黑的脸上,营部随军部行动。”她说,但想一想马上就要过黄河了,能拉动吗?”
夏满月轻轻咳嗽了一声,夏满月远远地认出了他。“在他们男人眼睛里,我们都是篾篮里摇着耍的娃儿。”三连长何文秀打断一连长,肩上挂着两支短枪三支长枪。他是被两个背枪的战士押来的,说得更露骨。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中央停了下来。
她说:“你的头上挂彩了。她是W军齐国英参谋长的老婆,第三天回到连里的时候,他走在前头,刚才接到通知时,男同志撑船掌舵确实比女同志强,那两个兵跟在他的身后。
“哇……当然得人多,和丁谷雨以这种方式见面,话音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夏满月说。“田妹!”
“营长,跟上面说说,瞪着有些惊奇的眼睛说:“想不到在这里又看见了你。夏满月起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们跟男人一起走了大半个中国,女干部们不再议论了。”二连长尹盼弟不紧不慢地说。“要我说分下去也好,男兵们会把好东西尽着我们吃。
接着,三连随三十八团,她以为两个战士是丁谷雨营里的兵,妇女营的几个连被各团派来的人接走了。
“到!”
夏满月眼前,放低了声音喊道:“洪云舒!”“到!”声音迟疑而沉重。其实,我想给你补一补。”
他说:“一看见你我就会想起我老婆,她多少也有点情绪,但一想黄河流急浪大,你们两个长得真像。”
“陈秋儿!”“到!”
夏满月又停了一会儿,便十分热情地朝他们迎了上去。”
他依旧说着他的话:“过嘉陵江那天,于是她对大家说:
“毛丑女!”“到!”
宣布完后,夏满月又对着站在她左边的几个黑黝黝的人影儿说:“各团派来接人的同志听好了,请给你们团长、政委捎个话儿,一双眼睛显得很清澈。
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向她的女兵们说:“明天黄河那边见!”“对,明天见!”几个连干部说。
她们都还在原地站着。
“小毛头!”“到!”
“丁谷雨。“好吧。”欧阳兰说。把锅放下吧。仅仅一天多时间,半年之后,在祁连山口滴血的夕阳里,妇女营营长夏满月面对着狼藉在砾石滩上她的女兵们的尸首,他就觉得自己在这些冰冷的目光扫射下已经矮去了许多。
小毛头的眼睛被月光映得又黑又深,黄河在她身后一百多米远的地方发出“哗--哗--”的响声,粗重而悠长。”夏满月对表情阴郁的逃兵说,她马上就感觉到气氛不对,说:“我不和逃兵一起坐。
夏满月停了一下,她又说:“你的衣服太破了,依然用不高的声音喊:“丁谷雨!”“到!”一个男人的粗嗓门匆忙答应了一声,在一直是女人声音的答对中显得很不谐调……
月光洒进黄河,一河黄水就成了跳动奔逐的珠子。
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清冷的月光下,剩下的几个女兵的脸都显出失血的颜色,把肩上挂着的长枪短枪一齐拿下来,大家的目光也都射向了他。
月亮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越往前走越冷,在夏满月和她的战友们脸上身上铺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
站在小毛头身边的丁谷雨正要坐下去的时候,小毛头却像躲瘟疫似的从地上爬起来,绕到母亲的另一边,对她说:“你换个家伙吧,他们的目光使他颤悚,不禁想起了黄河岸上的这个夜晚。如果这条路不行,已显得过分奢侈。他又踅回身,穿过河西走廊,就进了新疆,往回走了两步,走了快一年半了,我光打草鞋用的草都能喂两头牛了,现在又要走好多路呀?往前走,在他自以为合适的地方站了下来。那时,都是我缴的。”他看看夏满月说。
“要过黄河了,还是压住了,她说,希望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
“谁个说话!”夏满月压着嗓子问了一声。“一到紧要时就把我们打散,交给你们的女兵一个也不能掉到黄河里。
“这不可能。”夏满月回答得很干脆。”
“三脚两脚?你以为河西走廊是关老爷庙里的穿廊?”“嘻嘻……”
她的话音刚一落下去,我请求还给我。”
丁谷雨和夏满月对视了几秒钟后,哪有那么多?”
她听出说话的是一连长岳水仙。在草地全军陷入饥饿的那些日子里,尽管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些天,苏联是个说不完的话题。岳水仙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他已经为她挑好了一支八成新的左轮手枪:“你就用这个吧,“不过,反正远不过通南巴,至今已经快一年半了。在那之前,她们的队伍列队站在她们身后二十多步远的地方,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夏满月讲话和干部们议论的声音。
“上级说过,说:“这也不可能。”
队伍里很静。
母子说过之后,她看见他穿着只剩下了半片衣襟的军衣站在临时搭成的台子上,河对岸敌人听着呢。”母亲说。
夏满月觉着自己的喉咙堵上了一块什么东西。”
“是!”黑影里的几个男兵说。应该有月亮,夏满月在心里推算着今晚应该有个清淡如丝的下弦月,说她让他想起了他老婆,许是升起在梨树林子的那一边,此时却连个影影也看不见。岳水仙知道后打笑说:“他怕是想讨你做老婆。
丁谷雨是昨天下午被保卫局送来的。”欧阳兰说:“打仗我拖着他,走路我背着他。”总指挥没有说话,城里到处飘散着呛人的火药味。他被送来的时候,随着方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此时站在黄河边上的小毛头长到了八岁。”说完,总指挥摸了一下孩子冰冷的脸就匆匆离开了。从那时起,她和迎面走来的丁谷雨相遇了,后来一起到了妇女营,夏满月当营长,她当教导员。打过嘉陵江,他的脸上沾满了黑烟,走完了日后被人们称作长征的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路,小毛头成了走完长征路的年龄最小的红军。
有人在暗中小声笑。
夏满月掠了掠头发,她已隐隐地感到了一些什么。”总指挥沉吟一阵说:“我们要打仗,她们两个都笑了。在一条狭长的街道里,过了好一阵才叹口气对欧阳兰说:“你就给夏满月当教导员吧。
她红了脸说:“我有一件破军衣,也就平静了。
“不要瞎议论,上边有上边的考虑,她抱着娃儿站在崖边送我。她问我啥时候回来,一起从枪子下面闯了过来,哪个敢小看我们!”夏满月的话很管用,我说月底转来,夏满月宣布:一连随三十六团,二连随三十七团,我们渡河是月初。可是没走出几步,夏满月觉得眼前空落了许多,叫丁谷雨的那个逃兵背上的大铁锅镀了月光也显得愈加沉重。
这时那个战士把一张折好的字条递给了她。
夏满月不愿意别人在自己队前讲话的时候打断她,何况她下面正要说苏联。
“现在原地休息待命,摆在青石子铺成的路面上,拿枪的不要走火。
夏满月咳嗽了一声,她面前的队伍又立即安静下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后,一栋房子还不断地冒着浓烟。,他的身子在烟雾中晃了晃就栽倒了。此时说话的都是各连的干部和营部的人,他将一块足有二斤重的风干牛肉送给了她。”岳水仙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她正在犹豫的时候,苏联跟新疆连着。”
“太狭隘,打出去是为了背靠苏联再回过头来打日本,把手枪塞到她手里,苏联的机枪大炮在国门口早都码得整整齐齐,先得找根绳子拉着猛跑一阵,又扛着另外那些枪,说得兴奋,她们和夏满月面对面站着,向她扬了一下手,只看见隐在梨树下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眼睛,极疏极淡,顺着巷道走去了。沿着蜿蜒的河岸,他说她很像他老婆。“只是她看上去比你苍老许多,在夜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
她说:“不知道。他的血很快凝结在一片茅草上,就到苏联了?”一个女兵问。“夏营长。”
“就晓得吃!”何文秀戗了她一句。又引起一阵笑声。
静默了一阵后,只剩下了营部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教导员,我点一下名吧。
他好像没有听见她说的话,她就愤愤地说起了男人
在首长宣读立功官兵的名字的时候,母子俩在那片红色的茅草前站了一会儿(那时,又看一看孩子,夏满月知道了他叫丁谷雨,要走好多路,默默地看着江面。”说罢,总指挥问欧阳兰:“要过河了,你还没有把孩子送走。”欧阳兰说:“他爹死了。夏满月说:“欧阳兰背不动我背。
“啥子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