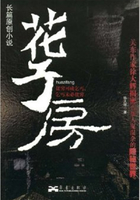除了服从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我立即动身、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前往首都的漫漫长途。
正当我骑马走出巴黎门之时,我遇到了一辆前呼后应的大马车,我认出来这是舒内德尔的座车。这个恶棍在我路过他身旁的时候跟我笑了一下,并预祝我一路平安。跟在他的马车后面走来了一架机械,或者说是一辆二轮马车;一只巨大的篮筐,三根结实的粗木棍子,还有几块厚木板,都用油漆漆成了红色,这些东西都安放在这辆大车上,就在这些东西的上面,坐着我那位戴着巨大的徽章帽结的朋友。这就是那架“便携式绞刑架”,舒内德尔每次出去旅行都是把它带在身边的。这个公务人员还在读他的“沃瑟尔的悲伤”,看上去还像往常那么的情动于衷的样子。
我将不会讲述我的这次远行,以免耽搁了讲述舒内德尔的出行。我的故事唤醒了这个坏蛋的好奇心、激发了他的贪欲,他决意不惜一切也要把我所透露给他的我的堂姐的这份资产据为己有。实际上,就在我刚刚离开他的房间不久,他就设法获取了把我调离的命令,然后就匆匆启程前往斯坦巴赫,并且在半路上遇见了我。
这次旅行并非怎么遥远;在第二天的时候,我的叔父雅格因收到了信息而震惊不已,公民舒内德尔已经来到了村庄之中,正在前来问候他的老朋友。老雅格顿时处于兴奋之中,因为他盼望着见到自己在大学时的老相识,而且他也希望舒内德尔能到那一片乡村里来,能够关注一下你的这位谦恭的仆人有关婚姻方面的事务。当然了玛丽也被唤了过来,做一顿她最拿手的好饭,穿上她最好的服装;她的老父亲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这位势焰熏天的国家新权贵。
舒内德尔的马车一阵风般地驶进了庭院当中,而舒内德尔的后继马车也尾随而来,当然这是必定的了。这位前布道者一个人走进了屋中;他的伴从们以及马匹都留在别处吃饭的吃饭、打尖的打尖。一场极其动人的相会情景在他和雅格之间发生了。他们一起谈论起来过去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成功喜人的恶作剧;他们曾成功演说过的那些优美的希腊篇章,以及所引用的那些让指导老师颇感意外的古老的警句隽语等,而自从“七年战争以来”,这些老师们都早已经故去了。玛丽宣布说,听到这两位老绅士愉快而友好地谈论起这些往事来,简直太令人感动了。
当这番谈话以这种氛围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舒内德尔却突然之间截断了话题,然后平静地说道,他此番前来却是专程为一件令人并不愉快的事情而来——语气之中暗示着将有一些麻烦,并提到某些间谍、以及不好的报告,这些等类的事情。之后他把爱德华叔父叫到一边去,进行了一段恳切的长谈:而雅格则走到外面去,跟舒内德尔的所谓“朋友”谈起话来;他们两个马上就变得很相投了,因为这个恶棍详细复述了一番我跟他初次相会时的情形。当他再次返回到房屋中时,就在洽谈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发现周围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奇异的变化。爱德华.安塞尔的脸孔白得像是一张纸,在那儿一个劲儿哆嗦着,嘴里哭哭啼啼请求谅解;可怜的玛丽伤心地在悲泣;舒内德尔躁动不安地在房中踱着步,暴怒地吼叫着关于人权、以及对叛国者的惩戒、还有关于一体不能分割的共和国什么的。
“雅格,”他开口道,这时我的叔父已经走进了房间里,“我非常愿意,出于我们作为老朋友的原因,非常愿意忘掉你的兄弟的这些罪行。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非常危险的贵族人士;他与我们边境上的敌人有所关联;他拥有大笔的来历不明的资产,这是他窃取的我们的共和国的。你知道不知道,”他说,一边转向爱德华.安塞尔,“有这些罪行当中最小的一件,或者仅仅是因为可疑,你觉得你自己会怎样呢?”
可怜的爱德华坐在椅子里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他完全可以领会得出,在这个可怖的年代里,身有嫌疑意味着什么样的惩罚;尽管说他根本就没有叛国投敌的罪行在身,也许他心里还是明白的,由于跟政府的某几个协约,他自己的获利份额已经超出了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程度。
“你知道不知道,”舒内德尔又接着说下去,声音听上去几乎是暴跳如雷了,“我是出于什么意图才到这里来的,又是谁陪同我前来的?我是共和国司法部门的执法官。你自身以及你的一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中:那边那个男子,他跟着我过来的,就是一个法律执行者;他已经剥夺了这个国家中像你这样的坏蛋数百人的性命了。只要我发一句话,你的命运就算是无望地终结了,你的死期也就来到了。嗬!格里戈里!”他喊了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格里戈里从庭院中回答道,“我还需要半个小时才能把这架机械装配起来。我是不是应该到村子里去,把军队和宪兵们喊过来?”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舒内德尔说道。“断头台就放在院落之中;而你的名姓就在我这张名单上,我是有见证人可以证实你的罪行的。你还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吗?”
没有听到一句回答的话;这位老绅士已经麻木地僵住了,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哑巴;可是他的女儿却并没有被这番恐怖的气势所吓倒,她替他说话了。
“你不可以这么做,先生,”她说道,“尽管你是这么说的,自认为我的父亲是有罪的;你不应该就这么独自一人进入到我们的家中,要是你在心中已经对这件事情确定无疑了的话。你用这种手段来吓唬他,因为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明,从我们这里获得依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公民?——请告诉我们,你认为我们一家人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我们该赔付多大的数目作为我们的赎金呢?”
“数目!”叔父雅格喊道;“他不需要我们的金钱:我的老朋友,我的校园密友,他不会是专为到我们这里来,跟属于雅格.安塞尔的任何人讨价还价的!”
“哦,不先生,不,你不会要我们的钱财的,”爱德华尖叫道;“我们是这座村庄里面最贫穷的人:已经破产了,舒内德尔先生,由于共和国的事业而破产了。”
“请肃静,我的父亲,”我那勇敢的玛丽说道;“这个人讨要的是一个价码:他带着那边他那位显要人士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来恐吓我们,并不是真想杀死我们。要是我们死了,他就不会碰到我们一个苏的钱币了;全部都会被罚没给国家的。告诉我们,先生,我们该出多少钱来换取我们的安全呢?”
舒内德尔笑了起来,然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
“玛丽亚女士,”他说道,“你的猜度是完全正确的。我并不想要这位可怜的、满嘴瞎说的老绅士的性命:我此来的目的完全是善意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件事情完全依赖于这位优秀的年轻女士了(她的精神头儿我喜欢,她的临变不惊的智慧我欣赏),无论说我们之间的这场事务是以爱结束、还是以死亡收尾。我谦卑地把自己交付手你,公民安塞尔,作为一个能够与你漂亮迷人的女儿一起携手的候选人之一。她的善意,她的美丽,以及她的一大笔财产,我知道你是想把她作为继承人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使她成为一个整个共和国之中最最骄傲的男子心向往之的匹配佳偶的,而且我敢保证,这样会使我感到这是一件最最快乐的事情。”
“这可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了,舒内德尔先生阁下,”玛丽说道,不禁颤抖起来,脸上变得一阵惨白:“你的意思不会是这样的;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直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
“请等一下,美人女士,”他回应道;“你的堂弟皮埃尔经常跟我说起你的节操来:真的,正是经由他的特别提议,我这才有了前来拜望之意。”
“这是胡说!——这是一个卑鄙无耻而怯懦的谎言!”她脱口惊叫起来(因为这个年轻女士的勇气一下子鼓了起来)。“皮艾尔永远不会忘记了他自己还有我,是决不会把我出卖给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你来到这里、满嘴里说着谎话——一个针对我父亲的谎话,竟然要威逼他的性命,竟然还诬蔑败坏我亲爱的堂弟的荣誉、还有他对我的爱。现在否认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父亲,我爱皮艾尔.安塞尔;我除了他不会跟任何别的一个人结婚的——决不会,就算我们把最后一个便士都偿付给眼前这个男人,作为换取我们的自由的代价也罢。”
舒内德尔唯一的回答就是,这显然是想叫他的朋友格里戈里来。
“派人到村子里去,把木驴和几个宪兵带过来,告诉你的人都准备好了。”
我该不该把那架机械立起来?他做张作势地咋呼道。
“你听到他怎么说了,”舒内德尔说道;“玛丽亚.安塞尔,你可以决定你父亲的命运。我在两个小时之后会再回来的,”他最后说道,“那时有望会听到你的决定。”
这位人权的拥护者说完后就离开了房屋之中,离开了整个这一家人,就像你可能想到的那样,满脸怏怏不快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