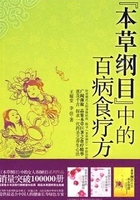“为甚不算?”
“他是……渴死的。”刘清涧说着,喉节不由自主地蠕动了一下。
郝黑子扭过头,不说话了。
是的,他是渴死的。一天,土匪袭击了给他们驮水的两峰骆驼,他们断水了。那时,边境巡逻队刚成立不久,交通、通讯条件都极差,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看见了黑色的死神。断水的第三天,巡逻队员刘治顺从国民党留下的地图资料上发现了W号界标下边的一口苦井,于是,他带了两个羊皮口袋,径自踏上了找水的路程。走了两天两夜,找到了那口井,然而井早已枯干了。
刘清涧想起了妈妈珍藏着的那个蓝布面的日记本,想起了日记本上最后的那段歪歪扭扭的文字:
太阳一点一点地升高,空气渐渐热起来了。我勉强坐起来,张大嘴喘了几口气,吃力地睁开眼睛,朝这儿那儿看了看。真希望能意外地看见一个人、一匹骆驼或者一只狗。但是我失望了,视野里,除了阳光下的戈壁滩和那些虚无缥渺的蜃景,任何活动着的东西也没有。只好寄希望于天,希望能滚过一声雷,飘来一片云,落下一阵雨,可是天上只有一个眩目的太阳。我知道,已经无法返回巡逻队的营地了。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将要在这里默默地死去。
我从来没有设想过,做为军人,我会这样窝囊地死掉。虽然已奄奄一息,但我仍然渴望着和一个窜匪或者一个逃犯在这里邂逅,我知道怎样维护新中国的哨兵的尊严和声誉……
真渴呀!血管里的血都成了粘稠的。昨夜,咬破手指,使劲地吸吮,那血也是咸的,咸得很浓。来到这里才三个月。三个月,多短呀……
戈壁滩上哪儿来的那么多苍蝇和蚊子,糊在脸上身上,轰不走,赶不跑,讨厌的东西,你们已经闻到……
真想活着,真想回去。真想看看我的还没见过面的儿子,呵!现在我已经是爸爸了!做爸爸一定是十分幸福的,用胡子把他扎哭,再用糖把他逗笑,当他会叫爸爸的时候,一天让他叫上一百遍……
我又醒了。刚才,恍恍惚惚中,我看到了一道碧清潺湲的山涧流水--那是儿时嬉戏的地方,哦!故乡的山涧水!
你不是要我给儿子起名字吗?清涧--行吗?
呵!水,水……
刘清涧闭上了眼睛,将额头贴在冰冷的积雪上。
午饭后,风雪渐渐小了,铅灰色的天空透出了点亮色。慰问团的同志们和铁舰山观察哨的三个战士围着红梅牌收音机,在强大得如同狂轰滥炸般的电波干扰下,费劲地收听了《元旦社论》。
接着,是诗人黎凡颇有见地的“答记者问”--“答记者问”,是慰问团同志们对黎凡解答问题的谐称,“颇有见地”,则是慰问团长的评价--本来应由蓝禾儿来解答,但他以替战士站哨为由婉言谢绝,而责成黎凡来完成这一任务。黎凡先是一番推辞,后见两个干部都不在场,遂如无羁之马,胆子不由大了些,再加上和慰问团一半日厮混,熟悉了,便欣然应允。此刻,“答记者问”正在煞有介事地进行。黎凡正襟危坐,一脸庄重,冷秋、罗长贵忙着递茶倒水,慰问团的同志们不断提出问题:“请问黎凡同志,你来到铁舰山几年了?”
“一年,在这里军龄最短。”
“长的呢?”
“十年。蓝排长就是。”
“蓝排长?”一个女演员眨巴眨巴眼睛,说,“我们私下议论,都觉着他是这儿的一个神秘人物。”
“不,那只是错觉。”黎凡笑笑说。
“你们喜欢他吗?”
“怎么说呢?”黎凡略微顿了一下说,“我们敬重他,他是一个具有良好素质的军人,正直而刚毅。”
“做为排长,他似乎显老了些。”
“是的,有点。”
“是什么阻碍了他的发展?”
“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机遇,再比如,我们的庙太小了,到边防营就到了顶,小庙难敬大佛--也许这比喻不太恰当。”
“如果换个地方,他有可能获得晋升吗?”
“完全有可能,他甚至也能成为将军。”
“可是,听说他就要退伍了,是吗?”
“是的。”
“为什么?”
“需要吧。”黎凡淡淡笑了笑。
“他缺少点儿感情,给人个冷冰冰的印象。”
“那是你们不了解他。”他说。
“我们上来的时候,听到了有关你们边防上的一点闲话……”一个乐队的同志拐弯抹角地说。
“我知道,你指的是传言的所谓三大嗜好--吸烟打牌说女人?”黎凡淡淡笑了笑。
“有吗?”
“任人说吧,我们堵不住别人的嘴。不过我们希望得到理解,吸烟,是因为我们太寂寞;甩老K,是因为除了站哨,我们还有许多多余的时间要消磨;说女人--其实并不经常--是因为这里没有女人,而我们已经到了知道女人的年龄。”黎凡声音微颤,显得有些激动。
短时间的沉默。
“你们有没有过痛苦的时候?”
“我们都是极平常的人,我们都有七情六欲,自然也包括痛苦。”
“看来,你们哨所上上下下很团结?”
“我们有时候也有矛盾。”
“有些哪方面的矛盾?”
“哪方面的矛盾都有。”黎凡说,他想了想,笑道,“甚至还有情场上的……”
“是吗?”好几位演员同时惊讶得睁大了眼腈。
雪住了,国境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白雪封裹了界山和界山两边的所有旷野、山丘和枯河,只有在背风的断崖上,才露出深褐色的沉重的岩石。
白雪的反光刺螫着冷春的眼睛,他感到一阵一阵的酸涩与疼痛。他慢慢地移过戴着手套的手,揉了揉眼睛。
“伙计!”韩五一轻轻叫了一声。
冷春的心震动了一下。在这一瞬间,这称呼唤起了他许多美好的回忆,他想起在家那阵,一起上学的时候,他们一起打猪草,冬天,一起搬着膝盖“斗鸡”取暖。韩五一总是这样称呼他。可是来边防四年了,他再没听到过这样亲切的呼叫。此刻听起来,仿佛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儿时。他的眼睛发热了。
“伙计!”冷春也用同样的称呼回答了他。
“妈的,今年元旦雪窝里过了!”韩五一望着静静的雪原,小声骂了一句。
“第五年了。”冷春感叹着。
他们默默地趴了一会儿。
“这阵村里忙什么呢?”韩五一扭过脸,问冷春,“快进腊月了吧?”
“快了吧。”冷春说,“一进腊月就忙了。”
“过腊八、祭灶、再就是忙着过正月。”
“听说去年正月十五,村里的高跷踩到羊坊店走不脱了呢,非要唱一出《起解》才放行。”
“今年准还要踩哩!”韩五一说,“妈的,想着心都痒痒。”
冷春轻轻叹一口气,二人都不再说话。
“真快,都第五年了。”过了好久,韩五一又一次感慨道。
“二十三了!”冷春说,他看看身旁的韩五一,问,“你二十四了吧?你大我一岁。”
“嗯。”韩五一应着,把一直向前边望着的头微微侧了侧,不等目光与冷春相遇,又把头扭了回去,眯着眼睛,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
“还熬什么呢?”韩五一微蹙眉头,用很低的声音说,“你秋天打报告复员吧!”
“为……为啥?”
“你让人家等到猴年马月?”韩五一怅然地说,“我记得,她属牛,也二十二了。”
“呵……不。”冷春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他用手在雪堆中摸着,轻轻抓住了韩五一的胳膊。
“别凉了人家。”韩五一强装出笑。“她是个好姑娘。”
“班长!”冷春用暗哑的声音叫了一声,但随即又改口叫道,“伙计!”
韩五一扭过脸来看了看他。
“还是你走吧!”冷春说,“你爹盖房摔了……”
“胡说!”韩五一吼了一声,打断冷春的话,过一会儿,又问,“听谁说的?”
“她,她信上说的。”冷春说。
“她--”韩五一嘴唇翕动了一下,脸上很快地又浮上了那种阴冷的神情,他哀伤地笑了笑,说,“她管好自家,我们韩家的事不用她操心。”说罢,怅然的目光又转向白茫茫的世界。
白的山,白的平滩,白的天空。韩五一忽然想到了白的梨花--熟悉的美丽的故乡的梨花!他觉着眼窝热热的。
“听我说,我爹的事不要张扬。”他压着声音说,并不看着冷春。
“嗯……知道。”冷春嗫嚅着说。
韩五一静静地待了一会,感慨地说:“我们还是服从命运的安排吧!妈的,荒凉的戈壁滩使了什么魔法,牢牢地拴住了我们这群人的心。”
冷春没有回答。
他们从立着界碑的界山望过去,吃力地搜巡着对方那条高大但不峻峭的山脉和山脉前边那片开阔的戈壁,天地一色,茫茫银白,极难分辨山与滩、天与地的界线。
……
“副连长!”郝黑子用极小的声音叫了一声,同时用胳膊轻轻地拱了拱刘清涧。
“什么事?”
“你看!”郝黑子用目光指指自己的一边肩头。
“玛祖鸟!”刘清涧的眼睛亮了一下。
“放了它。”
“不,我不。”
“黑子,快看!”忽然,刘清澜轻轻捏了他一把说。
郝黑子向那座高大但不峻峭的山脉看去,在那个倒三角的豁口处,一个小黑点在缓缓移动。
“是军车!”他说。
“喂,你看见了吗?”韩五一看着那个神秘的凹口,低声问。
“巡逻车吧?”冷春判断着。
“不,等等看!”
铁舰山观察哨的哨塔上,蓝禾儿伫立在潜望镜前,象一尊雕像。他这样站了很久。他的眼睛从目镜孔望出去,由东往西,一寸一寸地巡视着,在那白得晃眼的旷野上艰难地分辨着平时那些熟悉的山峰、深沟、沙丘和戈壁。白雪的雕塑柔和而丰腴,那些山丘和沟壑的轮廓变得平滑起来,连崚嶒的断崖也添了几分秀美,而辽阔的戈壁在积雪的覆盖下静静地躺着,简直就是陇东高原上冬天的塬地。
但它又不象古老的家乡,它总缺少点什么,几行杨柳,几株榆槐,几处茅舍,几柱炊烟,因而,即使在温存的雪中,即使在一片素白的遮掩下,眼前的景象依然带着几分荒凉,几分严峻。
他向W号界碑的方向看了看,他知道,刘清涧和那三个战士就在那儿潜伏。除了积雪,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相信,那个庄严的标志是在那儿。他用十年的时间,结识了这片袤土地上的每一个山丘,每一道干沟,头上的每一颗星星和脚下的每一块砾石--十年,那是一门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功课。
现在他读完了。
但他却不想从记忆中失掉它。他在储存。
“报告!”
身后传来了冷秋的声音。他太专注了,连他走近的脚步都没听到。
他从潜望镜前转过脸来,望着冷秋,没有说话。
“排长,我来换哨!”冷秋说。
“不用,你下去。”
“不行!”冷秋着急地说,“你已经连续站了三班哨……”
“下去!”蓝禾儿不耐烦地说。
“不,我不……”
“我还没有离开铁舰山呢!”蓝禾儿拉长着脸说,“我命令你,下去!”
“是!”冷秋不得已向他敬个礼,扭转身子,走出哨塔。
蓝禾儿重新伏在潜望镜前,他在寻觅,他在搜索,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总想着拣回一些什么。
“还剩五天了,呵,十年中的最后五天……”他想起了上哨之前营里打来的电话通知。
夜里九时,刘清涧才带着他的士兵们从边境潜伏点回到了铁舰山。
月亮出来了,照着无边无涯的白雪,晶莹、透明,风力发电机在夜空里稳重地转着,发出闪闪的亮光,黑妞儿慢慢地踱着,不时用嘴拱一拱地上的雪,寻找吃的。
月夜是情侣的。来了两天,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等到现在,雪雁才得到了他的边防军。他们手拉着手,在雪地上走。
他们在“红岩”下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