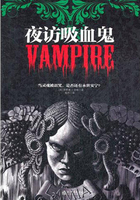见到黄小麦的时候,果然把我吓了一跳。我和小麦对视了半天,谁都没有吭声。最后,是我最先伸出了手去,在她的头上抚摸了好一阵,我说,你先去洗个脸好吗?
她乖乖地点点头,就洗脸去了。
她让我在院子深处的一张水泥桌边坐着等她。
一位心软的护士,便同情地敲开了我的房门。
那里很少坐人。
她说呆会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好吗?
我说等你洗脸回来再说吧。
她说看完了你得帮我,你得帮我离开这里,你还得帮我……她的两只眼睛就像两条已经无力挣扎的小鱼,我说去吧,先把脸洗好了再说。
她让我看的原来是一张开庭审判通知书。
我说这是谁的?
她说是我父亲。
我险些就惊叫起来,你父亲在监狱里?
我问那护士,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护士说,你去看看嘛,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从护士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黄小麦的情形已经到了谁见了谁都会怜悯的境地了。
她点点头,然后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说不清楚她那样的一种眼光该属于哪一种眼光,软软的,好像轻轻一碰就可以消失的某一种,但却一下就钻透了你的心窝,让你感到一种彻骨的寒颤。
她说他让我去看他。他还让我拿一样东西去给他。就是被你摔没了的那张磁带。
我心里猛地一震,但转念间便感到不可理解,我说你父亲他,他要那张磁带干什么?她说你不是也听过吗?那磁带里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是我妈的情人。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沉入一个黑色的深渊。我想我的脸色当时一定十分吓人。我说那你爸,他是不是就为这事进了监狱?
她点点头。
她说那男的被我爸爸给杀了。
这一点我自然可以料到。但我想不明白,他父亲要那张磁带干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让我拿去给他。我的心里忽地就沉重起来,这回轮到她像小武一样,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我就像是对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别说是她骗了我她咬了我,她就是把我的一只手给剁了,我都不能原谅我对她所造成的伤害。我说那张磁带是你爸原来交给你的,他让你帮他收藏?她却摇摇头。她说我爸他没有听到过。顿了顿又说,那是我在家里偷偷录到的。
我说那你爸是怎么知道的?是你告诉他的?她点点头。她说是的,是我告诉他的。我录到那个磁带后,当夜打电话告诉他的。
我说你爸爸当时在外边出差?
她说不是,我爸爸他在米城做生意,我妈妈也在。那男的就是米城的。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做的生意。那天是我妈带那个男的回来拿一样东西。早上起床后也不洗脸,她逢头垢面地抓着铁门,脸紧紧地贴在上边,朝着外边的护士乞求喊着,让他们帮她把把我叫过去。是被我无意中录到的。录完后我很害怕,我也很愤怒,我就偷偷地跑到赵旧的家里。赵旧那时跟我很好,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然后我就告诉了我爸,我爸当时在电话的那边,半天没有说话,我还担心他不会相信,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把他们在床上的那种声音全都给录下来了,你要不信哪天回来了你自己听。可他还没有回到家,他还没有听到那张磁带,他就把那个男的给杀了。
那我现在还能帮你什么呢?你不是说让我帮你吗?
我在赵旧家里还藏有一张。是我在他家翻录的。我怕手上只有一张弄丢了怎么办?我怕我爸拿不到他们的证据。
我顿时便激动了起来。我想跟她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但我突然觉得什么话都成也废话了,惟一是帮她从赵旧的家里拿出那张她藏着的录音带。我几乎没有多想,拉起她,就绕道钻进了医生的门诊楼里,然后钻进了一个无人的办公室,在门背偷偷拿了两件医生的白大褂急急地穿上,转身,我们俩就从容地行走在了通往医院大门的路上。我猜想当时如果有人站在高高的楼顶上往下看,我们俩人在他的眼里,完全可以说,在寻找着我的身影。人家吃饭的时候她不吃,就仿佛一对来自地狱的老少天使,在飘然地往大门口飞行。
医院的两个门卫当时都站在大门边来回地走着,眼睛都亮闪闪的,但没有一个在黄小麦的身上看出任何一点怀疑。其中一个还对我礼貌地举起了他的右手,表情友好地微笑着。我也朝他挥挥手,我们就走到外边去了。
门前不远的停车处,刚好有一辆等客的出租车,我们往里一钻,车子就开走了。
那两件白大褂后来就一直地陪伴着我们。
我先从商店里给她买了一个随身听,挂在她的胸前。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她突然把我拉到了一个小商店,然后选了一把菜刀,让我帮她出钱。我说你买这个干什么?她好像早就想好了如何告诉我她买刀的理由。她一开口就说,有一次我用他们家的菜刀砍对了石头,砍坏了,被他妈骂了半天,我买一把还给她。
我当时没有多想,我当时还觉得这疯女孩还挺心细的,就给她买下了。她拿着菜刀端详了两眼,抓了一张报纸包着,塞进了白大褂的下兜里,一边走一边用手压着,不压就一沉一沉地乱晃。
我说我帮你拿吧。
她说不用,我自己拿。
赵旧的家,是一个有钱人的家。那是一栋接近于别墅一样的房子,只是房子的前后左右,少了那种既能显示有钱又能显示一些滋味的东西,比如树的种植,比如绿地的布局,比如花的点缀,他那里也不是没有,失去了那张录音带的黄小麦,而是跟那些种在马路边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差异。黄小麦说,他们家也就是比别人多几个钱,没什么可观赏的。
她将胸前的随身听摘下来,挂到了我的脖子上,然后把我拉到一个阳台的下边,附着我的耳朵说,那张磁带我就藏在上面这个房间里,我上去,你在这下边等我,找到了我先扔下来,你帮我拿好。
我一听味道不对,好像她一去就肯定要出事似的。
头一次我没有去。
我说我去帮你跟他们好好说吧,赵旧会让你上去的。
她说赵旧现在不在家,你跟他妈说没用,他妈凶得很。
我指了指她衣兜里的那把菜刀,你不说拿刀还她吗?你给她还刀的时候,好好地跟她说说,她不会凶你的。
她把刀拿了出来,紧紧地攥在手里,一边比划一边说:我会跟她好好说的,我肯定会跟她好好说。
但我有点不太放心,我说,要不,你还是别拿这个东西进去吧,人家见了会以为你是干什么进去的。
她就又把手里的菜刀比划了两下。她说不会的,她知道她欠我一把菜刀,她一看见她心里就明白的。
第二次来人的时候,我的心才有了些许的动摇。毕竟是我把她弄进来的,我不能因为她骗了我,因为她咬了我,整天的抱着双膝,就丢了她不管了。
我说什么她欠你的,是你欠她的一把菜刀。
她说,反正她知道。
我说,我看还是我跟你一起上去的好。
她说不行,你一定要在下边。以防万一,团坐在泥地上发呆了。不同的是,以防万一你知道吗?
我想想也是。我说行,那你就进去吧。
她却忽然盯住了挂在我胸前的随身听,伸手上来摸了摸,然后无比信赖地凝望着我。然后说,如果我在房里出不来,你不要进去管我,你只要捡到我丢给你的磁带,你就走你的,然后你帮我拿到米城,拿给我爸爸,好吗?好像她那去的是一个出不来的地方,但为了他的父亲,为了她父亲要的那张磁带,她要义无反顾!
我一听就觉得又味道不对了!要是在往常,我的脸上也许会付之一笑,但这一次我脸上的肉竟冷冷地凝住了。我突然捏住她的双肩,我真的担心她会惹出什么意外来。
我说,要不还是让我先进去帮你试试吧。
她的脸上立时就绽出了笑容。她说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顽固呢?别罗嗦,听话!你就站在这里等我。然后转身往旁调皮地跳了两跳,就朝赵旧家的房门走去了。
我只好愣愣地望着她的身影。
我说小心点,知道吗!
她没有回头。她身上的那件白大褂忽然被风吹得往后一飘,只见她一闪,就在赵旧的家门口不见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房里的动静。
应该说,曾经有过一个很平静的时间,真的很平静,平静得我都快要屏住了呼吸。但那平静十分短暂,一阵激烈的冲突便狂风暴雨一般传来。
先是听到几声响亮的破碎声。
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很恶劣的声音。那肯定就是赵旧的母亲了。她说你要干吗你要干吗,你进我家来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黄小麦说不干什么,我来拿一张录音带。她说我要找他,你们帮我叫他一声,我求你们了!然后泪水不停地从脸上下落,身子也软软地跪在了铁门的脚下。
赵旧的母亲说什么录音带,她告诉他们她要见我,你给出去!我们家没有你的录音带,你马上给我出去!
黄小麦说别过来!我手里拿着刀的,你看见没有?
赵旧的母亲也许真的慌了,她说你要干吗,你想杀人呀,你给我马上滚出去!
黄小麦说你别过来,我拿了我的录音带我马上走。
赵旧的母亲说,我们家没有你的录音带,我赵旧说他已经给你送去了。
黄小麦说还有一张,是我藏在赵旧的床脚底下的。你别过来!我不会拿你的任何东西的,我就拿我的磁带,拿到了我就走。你不要这样,我手里有刀的!
屋里突然传出了有东西砸落在地上的爆炸声,那肯定是赵旧母亲的愤怒所致。我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我觉得再下去就肯定要出事了,我望了一眼空空的阳台,转身就往赵旧家的房门跑去,可我刚刚跑到门边,阳台就传来了黄小麦的呐喊。
她说你跑哪里去了,你快点过来,我要跳搂了!
我吓得一转身就又飞一样往回跑来,刚跑到楼角,就看到了黄小麦已经高高的站在了阳台的栏杆上,与此同时,一个穷凶极恶的女人在阳台边的房门口挥着一根长棍,正疯狂地扫往黄小麦。但那根棍子只在阳台的栏杆扫了一空,黄小麦早已纵身一跃,鸟似的往楼下飞来。
飞身而下的黄小麦当然没事,我接住她那样的一个女孩,就像是接住一只小鸟。但黄小麦的手里却没有拿到她想要的磁带,她的手里紧紧握着的还是那把菜刀。
我们俩跑到大街上的时候,她并没有茫然地遥望着天空,她突然大声地说道,算了,不要了!我说我们找赵旧再试一试吧。她说不试了,再试就没命了!你刚才看到没有?赵旧她妈那疯婆,凶得要命!我告诉你,上次要不是因为她,还有那个姓李的老师,我怎么进了疯人院呢?就是他们把我送进去的。我说不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你们家的什么人把你送进去的。
黄小麦说放屁!谁说的?
我说是你原来的病历卡上写的,我专门找来看过的。
黄小麦朝我奇怪地瞪着眼睛,她说你相信?你要是相信他们那你就等于相信了坏人了,你知道吗?
看着包扎在纱布下的手腕,我心里就禁不住地冒火。我说我不去!我说你让她疯去吧!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他们又不是坏人。
她说他们怎么不是坏人?你说他们怎么不是坏人?
我说你拿着这么一把刀闯进人家家里,人家当然要把你赶出来的,你不能凭这点说别人就是坏人。
她说我说的不仅仅是现在,我说的是以前,是他们把我送进疯人院的那个时候。
我说那时候你也是因为有了病他们才送你进去的嘛。
她又大声地说了一声狗屁!我那时根本就不是疯,我是被他们送进疯人院出来以后才疯的,也不是,我是出来后装疯的。
我看着她笑了笑,我说对,很多聪明的疯子都说自己是装疯的。她好像没有听出我话里的意思,她说你什么意思?她说我真的是装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要吓唬他们,我恨死了他们了。可他们也是恨死了我,这一点我知道,他们就是因为恨我才把我弄到疯人院去的。
我说他们为什么恨你呢?是因为你爸爸坐牢的事?
她说那种事我说了你也不懂,你也不会相信,我告诉你吧,我不跟你说过,那天晚上我在赵旧家里录了一张录音带吗?录完了我们下楼,后来我们俩在树下亲嘴的时候被我们一个姓李的老师看到了,像是失去了魂魄,你相信吗?
我有点想笑,我说不会吧,亲一个嘴她就恨你?
她说对呀,亲一个嘴有什么呢?男人和女人,有谁不想亲嘴呢?可那个姓李的,她看到了就觉得不行。她告诉赵旧的妈妈,说我勾引了赵旧。还说她和我妈原来是同学,说我妈生来就是一个烂货。赵旧的妈妈就张牙舞爪地跳了起来,不让赵旧再跟我往来了。赵旧也一看见我就躲,一看见我就跑开。我心里一恨,他妈的那姓李的!我于是整天跑去闹她,去骂她!我才不怕她,老师又怎么样?再说了,因为我爸我妈他们的事,我那时心情也不好。我也不想再读书了。我整天疯疯癫癫的到处晃,没想到他们就在背地里把我真的当成了疯子了,说我是得了精神病了,就一伙人在大街上追着我,把我塞了车里,拉进了疯人院。
黄小麦的声音一路惊动着四周的行人,人们都用一种怪怪的目光扫视着我们,有人还禁不住说出了嘴来,他们说这俩人怎么回事?有病了怎么啦?黄小麦的耳朵挺灵的,她猛地就回过了头去,她说你才是有病咧!
那人说没病你在大街上嚷嚷什么呢?
那时候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她让他们帮她把我叫过去。黄小麦突然在阳光里晃了晃手里的菜刀,晃得那些人哗地一声,就四散跑开了。有人连鞋子都丢在了街上。
我们就这样一边大声地说话一边在街上走着,最后竟走到了瓦城的街头。
她突然问,我们现在去哪?
我说你说呢?我们去哪?
她望着我愣了。有点傻傻地笑着。随后她望了望前边的公路说,要不,我就这样先去见见我爸爸吧。你说他会相信我吗?没等我回答,而是四下里到处乞盼地张望着,她又自己说开了。她说他肯定会相信我的,他要是不相信我,他就不会杀了那个人,你说是吗?
我说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吧,他要的那张磁带是我给砸坏的,我去帮你说说吧。她两眼便闪亮闪亮地望在我的脸上,就像一只感激施主的可爱的小羊。
于是,我们俩转身坐在了前往米城的长途班车上。
她爸爸被关在米城的监狱里。他是在米城被抓的。杀人后,他没有离开米城。
我们到达米城的时候是晚上。
我说你开一个房,我开一个房,我们开两个房好吗?
她却不干。她说不,我跟你住一个房。
我说问题是别人不会让我们住在一起的。
她却告诉我,说别人才不管你呢。
果然如她所说,我们站在柜台前登记住房的时候,柜台里的小姐只问一句,后边就不再问了。她说你们是要大房还是要双人间。我说要一个双人间吧。她就把钥匙放在了柜台上。我们就这样住进了房里。
因为拿不到她父亲想要的那张磁带,因为她拿到过的那张磁带是被我给毁灭的,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她在黑暗里也是久久的没有入睡,她不停地翻动着身子,等到她在床上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最后只剩了甜甜的呼吸声的时候,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凌晨了。
我悄悄地就爬了起来。我在桌子上给她留了一张一百块钱,留了一张字条,就偷偷地打开房门,溜到外边去了。
我在那张字条上写着,我出去散散步,可能晚一些时候才回来。我让她自己先到下边找东西早餐,但不要乱走,免得我回来了找不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