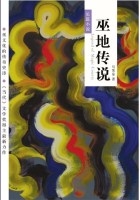陶羊子现在有钱了。他每月从芮总府拿到酬金,另外在钟园也有酬金,再加时不时有棋友的请客送礼。可钱多了,似乎还是余不下来,他花销也多了。三天二头与胡桃下馆子。他不可能再去吃那几角钱的简餐了。胡桃带着他,几乎吃遍了南城餐馆。他的出行也不再走路。以前再远的路,他都是走着去的。现在一段近路都叫黄包车送去。有客请他,他也回请。进戏院看戏,他便在秦时月包厢旁边开一个包厢,两人可以伸头交谈两句。在包厢坐着,少不了要给杂工小费,他不好意思单给服务生,凡来身边走动的杂工,他都会给,那些都是先前和他一起谋事的人。
陶羊子在围棋研究会的南院,租了一个大房间,那里出进都有人伺候。小巷里女老板的房间,他也不回,那里的一点租金实在算不上什么。但他很少去。有时去了,便带上一些东西给女老板。女老板现在一见他便迎着,十分亲热的样子,嘴里说着好听的话。陶羊子独自站在房间的窗前,听着风微微地吹过墙上没有贴平的报纸声息,回想着过去的时光,他想了许多。只有在这里,他的心是静的。他的心本来是粗糙的,现在变细了。因细而多出了烦恼。就像他的肠胃,大概是吃惯了粗食,而现在多吃了好东西,就时不时地会不舒服,生出腹泻来。
任秋过生日,陶羊子带了一件礼物去,他觉得她肯定会喜欢,价格有点贵,他想也没想就买了下来,这代表他的一片心。他到的时候,发现天勤已经在那儿,任秋手里正拿着方天勤送的一只西洋八音盒。只要打开盒盖,便响起生日快乐的曲子,还有两个特别漂亮的西洋少男少女,在音乐声中慢慢地前移靠拢相拥一下又旋转开去。任秋对着这个八音盒,笑靥如花。
任秋接过陶羊子的礼物,看了看,说声谢谢,就放到了窗台上。她转身看着两个男人说:“真高兴你们来为我过生日,我准备了一桌菜。”
方天勤说:“寿星不用忙的,出去吃就是,挑你最喜欢的饭店。”
陶羊子跟着说:“是啊……”
任秋说:“要我一个人,哪儿吃都行,也想不到什么生日不生日。你们来陪我过生日,我很高兴。何苦花那些钱……还是在家里好。可你们要答应我,今天别对我说什么棋不棋的。”
他们三人围着桌子一起吃了一顿,在陶羊子记忆中,他们仨从没一起吃过饭。任秋显得很高兴,但陶羊子感觉她的高兴多少有点做给他们看的,她并不习惯同时与两个男人交往。陶羊子还敏感到,任秋更照顾到天勤,给天勤的笑脸更多一些。
陶羊子清楚她与天勤的感情,但他不想让开,他想得到她,与她成一个家。但天勤毕竟在芮总府时间长了,等级也许比他要高,酬金要比他拿得多,比他更有优势。任秋虽然对他很好,不时露着亲昵,可他总能在她的言行中感觉到天勤的气息。他有点弄不清她的意思。
对任秋,陶羊子本来是没有这些外在比较的,她就是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她的家庭教养不比别的有钱人家低,儿时他们就不存在距离,更有一层师父的关系,他与她要比别人亲近。她应该成为他的妻子。
而外在条件也影响着人的内心。徘徊在社会阶层中的陶羊子渐悟到,人的社会身份千差万别,在他的感觉中,天勤哪方面都比他强。
可是,对任秋他绝不放手。他清楚天勤有好多女人,在女人场上,天勤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乡村的落后观念:玩女人占便宜毫无负担。天勤似乎还故意显露着,借以炫耀来证明他的社会价值。
可是对着任秋,陶羊子不好明说什么。她曾说她是知道天勤的,但她究竟知道多少?他要多说,便有“小人搬弄是非”的心理负担,这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所不容的。
从任秋家里出来,他突然想到了梅若云。他便去了颐园路。是梅若云出来开的门。她没请他进屋,他们在院子里站了一会。院子里的花都谢了,茎叶发枯,院角一片斜倒的残花,显着衰败的气息。又是一个秋天了,日子过得真快。陶羊子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五岁了。
梅若云没有像过去那样静静地看着他。她微微垂着头,松黑的花圃泥土上,有一小片花瓣,不知是从哪里吹落来的,它还是那么鲜嫩,橘黄的色彩依然清新。他与她说话,她抬头朝上的时候,眼睛里有着一点迷蒙。这是陶羊子先前没有见过的。以往她的眼睛总是明澈如水,微笑时,眼光中有如水波漾动的涟漪,蕴含着无限的神气。而眼下梅若云的眼神却略显茫然。
陶羊子一时不知对她说什么。原来的她神情是明净的,随便的一言半语,哪怕是默默无声,都化解着他的心绪。他注意到她的额角眼下有些浅浅的阴影,不如想像中那么白皙光润。是不是在大场合里见多了漂亮女人才心生异感?他再看看,感觉她还是唯一的,无可比的。
陶羊子开口问:“你最近好吗?”
梅若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陶羊子说:“你有不顺心的事吗?”
梅若云说:“父亲的生意不怎么好。”
陶羊子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他只知道有赚的当然有赔的。赚和赔都是正常的,赔掉了再赚就是。
梅若云父亲的生意经营,这些年转向了法国。陶羊子听梅若云说过,家里想让她去法国留学,只是她不想去。
陶羊子向她说起了这些日子来的感觉,对她诉说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多少是迷失了,他很希望得到她像往常那样的抚慰,熨平他紊乱的心绪。他问她,是不是这种烦恼,对有钱人来说都一样,不用在意。
梅若云抬起头来,“啊”了一声,像是没听清似的。
陶羊子说:“我真的愿意还像过去在戏院里那样,单纯地做事,单纯地下棋。”
梅若云微微地摇摇头说:“既然走出来了,就再也退不回去了。”
陶羊子想起来,他到芮总府当棋士,只有梅若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是不是她清楚他会遇上烦恼的?想当时她也是高兴的。现在陶羊子发现,女人是个谜,确实是很难弄清楚的。
从梅若云家出来,陶羊子心里添了一点烦恼。过去他不管有多少心事,只要一见着她,心里便像无数棋子如鸟儿一般飞移了,留下了一块空空透明的棋枰。离开她身边时,依然会带着这种明快的感觉。心中空空,不是空落而是空净。但这一次见面,却让他原来填满的心里,又加了一重堵。是不是进了上层社会,他整个儿像被吹胀的气球,摇晃地飘浮起来,接触面大了,而他内在的层面显得薄了,似乎一刺即破。
这天陶羊子去芮总府领酬金,听说一个叫宫藤、一个叫秋明的日本职业棋手早已进中国东北,从北向南,沿途与当地的棋手对弈,一路下来,几乎是势如破竹,只有在北平让先输过一盘,听说还是漏算了。这两位日本职业棋手大有杀遍中国棋界的意味,就快要杀到南城了。
芮总本来有令,芮总府棋士一定要杀败日本棋手。现在芮总变了要求:只要有胜局,不能让芮总府全部输棋。六位棋手都显得紧张起来。他们清楚:如果这一战全军覆没,他们也没有脸面再在芮总府里呆下去了。
陶羊子躲到女老板的后楼上来,只有在这里,他能沉静下来。他摆了几盘棋谱,感觉有点生疏。不像过去那样咬得紧了。他让自己的思维空下来,排除所有的杂念。他回想到他与松三的一盘棋,这是他与日本棋手下的第一局棋。细细想来,松三的棋不是每步都那么完美,但整个行棋的调子与中国棋手是不同的。他只与这一个日本棋手下过,并且只对过一盘棋。,那么其他的日本棋手又会是怎样的下法?棋力到一定层次,搏杀与计算都不成问题,对大局的把握与行棋的调子,尤其是知己知彼,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棋手之间,局部的变化与定型,基本是摸透的,对常型的处理,也有迹可寻。日本高段棋手肯定有不同处,所以能一路杀败众多中国棋手,并且还都是让子棋。
前几日,陶羊子在钟园遇上一位从外地来的年轻人,比他要小上两岁。听说是东北来的,号称东北虎。听说东北虎经常与当地日本军官中的棋手下棋,并且在东北棋界有了名气。他颇有信心来到南城,就想找芮总府棋士一决高下。但一连找了几位芮总府的棋手,没人与他对局。棋士们见多了这种各地来的想一下子扬名立万的棋手,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棋力。于是,东北虎便从南城的几处棋摊杀起,声称要杀遍南城所有的高手。这就杀到了钟园,在钟园下棋也有好几天了,把钟园其他的几位下得好的棋手都杀败了。
偏偏这几日陶羊子心绪有点乱,纠缠着步入上层以后的人生烦恼,很少到钟园去。胡桃只有来找陶羊子,说你再不出面,老家就被人家抄了。
陶羊子来到钟园。虽然对方并不是什么有名人物,但他的放言已惊动钟园下棋的棋手们,都想着要陶羊子教训教训他,听到消息能来的都来了,围成了一圈一圈。钟园老板告诉大家,对这位狂妄的东北虎,太当一回事,倒显得他是一棵葱了。
陶羊子本来也没当他一回事。开局的时候,径熟手滑,似乎入了对手的一个套子,空上就有了一些亏损。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吃的亏。这个定式他是研究过的。盘上的得失,只有对局者清楚,一般人看不出来。钟园里的棋手还认为是陶羊子一惯的走法。东北虎多了一点实空,信心大增,一步一步走得坚实。陶羊子觉得这位东北虎一步紧逼一步,自己所有的招数都被他破了。陶羊子很想在中盘,就采用先手官子来扳回棋空。但东北虎似乎官子上也颇有研究,一连几步都没赚到他的便宜。慢慢地连钟园里的其他几位好棋手也看出来,陶羊子的盘面不容乐观了。
陶羊子静下心来,他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先前他的用时一直比东北虎少。东北虎此时轻松起来,面有得色。想他一个年轻人从外地来,斩了芮总府的棋士,多有面子。接着他再横扫南城,也许能成中国第一棋手。
陶羊子只有放胜负手了。他把棋打进了东北虎的空中,走成了一个虎步,东北虎打了一手,陶羊子就势做了一个劫。西南王那一次与他走得最紧张的半局时用过此招数,是中国围棋传统中最强的搏杀招数,一下子把盘面弄乱了。这时就看棋手的棋力与算路了。陶羊子并不特别擅长这个,但过去他研究过,走黑棋时也用过。现在他执白用了这个手筋,白棋做的劫使东北虎紧张了,他怕打入的白棋整个地活起来,于是花了最大的力量去打这个劫,想一举歼灭进入的白劫。一个劫打来打去,劫材满盘找来,黑棋好不容易打胜了劫,封住了出口。但白棋两边多行了两步棋。在看起来无关紧张要的地方吃了黑棋二个子,还逼着黑棋包围打入进去的几个白子,紧气吃棋。看起来白棋被多吃了几子,其实吃棋处本来就可以算作黑棋的空。
东北虎这才发现,虽然他多吃到几个白子,但这一打劫作战,他亏空边角的两个子,同时白棋因吃两子形成了收官厚味。算下来,他亏空了不少。盘面上白棋的空已不比黑棋少了。
这时,连钟园的另几位棋力较好的棋手也算出来,白棋有贴子的优势。黑棋怎么也不够了。他们都露出了笑脸。再走几步,陶羊子更显出白棋的官子功夫来,黑棋连盘面也不够了。东北虎想使手段来争胜,陶羊子到底棋力强,更扩大了白棋的优势。东北虎只好投子了。
东北虎指着那个因劫打成一团的地方,说:“这里亏了。”
钟园的一位老棋手说:“弱棋怕打劫啊。”
东北虎想说什么,但棋输了,气也就弱了。输棋者没什么可说嘴的。别人的话都好像是千正万确了。
陶羊子心里明白,他的得胜只是经验上的问题。复盘的时候,陶羊子与东北虎聊着棋,指出他的棋受日本棋影响较大。东北虎承认他确实与一个叫天作的日本军官经常下棋。那也是一个棋迷,一有空就把他找去下棋。先是军官胜得多些,后来他们就势均力敌了。最后是东北虎稍稍多胜一点。毕竟日本军官不能一天到晚研究棋吧。
现在陶羊子又把那局棋复盘出来,他发现东北虎与松三的棋路有相近的地方。一位日本的业余棋手,还有一位长期和日本业余棋手下棋的棋手,他们下出的棋,让他感受到日本棋不同一般的棋路,他想弄清那棋路,但一时很难弄清。毕竟日本的棋路并非只是一个招数一个定式,而是整个不同的行棋思路。让陶羊子更感围棋的天地无限空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