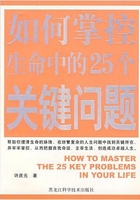二
《废都》的整体精神特征,有人名之曰“废都意识”,不失为一种简明的概括,只是需要具体深入的剖析。
读《废都》,我确乎感到惊讶和震悚,它那大胆,赤裸,彻底,毫无顾忌的暴露笔墨,实为多年来文学中所仅见,就像节竹寺里有位罗汉,撕开了胸膛亮出心脏让人看的形状。贾平凹的创作,向来以举重若轻、挥洒自如见长,颇得温柔敦厚之旨,其悲剧意识比较外在,更多的是乐感文化的自足,在这小说开始的部分,看他点染人物,铺排场景,熏染氛围,看他写酒席应酬,男女逗嘴,请客闲谈,很是叙次井然,且不时闪跳着幽默,以为贾平凹还是贾平凹;可是,越往后看就越难受,越压抑,越阴郁,前面欢愉、调侃的气氛迅即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种毁灭的悲怆和窒息。书中的大多数男女,虽也谈笑自若,虽也自寻乐趣,但像一些虚幻的影子,或像一群乱撞的没头苍蝇,或为眼前的微末利益驱使,或深陷在物欲肉欲中不能自拔,大家都像丢了魂儿似的,不知明天干什么好,谁也腾不出空儿思索一下生存的意义。因为灵与肉分了家,灵魂还留在昨天的残梦中,躯体却不能不加入变动了的世事,于是只能听凭外物的裹胁和刺激,作出条件反射似的被动反应。为了感恩,就去写吹捧文章;要吹捧,就要媚俗,就要添油加醋;添油加醋就惹出了官司;惹出了官司就要设法平息;要平息就不能不贿送字画,捉刀代笔地写文章;捉刀代笔就不能不作假,作假就不能不惹出新麻烦……这可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一旦进入了这种连环套、怪圈,就欲生不得,欲死无门了;可是,你能拦得住谁不进入这种连环套呢?是飞蛾就必然要扑火。这里的人们,头上没有理智的星光,脚下没有插足之地,大家都从原先给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抛了出来,一个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变得互相不认识对方,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甚炽,大家都忙于动作,终止了思考,只好把思索人的退化问题留给那头奶牛,把思索阴阳两界的神秘现象交给行将就木的牛老太太。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片物欲膨胀、精神荒凉的废墟。
它之所以出现如此悲凉的情景,是与《废都》中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有人批评《废都》中的人物环境缺乏现代都市意识,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观,没有霓虹灯、高速公路,没有架着金丝眼镜的留洋博士,也少中西文化的交汇冲撞,因而近乎城镇而非大都,庄之蝶也不像观念簇新的当代作家,腿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呢。这当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误读,还是用虚悬了的现代都市题材作品的要求来衡量之故。在我看来,《废都》的写西京城,写庄之蝶,主旨并非写现代都市文明的困境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而是写古老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颓败,写由“士”演变的中国文化人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西京城的土里土气,庄之蝶的偷香窃玉,大约都与这种绝对中国化的传统有关。
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像个大博物馆,同外界有种隔离感,街上不时可捡到汉砖,快要拆除的民房的门楼上,竟是郑板桥字画的砖雕;老百姓家里的两把矮椅、一个香炉,可能是唐代遗物;破破烂烂的院落,也许正是簪缨之族的故居,真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人从杨玉环的坟丘挖了一兜土回来,居然长出奇异的四色花,旋即花儿枯死,人儿病倒;有人在城墙上吹埙,声调呜咽,如泣如诉,等力气用完,那声音像风撞在墙角,无力地消失了。这是一种谁也逃不脱的精神气候、人文氛围。如果说,这种氛围终究是外在形态的话,那么,可怕的是,浸渍在这种氛围中的几千年的人们,渐渐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了一座废都生了根。这心中的废都,集纳了大量的古传丸散,秘制膏丹,集合着修炼千年的人格理想,行为模式,审美趣味,佛玄道秘,致使人们的外在环境虽已巨变,内在的心理结构却纹丝不动。庄之蝶一看到古玩就两眼放光,为之入迷;孟云房钻研《邵子神数》时一只眼瞎了,却偏说因为泄露了天机而“一目了然”,为之入魔。至于谈玄说道,巫医星相,品女人“脚”,赏女人“态”之类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废都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废都》像一个现代寓言。
事实上,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这是一种心灵的挣扎,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或在传统与现实的夹缝中惶惑莫名,无所适从;或由禁欲而纵欲,狂躁不安,自寻毁灭;或投机钻营,聚敛财富,重温财主缙绅的旧梦;或一腔旧式文人、破落贵族的傲气,作困兽之斗。书中所谓四大文化名人者,以及书商、农民企业家、编辑、研究员们,大率如此。书法家兼赌鬼的龚靖元之死,就很典型。他最后:“抱了那十万元发呆,恨全是钱来得容易,钱又害了自己和儿子,一时悲凉至极,万念俱灰,生出死的念头。”他们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可以商量,他们所表现的这种种意识、心态,不论叫废都意识也好,叫世纪末情绪也好,却不能不说反映着转型社会典型的精神特征的一方面。
我说过,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比较外在,这部作品中“牛”的思考者形象也仍然是外在的、表面的,可是,庄之蝶们缘于生命的颓废,却不能说是表面的。一般人只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混乱现象而看不到颓废,尤其不能从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矛盾中发现颓废。其实这种颓废包含着严肃的悲剧性,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无力跟上这种要求的冲突。
三
我揣摩贾平凹的写《废都》,最初一个重要的意图是:毫无讳饰地展示这个光怪陆离的浮躁时代、晕眩时代的生活本相,尤其是世俗化、民间化的本相,留下一部珍贵的世情小说。从穿插其间的那个唱民间谣曲的老头,可以见出此种意图。作者未必不知道今天的人看这些谣曲并不怎么新鲜,但后世人看它们,就大有兴观群怨的喻世价值了。可是,写着写着,主调发生了微妙变化,主观化压倒了客观化,自剖灵魂的倾向压倒了展现世情的倾向,多少冲淡了它作为世情小说的品格,也缩小了它对社会历史内容的涵盖。从根本上说,问题出在作家与庄之蝶这个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庄之蝶的角色经常被作家自己代替,以至无法分解。
然而,尽管如此,《废都》关于世情的描绘仍是极为出色的。鲁迅先生言及“世情小说”时说:“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舍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废都》的写法,正复如此,《废都》的结构很巧妙,貌似信笔所之,漫无边际,实乃精心结撰,细针密线,它以庄之蝶为中心,如蜘蛛结网一般地展开一层层世态风景,且联络自然,浑然一体,无生硬铺排,人为垒砌之病。庄与其他几个“文化名人”,钟主编、景雪荫诸人,形成文化圈子;与孟云房、夏婕、京五、洪江、周敏诸人,形成社交圈子;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成男女圈子;与市长、秘书、农民企业家、人大主任等,形成政治经济圈子;与牛老太太、刘嫂、惠明、阿兰、黄鸿宝老婆等,形成民间圈子。这些“圈子”其实是我们划分出来的,在作品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流水般无法分切。
在这里,细细品味作者怎样描写世态是没有篇幅的。我只想指出,作者写世情,一不是孤立地写,而是完全将世情化入艺术肌体;二不是冷静地旁观,而是带着浓厚的废都意识来看世情,往往看得深刻。譬如,钟主编的命运可谓惨矣,无疑反映着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坎坷,如牛负重。他最惨者何在?在于得不到应有的爱,得不到视若生命的某些寄托物。他渴望收到“梅子”的信,孰不知“梅子”本属子虚,那些情书,不过是别人不忍看他痛苦而编造的假信。他一直苦求高级职称,不料到死也没有得到;只因死后火葬场规定高级职称者可提前火化,他才总算得到一纸空名。这不是黑色幽默吗?但又未必不是世情的烛照。同是评职称,阮知非就轻松得多。他头顶着“文化名人”的桂冠,其实不学无术,惟一的本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耍獠牙”的舞台特技,也早忘光了。他以庄之蝶为他代笔一篇如何“耍獠牙”的论文,作为进身之阶,并且声言,“我是活鬼闹世事,成了就成,不成拉倒。”他自然不会不成功。与不幸的钟主编相比,阮知非才是浮躁世事中的当代英雄,他不惧怕名实相违,只怕缺少欺世盗名的胆量。此人后来发了横财,却被人捅瞎了眼睛,马上换了一副狗眼,从此看人看物总要低上几分。这不也是黑色幽默吗?但透过滑稽,正可看到世事中伪劣和浮滑的部分。
人情世态就是这样从作者的笔底浮现出来的。鲁迅先生谈到《金瓶梅》等“世情书”时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我虽不认为《废都》已臻此境,但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钩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生,他确是取了真经,得了神韵。他写黄鸿宝家的庭院小景,能让人想见一切乡村暴发户的气焰,他写“鬼市”的人影幢幢,交头接耳,能让人想见西京古都正在被“商品”这个怪物闹得夜不成寐。这样的世情,这样的氛围,才会有庄之蝶这样的人,否则,废都也就不成其为废都了。
四
庄之蝶的大名,出自庄子的《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那本意并不悲凉,是个自适其志,无拘无束的美梦,同属“物化”,变蝴蝶比变大甲虫要愉快得多。可是,当庄之蝶发现,自己很像旅游点上披红挂绿任游客戏耍的那匹大红马后,这名字就成了反讽。证之于《废都》,庄之蝶让人联想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语)的迷惘,“长恨吾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语)的无奈,庄之蝶三个字,无他,“吾非我”而已。
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作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理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庄之蝶是个精神上的集合体,是个极端,是个超负荷地承载着文化人的复杂矛盾心理的人,通过他,作品把特定时代一部分文化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揭示得淋漓尽致。当然,像庄之蝶这样性欲泛滥的毕竟不多,倘说这就是当今文化人的模样,不但社会要鄙视,知识分子说不定也要抗议。可是,超过性欲狂疾的表相,他的自我迷失,无着无落,他的背负传统,无力超越,他的灵魂无寄,困于外物,能说没有一定的典型性吗?只是一切被推到了极端,推到了颓废和沉沦的极端,这就不免引起骇怪。
应该看到,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有点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了,这就不免刺激有余,灵性不足,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全书也就缺乏更为深邃的人文精神,以至伤害了整体的艺术品格。但是,即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
有一次,周敏对庄之蝶的苦恼很不理解,曾说:“我不明白,你现在是名人,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倒喜欢这埙声?”周敏的不理解,也是一般人的不理解,但不理解庄的苦恼,也就无法理解《废都》全书。据书中介绍,庄之蝶是档次高、成就大、声名远播的作家,是个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他不乏善良和同情心,为了安慰孤苦的钟主编,不厌其烦地炮制假情书,但他又善良得近乎懦怯,周敏胡乱吹捧他,他体谅周敏一是为了报恩二是为了立足,也就默许了;景雪荫大闹,他于心不安,就写信道歉,说了实话。不料,这些善举、让步恰恰成了自掘的陷阱,给他招来无穷的祸患。书中写到庄之蝶,常用一个词,叫“泼烦”,此乃西北土语,意谓并非因一事引起的纷至沓来的烦恼。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以“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悲哀。
庄之蝶不是不想保持自己的本性、个性、独立性,做到我是我,不是物;我是我,不是他;我是我,不是“名”,但在现实面前一一崩溃了。作为名人,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包围他,需要他,他不愿别人以名人待他,却又意识到自己是名人,处处牵就角色,限制自我。市长利用他,制造假农药的厂长愚弄他,他最信任的洪江出卖他,全都离不开他的名人之“名”。他终于悟到,他其实是“名”的仆役。这可说是社会性烦恼。作为“作家”,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写什么正经东西,他的几桩宏伟文事,无非是写有偿的报告文学,写假情书,写假论文,写挽联,替法院某人之子代写文章之类,捉刀代笔,李代桃僵。结果他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性”,也没有了自己的“空间性”,找不到自己了。但正像唐宛儿说的,他又是个需要不停地寻找新刺激的人,既然作为生命存在的形式的创作已不存在,怎么办?只好到性欲狂潮中去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这可说是生存性烦恼。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但并非所有的人对忧烦都具有清醒的自觉。有人没入物质和世俗的无物之阵,人云亦云,只能感觉世俗的烦恼,不能感觉精神的烦恼,更不能感觉形而上意义的烦恼;庄之蝶则不同,他极度敏感,随时随地地追问着,我是谁,真正的我到哪里去了;加上他头脑里塞满了《素女经》、《闲情偶记》、《浮生六记》之类的劳什子,硬要到现实中寻找他所谓的古典美,他能不恍兮惚兮吗?有一次,他在太阳下发现自己的影子没有了,惊骇不已;他和唐宛儿在宾馆里胡搞,丑态百出,不一会儿又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就坐,泰然自若,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个怎样的怪物,或人是个怎样复杂的怪物。对庄之蝶来说,存在有如牢狱,自我去而不返,“性”也拯救不了灵魂,他便日甚一日地走向颓废。他的频繁的性生活,从最初的性爱逐渐转化为动物性宣泄,由确证自我转化为体验死亡。小说接近尾声前,他与唐宛儿有过一次疯狂的自虐和施虐式的性行为,自始至终还有哀乐伴奏,这很像三岛由纪夫的《忧国》里,剖腹自杀前的武士用性交来告别人世,性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庄之蝶与唐宛儿,终于像“两块泡了水的土坯”一样颓然无力。
还有比这更颓废的吗?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如果说,他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饰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