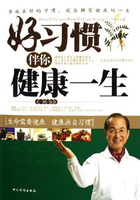白嘉轩是作者的一个重大发现。现当代文学史上,虽不能说没有原型,但的确没有人用如此的完整形态,如此细密的笔触,如此的评价眼光描写过他。在经济上,他当过地主,尽管因解放前三年鹿三已死他未再雇长工,恰好“漏了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具备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写他,不是纠缠在常见的阶级斗争眼光下的善善恶恶,也不是按着常见的反面形象的模式来处理,而是超越了简单化的批判层面,从文化的根因上来写。对于他的狡黠,迷信风水,视土地如命,作者倒也没有放过。小说开始不久,他就精心策划了一场买地戏,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自家福运绵长。这不是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思维吗?但这些不是白嘉轩的重心所在,由于他终生不脱离劳动,生活方式与自耕农并无不同,他表达的实际是农民的思想情绪,这个深沉的精灵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的地主可以望其项背。其实,在静默的、较为封闭的农村,至今我们仍能嗅到白嘉轩的灵魂的残余气息,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
白嘉轩一出场,就以他的“六娶六亡”以至不得不娶第七房女人的传奇经历先声夺人。小说劈头第一句话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有人发现这一段有声有色的描写与后面的情节关系不大,就认为不过是有趣的楔子或哗众的手段罢了,或认为无非是写其传宗接代的生活目标而已。其实不然。这里既有生殖崇拜的影子,又在渲染这位人格神强大的雄性的能量,暗喻他的出现如何不同凡响。作者写这位白鹿原的族长,有意疏离其社会性,强化其文化性。白嘉轩对政治有种天然的疏远,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内省、自励、慎独、仁爱上去,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扞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做人”,是他的毕生追求。“麦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那评价是这样一句话:“三哥,你是人!”这个评价也是他自己的心迹表露。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义,重人伦,尊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他淡泊自守,“愿自耕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一生从不放弃劳动。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他有如一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按说,白嘉轩所信奉的文化,所恪守的戒律是最压抑人性的,他却表现出非常独立的人格,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大约也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吧。如果权且抛开阶级属性和文化属性仅仅作为一个人来欣赏,白嘉轩沉着,内敛,坚强,不失为大丈夫,男子汉,具有强大的魅力。他的身形特点是“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后来被土匪打断了腰,自然“挺”不下去了,佝偻着腰仰面看人,如狗的形状,但在精神上,他依然“挺得太直太硬”。这个人,真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贯彻始终。当然,这里的独立人格与近代民主思潮所谓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维护他的人格尊严和他所忠诚的纲常名教,白嘉轩遭受的精神打击异常残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惟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食,为的是让他们懂得“啥叫粮食”。长子白孝文新婚后有“贪色”倾向,被他警觉,及时遏制,小女儿白灵是他掌上明珠,任其娇纵,可是一发现白灵有离经叛道的苗头,他即不惜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只当她死了”。凡是事关礼教大义,他就露出了很少表露的残忍性。对于白孝文的堕落,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维,毁了的不止是一个孝文,白家要毁了。”孝文倒向荡妇田小娥的怀抱一节,是深刻揭示白嘉轩的灵魂最有力量的情节。起初这只是“杀人的闲话”,等到眼看就要证实的瞬间,作品写来真有惊天动地,万箭钻心之力:
“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了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这真是灵魂的电闪雷鸣!能够承受一切的白嘉轩,在这个静静的雪夜体验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死亡和彻底绝望,他被真正击中了要害。我们不能不赞赏作者的诛心之笔。然而,即使面对如此摧毁性的打击,白嘉轩也还没有倒下,可见他的精神之可惧,生命力之泼旺。他说:“要想在咱庄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鹿三的一句:“嘉轩,你好苦啊”,道尽了他为维持礼教和风化所忍受的非凡痛苦。
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煞人性的尖锐矛盾。这也可说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义,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软。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田小娥死后,尸体腐烂发臭,后来蔓延的一场大瘟疫据说就是由她引起的,村人们无不栗栗自危,对这昔日的“淫妇”、“婊子”烧香磕头,还许愿要“抬灵修庙”。白嘉轩却不顾众怨,沉静如铁,说:“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他果然在小娥的旧居上造了塔,连同荒草中飞起的小飞娥一并烧灭。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是最冷血的食人者。
的确,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作者是否无条件地肯定传统文化的疑问。只有把与白嘉轩对立的另一人物鹿子霖拉出来一起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白嘉轩是真仁真义,鹿子霖就是假仁假义。白、鹿两家的矛盾贯串始终,这两家也确乎为争地争权发生过一些冲突,特别是鹿子霖的巧设风流圈套拉孝文下水,深重地伤害过白嘉轩。但我以为,白、鹿两家的矛盾并不像有些作品,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争,它是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是白鹿原的“乡约”,是反动政权布置在村社里的爪牙。他贪婪,阴险,自私,淫荡,舍不得放弃任何眼前利益。他也耐不住半点寂寞,“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被欲望和野心燃烧着,一面在上司田福贤面前摇尾乞怜,一面在田小娥身上发泄疯狂的占有欲。他的两个儿子都很成材,兆鹏是中共高层领导,兆海是国民党内的抗日军官,他除了在不同时期从儿子们身上分些余炎,夸耀乡里,并无多少真挚的骨肉之亲。真是尊长不像尊长,父亲不像父亲。白嘉轩对官职坚辞不受,他却为谋官极尽钻营;白嘉轩不靠官职声威自重,他却必须借一个官名撑持门面。冷先生一语:“你要能掺上嘉轩的三分性气就好了”,点穿了他极端自私的卑污人格。他有时毒辣得惊人,看着因捉奸而气昏倒地的白嘉轩,“像欣赏被自己射中倒地的一只猎物”;有时又怯懦得可鄙,受儿子牵连入狱后逢人表白,以泪洗面。当然,他也不是天良泯绝到了万劫不复,“麦草事件”中他与儿媳妇在性心理上一报一还,耳热心跳,潜台词丰富,但终究还是在乱伦的边缘收住了脚。再说,他的贪婪燥热,急功近利对白鹿原的沉滞生活也许还有点推动作用呢。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像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是,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噬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他怎不倍感身心交瘁呢!
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预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生活的长远价值问题,以至写出这个悲剧的作者也未必能清醒地解释这个悲剧。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就是二十世纪末叶的今天,这个悲剧也没有绝迹,现代国人不也为找不到精神家园和文化立足点而浮躁、焦灼吗?我们看到,虽然白嘉轩在白鹿原上威望素着,但在几十年颠来倒去的政治斗争中,他愈来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愈来愈陷入无所作为的尴尬。怀抱着仁义信念的白嘉轩发现,昔日兹水县令授予“仁义白鹿村”的荣耀已成旧梦,暴动、杀戮、灾祸、国难、流血的武装斗争却接踵而来,他无力回天,只能和他的精神之父朱先生一起,把白鹿原喻为“烙烧饼的鏊子”了。纵观白嘉轩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创巨痛深。他为反对横征暴敛发动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他被游街示众,事后并不参与血腥报复;他被土匪致残;他经受过失女之痛,丧妻之悲,破家之难,不肖子孙的违忤之苦……但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文化信仰。他坚持认为,“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他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既看不惯共产党,也看不惯国民党,在现实斗争中无所凭依,就只能做些积德行善,维持风化的事务,到了最后,他除了在冷寂中续续家谱,己无所事事。这不是一个抱着农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吗?
究其根本,白嘉轩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某些精华,东方化的人之理想。我同意这样的看法:“白嘉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我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和传统文化区别开来,白嘉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是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在于,作者缺乏更清醒的悲剧意识,小说临近尾声如强弩之末,白嘉轩的悲剧性本应愈演愈烈,作者却放弃了最后“冲刺”,遂使“生于末世运偏消”的悲剧力量的挽歌情调大为减弱,实为全书最大之遗憾。
四
《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白鹿原》一书中交织着复杂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和党派斗争、家族矛盾,但作为大动脉贯穿始终的,却是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也是全书最见光彩,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无数生命的扭曲、荼毒、萎谢,构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战的惨烈景象。人不再是观念的符号,人与人的冲突也不再直接诉诸社会观和价值观的冲突,而是转化为人性的深度,灵魂内部的鼎沸煎熬。
如果抛开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成见,我们将发现,黑娃也好,白孝文也好,田小娥也好,他们都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异常复杂的形象。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她早先是郭举人的小妾,实际地位“连狗都不如”,是一种特殊的锦衣玉食的奴隶,性奴隶。她与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闷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她和黑娃都首先是为了满足性饥渴,但因为合乎人性和人道,那初尝禁果的颤栗,新锐的感觉,可以当作抒情诗来读。小娥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罢了,可这点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轩的“礼”斩绝了,不准她进祠堂,因而也不被白鹿原社会承认。黑娃出逃后,她伶仃如秋燕,无依无靠,鹿子霖趁机占有了她,她虽出于无奈,但也带着出卖性质。社会遗弃了她,她也开始戏弄社会;她是受虐者,但也渐渐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只是,她常常找错了对象。她的诱骗狗蛋,已有为虎作伥之嫌,至于在鹿子霖的教唆下,把白孝文的“裤子码下来”,则已堕为宗族争斗诡计的工具。白嘉轩用“刺刷”当众打得她鲜血淋漓,这固属封建礼教对她的摧残;她以牙还牙,诱白孝文成奸,给“清白”泼污水,也不失为予与汝偕亡的决绝;可是,受鹿子霖操纵,等于助纣为虐,又使仅有的一点正义性消失殆尽。这是多么复杂的纠葛!善耶?恶耶?是反抗,还是堕落?是正义,还是邪恶?实难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