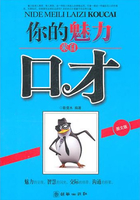两家门前都停着十几辆马车,声势浩大。西园门前的马车全是黑漆平顶,车厢上用古篆体雕刻着典雅的“张”字,乍一看上去朴实无华,实则宽大轩敞,乘坐起来颇为舒适。徐家门前的马车朱轮盖轮,富丽堂皇,精致讲究,显见得马车主人非富即贵。
张劢微微笑了笑,娘亲还是同从前一般讲究,出趟门兴师动众的,竟跟着十几辆马车。若是爹爹独自出行,两匹宝马换着骑便好,哪用得上这些。
徐逊抱着弟弟骑在马上,望着自家门前停着的马车,心中奇怪。舅母来了?居然没有提前写封书信,也没有遣仆役知会一声,这可透着怪异。照理说,舅母若来,爹娘定是知道的,应该大老远的打发人迎接才对。
虽是心中奇怪,面上自然不会流露出来,对坐在身前的徐述温和说道:“阿述,咱们到家了。”到下马石前,徐逊自己先下了马,回身把徐述抱下来。张劢却是抱着徐逸飞身下马,姿势洒脱优美,看的徐述十分羡慕。
徐逊和张劢拱手道别,分别护着自家女眷回了家。这十几辆马车停到门前,可想而知来了多少人,回家以后都有的忙碌。相互拜访、引见,都是安顿下来之后的事。
陆芸和阿迟下车换轿,回了内宅。回去后陆芸且不管什么舅太太、表少爷,先把阿迟拉到内室,拉着手细细打量,“闺女,没伤着吧?”阿迟笑嘻嘻,“真没有,才斜了那么一下,就被托住了。”在车上您已经问了很多遍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陆芸还是不放心,“如今不便声张,晚间悄悄请个大夫来,给你扶扶脉。”阿迟乖巧点头,“成啊,听您的。”今天也算历险了,不瞧瞧大夫,爹娘不会放心的。
说完悄悄话,母女二人出了内室。机灵的丫头昌化曲膝行礼,脆生生回道:“舅太太带着陆家大少爷,严家五少爷,陆家三小姐、四小姐,严家大小姐,二十位侍女,三十名护卫。陆少爷、严少爷并护卫们都请在外院安顿了,舅太太和三位表小姐,如今在千里阁。”陆琝在凤凰台单住一所庭院,名为千里阁。
陆芸凝神想了想,“把映霞馆收拾出来,请舅太太暂住。”。映霞馆房舍宽大,足够大嫂一行四人住的,便是再带上二十名侍女,也不拥挤。
昌化答应了,自去行事。陆芸安顿过一应琐事,梳洗更衣,重匀粉面,满面春风的带着阿迟去到小花厅,准备招待远道而来的娘家亲戚。
“妹妹,我这可想死我了!”一名相貌雍容大方、眉眼慈祥端正的中年贵妇出现在厅门口,含泪说道。陆芸忙起身迎了上去,“嫂嫂,多年不见,所幸您风采依旧!”
这中年贵妇自是陆芸的娘家嫂子陆大太太了。她身后跟着七八个俏丽的丫头,三位衣饰华贵、相貌端正的妙龄少女,分别是陆大太太的女儿陆珍、陆玲,和严家大小姐严芳华。
姑嫂二人执手诉着离别之情,良久方收了泪,分宾主坐下。陆芸口中问着,“二老可好?妹妹不孝,已是多年未曾回家。”陆大太太笑道:“二老身子都硬朗,精神头比咱们还强呢。”陆芸大觉安慰。
陆芸招手叫过阿迟,“快拜见大舅母。”阿迟恭敬应了,规规矩矩行礼,“大舅母安好。”举止如行云流水一般优美自然,礼仪大方周到,竟是一丝毛病也挑不出来。
陆大太太满面含笑,“好孩子,快起来。”亲手拉起阿迟,细细打量了,眼中掩饰不住的惊艳之色。这丫头生的实在好看,难怪琝儿会生了痴念。
陆大太太送了一只赤金镶珍珠手镯给阿迟,“好孩子,戴着玩罢。”这手镯是把黄金打成细细的金丝缠绕而成,样式精巧别致,颇为不俗。阿迟拜谢了,“谢舅母厚爱。”
陆珍、陆玲、严芳华也过来拜见了陆芸。陆芸先拉过陆珍、陆玲亲热了一番,“上回姑姑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还小,如今可长成大姑娘了。”又拉着严芳华夸了一回,“不愧是大嫂的侄女,极是出挑。”每人送了一只镶珠嵌宝的蝴蝶金钗,灵动可爱。
陆大太太说起这次南京之行,颇有焦虑之色,“玮儿比琝儿还大着四五岁,功课却还不如弟弟,我未免着急。恰好侄儿英华要到南京求学,我便想着,玮儿到南京拜了大儒为师,许是功课会有起色,也说不定。”
陆玮是长子,性子忠厚,才能却平庸了一些,不如次子陆琝机敏。陆大太太忧心长子的前途,带他到南京投奔名师,也在情理之中。
陆芸笑道:“极是应该,阿玮如有名师指点,课业定会精进。”陆大太太叹息,“但愿如此。咱家在武定桥的宅子,我已命人去收拾,待收拾妥当了,玮儿、琝儿和英华侄儿一道住过去,离着学堂也近便。”
陆芸并没多留,“阿玮性子沉静,有他管束着,阿琝和令侄定也是安心学业的。”陆家在武定桥的老宅,一应家什俱全,方便的很。再说武定桥确实离国子监近多了,凤凰台地方虽幽静,却有些偏僻。
陆芸竟不挽留,陆大太太一边松了口气,一边又觉着若有所失:小姑竟不挽留么?好似对玮儿、琝儿没什么姑侄之情一般。
陆大太太看着阿迟微笑,“好孩子,听说你要抄本佛经给老太太?真是孝顺懂事的好孩子,老太太见着佛经,必是高兴的。”
提起抄佛经,阿迟笑意盈盈,“舅母,是我们兄妹四人一道,要抄本佛经送给外祖母。大哥,我,还有阿述、阿逸,每晚都会洗手焚香,恭恭敬敬为外祖母抄录一段佛经。”
陆大太太心里更不是滋味了。怎么着?阿迟竟然根本没想着讨好外祖母,拉着哥哥、弟弟一起抄经。难不成,阿迟她年纪尚小,不通世事?
陆琝要到国子监读书,老太太命他借居徐府之时,陆大太太自是明了老太太的居心,先是连连冷笑,继而不屑想着,“男女结亲,只有男家求着女家的,我横竖不开口求亲,看你们能怎样。”阿迟动了心,小姑子动了心,那有什么用?我这当娘的不吐口,亲事便成不了。
若是少男少女间不小心出了点子什么,那更是对不起了,不知羞耻、不知名节为何物的女孩儿,我们陆家不要!上赶子贴过来么,好不要脸。
陆大太太本是安安生生留在安庆,等着小姑子夫妇遣媒上门时,气定神闲的驳斥一回。谁知左等右等,凤凰台音信渐疏,一点献殷勤的动静也没有。
严芳华已是十六岁,等不起;陆玮功课平平,眼见得科举无望;严英华在家里吵着嫌老师不好,耽误了他;陆珍、陆玲时时惦记,“南京很繁华,真想去开开眼界。”几件事凑在一起,陆大太太决定亲赴南京。
本以为自己一来,小姑子会带着儿女隆重迎接,一盆火似的赶着,阿迟更会含羞带怯,一幅小儿女情态。谁知小姑子亲热归亲热,却也仅仅是亲热而已,阿迟落落大方的,星眸坦荡,毫不拘泥。
陆琝是自己最看重的次子,老太太最宝贝的孙子,陆家这一辈人最卓异不凡的少年郎,多少名门闺秀见过他一面便会念念不忘,怎么会这样?陆大太太想不通。
阿迟跟陆珍、陆玲、严芳华坐在一处,和气的介绍南京景色,“金陵第一名湖莫愁湖,南朝第一寺鸡鸣寺,燕子矶,阅江楼,清凉山,夫子庙,栖霞山,都值得一看。”
陆玲只有十岁,一脸稚气,“阿迟表姐,这些地方你都去过么?”阿迟点头,“家父家母带着我和哥哥、弟弟们去过,风景极美。”
陆玲羡慕的不行,“阿迟表姐你真是见多识广。”她才九岁,已是被关在家里学女工、读书,磨性子,外出游玩对于她来说是很奢侈的事。
陆珍跟阿迟差不多的年纪,眼中也有艳羡之意,“姑丈姑母待阿迟表姐真好。”带哥哥弟弟的时候,也没忘了她,可真不坏。
严芳华矜持的笑着,“琝表哥借居贵府,多蒙阿迟表妹照看,我们是很感激的。”这位阿迟姑娘确实貌美动人,那又有什么用呢,琝表哥只是暂时借居罢了。
阿迟失笑,“严姐姐这话欠斟酌,表哥借居我家,家父可以照看举业,家母可以照看日常起居,家兄可以做伴陪同,便是我家小弟,也可以和表哥切磋功课,只有我,却能照看表哥什么呢?我和表哥不过偶一见面,点头问好而已,这般小事,当不得严姐姐郑重相谢。”
严芳华涨红了脸,说不出话。陆玲天真说道:“是呢,阿迟表姐又不管家,照看不到哥哥什么的。哥哥的日常起居,都是姑姑照管,可精细了。”
陆大太太慈祥笑着,冲几位小姑娘看过来,“芳儿名芳华,阿迟名素华,两人的名字听起来倒像姐妹。瞧瞧,两人坐在一处,竟也有几分相像。”
阿迟笑盈盈站起来,“回舅母的话,爹娘兄长都唤我阿迟,老亲旧戚人家,闺中好友,也唤我阿迟。我竟是觉着,小名带‘阿’的姑娘家,跟我才像姐妹。”
陆芸哧的一声笑了,嗔怪指着阿迟,“听听这孩子话!小名带‘阿’的姑娘家,光南京城便有成百上千呢,你便有这许多姐妹不成?”
众人都笑起来。正说笑间,徐郴下衙回家,先在外院和陆玮、严英华等人相见了,说了会儿话,带他们来到内宅,拜见陆芸。
阿迟起身要回避。陆大太太嗔道:“这孩子!又不是外人,你表哥,你严家表哥,有什么见不得的?”阿迟笑着福了福,做害羞状,走了。
陆玮、严英华拜见过陆芸,便各自回房,梳洗更衣,稍事歇息,以备晚上的接风宴席。陆大太太等女眷更别提了,那是一定要沐浴更衣,好好打扮一番的。
陆芸还没来的及跟徐郴说两句话,西园便送来许多土产,“我家侯爷和夫人一路走来,随手买的,送给少爷、小姐玩耍。”有小火炉,小风车,憨态可掬的瓷器娃娃等,另有各地著名小吃、京城小吃。都不贵重,却显着亲近。
徐家则是送了各色精致小菜,数瓶香洌的果子酒,还有新鲜的鹿肉粥、羊肉粥、虾粥等,更是家常。张憇专程使人过来道谢,“粥极鲜美,老爷子赞不绝口。”
紧接着,武乡侯府送来不少珍贵补品、药品,来送礼的管事嬷嬷极为殷勤,“给大小姐陪不是。今日之事,必定会给大小姐一个交待。”陆芸并不多说什么,只客气的微笑着,把人送走了。
徐郴这才知道阿迟遇险,皱眉道:“请大夫看了没有?”阿迟轻盈的转了一个圈,“您看看,我真没事。”陆芸忙道:“不想惊动了人,原想着晚上悄悄请了大夫来,给阿迟扶脉。”
徐郴摇头,“不必等,这会子便请去。”命人请了相熟的大夫。这大夫姓吴,医术很好,却有些脾气,细细给阿迟诊过脉,沉下脸,“徐侍郎,您消遣我还是怎么着?令爱好好的,看的什么病?”背起药箱走了。
徐郴板了半天脸,这才会笑了,阿迟也笑,“我都说了,好好的,任事没有,您偏不信,这下子可好,把吴大夫得罪了。”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大夫多难得呀,硬是把人气走了。
“得罪不了。”徐郴微笑,“爹爹跟他相交多年,这点子小事,他不会真恼。”他就这脾气,跟谁都横,跟谁都不会假以辞色。
徐郴亲笔写下谢函,命人送到西园。这回多亏了张劢,不然阿迟难免受伤。想到粉团儿一般的女儿差点摔倒,差点受伤,徐郴又是心痛,又是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