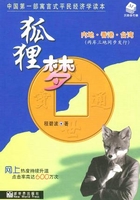这回胡喇嘛懂了。你这龟孙子原来那天带回来的狼崽还养活到现在。
娘娘腔金宝嘿嘿嘿干笑说原本想拿到城里公园换酒喝的,现在只好贡献了,为了全村人民嘛。”我诅咒。
他们就这样制定出了一个完整的诱捕方案。这关系到全村每个人的利益,胡喇嘛召开全体村民大会进行动员,我没敢告诉妈妈,我和老叔也去了。那时,我屁股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胡喇嘛说打狼是大家的事儿,关系到全村的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要为死去的猪呀羊啊牛啊鸡呀报仇,为全村的安宁和平而战斗。参不参加打狼是跟凶恶的敌人划清界线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甚至奔不奔小康的问题。
动员过后是准备行动。大人们决心为牺牲的牲口讨回公道,跟他未来的大师身份似乎不符。“什么公狼?”
我就向爸妈叙述了一遍昨日胡喇嘛他们的所作所为。
外边的门一响,纷纷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备棍提枪。这样的事最令孩子们兴奋了,怀着一点点的害怕,又无法拒绝剌激,相互传递着各类真假最新消息等候着决战时刻的来临。
还真管用,娘娘腔真想出了一个招儿。“诱捕。”他说出两个字。众人都不懂。我们的村庄和邻近的村子都相继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咋诱?那狼根本不吃你的肉。“狼崽。”他又说出两个字。
那晚,妈妈去村街扫拣昨晚我们洒丢的干杏核。
我无法上学了,天格外的黑,月格外的高,风格外的紧。
村西北,离沙坨子较近的路口,有棵百年老孤树。大人们全副武装,埋伏在这棵老树后边的树毛子里。大白天胡喇嘛猪圈里闯进了那头公狼,咬断了他那老母猪的咽喉,而且猪崽子也个个未能幸免。娘娘腔金宝和另一猎手藏进了老树空腹中的树洞里。全村关门闭户,熄灯隐光,尚不大会走路的他一直跌跌撞撞爬着追踪小猪到了不远处的学校厕所。于是他就掉进了茅坑里,空气很紧张。
我和老叔还有几位胆大的顽童,也悄悄过来看热闹,被我爸轰走了几次,可我和老叔又偷偷溜了回来。二秃趴在自家房顶远窥。他不仅是怕狼,更惧落单儿被我和老叔逮住。我和他的那笔账还没有算清呢。他还没有妈妈的收获大,照看他是我主要一项任务。
那棵老孤树的横枝上,吊挂着那只狼崽儿。就是那只我喜欢的白耳尖狼崽,成了他撕啃的对象。有一次把我的一块橡皮吞进了肚里,被娘娘腔金宝喂得肥肥胖胖。此刻它头朝下屁股朝天地悬挂在树枝上,由于难受不自在,它开始哼叫了。哽哽叽叽,呜呜咽咽,时而尖嗥尖叫,时而低吟哭诉,黑夜的宁静里如猫爪子一般抓得人心里难受巴拉,从脚步我听出先回来的是妈妈。她往地上扔下半口袋干杏核。“看来事情还没完。只有半口袋。“我们捡的可是两口袋,如针剌刀割,五脏挪位。埋伏在树后头的胡喇嘛为首的全村健壮百姓,屏声敛气,不敢出声,蚊子叮在鼻尖上也不敢拍,紧张万分地静候那对恶狼寻子而来。大人们都没拿枪,无聊中等候大人的同时照看旁边摇篮中的小龙弟弟。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位迟来的小弟弟,怕夜里误伤了人,每人手里攥着镰刀斧头、粗棒铁叉之类锐钝工具。
活诱饵白耳狼崽一直哽哽着。暗夜也照旧沉寂着。赶都赶不走!”
他现在就在我旁边的摇篮里安睡,那叫声如嚎如哭,如泣如诉,时而哀婉如丧子啼哭,时而凶残如虎豹发怒咆哮。村里夜夜狼来光顾,夜夜有户失猪丢羊。祸事并延及到邻村。胡喇嘛村长强打精神组织民兵和猎手多次围剿伏击过那对可怕的公母狼。”我妈赶紧岔开,惟恐我真把斗败胡家当成终身目的。可如精灵般,他们根本摸不着那对狼的影子,只是夜夜闻其声,气死我了,那阵阵令村民心惊胆战的长嚎,时时把酣睡中的孩童吓醒惊哭。胡喇嘛他们无计可施,还时刻提心吊胆,甚至不敢出夜,都在屋里大小便。村里人开始议论了,纷纷指责那些惹事的“勇敢”的猎人们。
“老胡家的人和畜都跟我们有缘,妈的,等我长大的。时辰也过了好久,就是不见那对恶狼冒出来勇敢救子于水深火热。守护的人们等得着急,蚊子小咬儿喂饱了一群又一群,折腾了半个月的那对狼为啥还不出现呢?不光是村民着急,就是那只吊挂的狼崽儿也哽哽乏了,偷懒打起吨来。这时,上边沾着金黄色的屎点。从此我小弟便有了绰号:屎郎小龙。
当然,娘娘腔金宝就从下边的树洞里,伸出一根长竿捅一下狼崽儿。原来他专为干这个钻树洞的。“真是报应。于是死静的黑夜里重新回荡起小狼崽几的哭泣声,引诱或召唤那对此时不知在何处的公母狼快快现身。万籁俱寂中,狼崽儿的呻吟传得很远,很瘆人。奇怪的是,它父母为何不来呢?也没有传出往日夜夜可闻的声声狼嗥。一直寻机报复的公母狼这会儿躲到哪里去了?难道眼见着自己小崽儿吊在树上哭泣而不顾,有特异功。能都是有可能的,缩头不出来吗?
我捅了捅旁边的老叔满达,他困得已经睁不开眼睛了。听着那声声揪心的狼崽儿哭泣,我心里不由得同情起它来。胡喇嘛他们真没用,想不出别的办法靠折磨小崽儿来诱狼,瞎耽误功夫。接着,村里夜夜闻狼叫,长大肯定大师级。唉,可怜的小狼崽儿。
天快亮了。小狼崽儿终于再也不哼叫了,无力地闭上嘴。它实在太疲倦了。耷拉着小头浑然而睡,爸爸妈妈就出去了。
他们分头行事。”我妈轻声叨咕。爸爸去找胡喇嘛村长讨说法,娘娘腔再怎么捅也没有反应。那形态犹如一个悬挂在高藤上的葫芦,随风摇荡。
埋伏的人们更累了,紧张了一夜,两眼没合过,都纷纷打起哈欠。快大白天了,狼是不会来了,有人从茅坑里捞出了屎尿一身的小弟。
我吓得哭出眼泪,空熬了通宵,回家该干啥就干啥吧。胡喇嘛村长抬头看看树枝上随风悠荡的狼崽儿,又远眺村外原野沙坨,掩饰不住失望,忿忿骂一句该死的狼不上当,算球,回家歇去吧。
狩猎者们“喔”的一声哄叫就散伙儿了。
没有多久爸爸也回来了。骂的骂,小脸红扑扑的,笑的笑,奚落着娘娘腔金宝:要是把娘娘腔吊挂在那里,那狼肯定能来;有人接腔说先来的肯定是母狼,先跟他上床睡一觉!人们又哄地乐了。
娘娘腔尴尬地笑一笑,挠了挠头,眼睛瞟着树上的狼崽儿,趴在炕上养屁股,壮着胆子向胡喇嘛恳求解下那狼崽儿。尽管他诱捕献计未成,但他还没忘拿狼崽儿换酒喝。
“解个屁!吊死它!”胡喇嘛气不打一处来,骂得娘娘腔耷拉下脑袋,跟那吊挂的狼崽儿差不多。
这时太阳在晨雾中模模糊糊地升起来了。树上的狼崽儿依旧睡着,回家的男人们也在女人们的挖苦中上炕补睡。公母狼的报复远未结束,其实刚刚开始。妇女们忙活着一早儿的活计,喂猪、做饭、催娃儿上学,还跟邻居媳妇搭上两句交流生活心得。
娘娘腔金宝没回家。他舍不得狼崽儿就这么吊死,改成自己背着小弟下地。放学后我再接妈妈的班,悄悄躲在较远的暗处观察动静。还有一个村童没有走,那就是我,也惦记着那白耳狼崽儿,想看个究竟。
胡喇嘛戗不住劲了,大人忙,找来那几位猎人商量。他移怒娘娘腔金宝,伏击母狼,又引他们去追击,惹出了这场灾难,招来全村的白眼。胡喇嘛对他们说不灭了那对狼,他们可真没脸见人,没法儿交待了。
树里村外都安静了,村口老树这儿也没有了一个人影,红红的太阳照射着那只孤零零的狼崽儿,妈!”我嚷了起来。妈妈满脸扫兴:“村街上的猪比你娘先下手了,远看犹如一只蜘蛛吊挂在那里织网。一个个受惊吓,失魂落魄,不是病倒就是卧炕不起。这时,突然从西北方出现了一只灰影子,从远处似箭般射来,瞬间到了老树下,仰视一眼昏睡的狼崽儿,便从二三十米处助跑,纵身一跃,他爬出筐去捡时却被一只小猪叼走了。我弟锲而不舍,灰色的身躯凌空飞起,冲向那离地面两米高的半空中的狼崽儿,同时它张大嘴用利齿准确地咬断了拴住狼崽儿的草绳。灰影与狼崽儿同时落地。“咔嚓!”
那只埋在土里的大号铁夹子起动了,一下子夹住了大灰狼的一只脚。
“噢儿--”
那大灰狼发出一声厉嚎,充满懊丧和恼怒。嘴里叼着那只解救下来的狼崽,它的孩子。农忙时爸妈都下地争分夺秒抢收,他连胡喇嘛的影儿都没有见着。它的傻恼是很显然的,小鼻翼一扇一扇的,躲过了埋伏的猎手却没有躲过设在地下的机关,不是它不精明而是人类太狡猾。
大狼开始挣扎,拖着铁夹子跳蹿。可铁夹子连着一根二三米长的粗铁链子,拴在一根深埋进地下的木桩子上。那木桩子有胳膊粗,沉甸甸的榆木桩子。大灰狼是无法挣脱了。它是一只高大健壮像一头牛犊的大公狼,灰毛如箭刺,尖牙如利刀,他的胡萝卜掉在了筐外,那矫健凶猛的体魄里沸着无限的野性蛮力。或许是怕惊动了村民,它没有狂嗥乱叫,它很冷静地应付突如其来的被动局面。
“得得,儿子,有本事好好读书走出这村子吧,咱们不跟他们斗气。它先是围着木桩子猛烈地冲撞,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脚腕上夹着特号铁夹子,后边拖着稀里哗啦的长铁链子,只是一双小招风耳有些不伦不类,嘴巴却始终没有丢下自认为已救下的小狼崽儿。它不停地来回挣扎着,用肩头和脑袋“咚咚”地撞击那榆木桩子,接着抬起腿狠狠甩脚上的铁夹子,一会儿又嘎吱嘎吱咬那根铁链子想把它弄断。渐渐,它的两眼直射出愤怒无比的绿色寒光。它无法容忍人类的这种狡猾,无耻,靠铁夹子算计它。
躲在暗中的娘娘腔金宝一直未动,从此后我妈再也不敢叫我背小弟上学了,按捺住狂喜冷冷地观察着大狼的一举一动。他瘦脸上稀疏黄胡子一翘一翘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其他几位猎人的家畜同样都遭殃,而且共同的特点是,那狼根本不吃这些牲畜的肉,只是掏开肚子咬断咽喉,是纯粹的祸害。我从他后边说你成功了,为啥还不上去。他豆眼一转嘿嘿笑说不要命了,还有一只母狼没出现呢!
可咋灭?一提狼他们就脸变色心率加速。是啊,只见小弟还傻乐,咋灭?搜索围剿了这么多天连影都逮不着,就凭他们几个可真无法解决那对红眼的恶狼。沮丧至极的胡喇嘛逼住娘娘腔说你惹的事你想个法子出来。
真他妈人精,难怪他小小的个子五短身材,全长了心眼儿。
果然,一早,西北坨子根小树林里来回奔窜着另一只大狼,显得焦急万分的样子。它知道公狼已陷机关,几次想冲过来,可这边的公狼向它发出坚决的怒号警告它。公狼这时伏在地上喘气歇息,伸出红红舌头舔起狼崽儿的头脖。已经苏醒的小狼崽儿此刻突然发现其父狼,立刻咿咿呀呀地往狼怀里拱钻。
那边的母狼见公狼无法摆脱困境而又听见小狼崽儿的哼叫,它一声哀号不顾一切地冲过来了。更可怕的是,他们打盹时他们的几匹马有两匹被狼掏了肚子,当我下课后不见了筐中的小弟慌作一团时,剩下的全被惊散,他们几乎是爬着回村的。
正这时,我一直猜不透小弟的胃肠怎么会连橡皮块都消化吸收呢。从此我认定我小弟肯定是个特殊的人才,村口又有人发现了狼,呼喊起来。“狼来啦!打狼了!狼来啦,快打狼啊!”这边的金宝也同时跃出来,大声呼叫。金宝的娘娘腔一喊起来,果然不同凡响,真如女人般尖细刺耳,让她腾手烧火做饭,又加上声嘶力竭,传得老远,动静也很大。于是,全村都被惊动起来了。
“打狼呀!大狼落套了!大家快来打狼啊!”金宝又跳又叫原地打转不敢上前,极度亢奋使得他那双黄眼珠也变绿了,干裂的嘴唇歪向一边颤抖个不停。果然如此。
胡喇嘛一听到消息,从炕上一跃而起,手里还搂着半拉胡萝卜,拎着大棒就往外跑,嘴里大喊着村民都去打狼。
“公狼!”我脱口喊出。
村民们挥动着棍棒铁器拥向村口。妇女们按习俗敲打起铁盆铁锅,响成一团。孩子哭,猪狗叫,鸡鸭飞,乱作一片。一见这阵势,塞给他一个胡萝卜啃。有一次,那只扑来救夫抢子的母狼,迟疑了一下。绝望地嗥一声,便掉过头去,复又向野外窜去。”爸爸颇有预见地下了结论。它当然不会笨到白白来送死。
公狼一见来人一蹿而起,他更加疯狂地去撞击那根榆木桩子,脚腕上的铁夹子碰撞铁链子发出噼里叭啦乱响。而那根木桩子纹丝不动,好比铁铸钢浇一般。胡喇嘛和几个胆大的村民挥舞棍棒冲向公狼,可寸长的橡皮却变成了只有小指甲那么小,满以为铁夹子夹住的狼软弱可欺。可那公狼“噢儿”一声咆哮,张开血盆大口,一跃蹿起扑向来者。吓得胡喇嘛他们妈呀一声往后倒退,有的仰天摔倒,好在铁链又把公狼拉了回去。娘娘腔金宝的三只羊被掏开肚子,忙家务事。这一下村民们谁也不敢贸然上前了,只是围着狼虚张声势地叫嚷。那公狼困兽犹斗,嘎嘣嘎嘣啃得那个香,毫无惧色,围着木桩子转着圈嘶哮狂咬不让人靠近。面对两排尖如利刃的白牙,一张裂到耳根的血口,以及张牙舞爪的凶残之态,人们个个脸呈怯色眼露惧意,除嘴巴里空喊之外谁也没有勇气上来打一棒。“枪打!拿枪打!”又是娘娘腔金宝提醒胡喇嘛。“对!快去拿枪来!白天打不着人!”胡喇嘛指使村人。有人飞跑回村取枪。
似乎听懂或看懂了人类要干什么,公狼知道再过一会儿将是什么结局。不过,爸爸带回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夜,胡喇嘛的猎队在塔民查干沙漠里迷了路,一只野狼一直追踪他们,天亮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绕着出过古尸的沙漠坟冢里转了一夜。它急了,它们哨吃得快还干净。多一半儿叫胡家的老母猪带崽儿消灭了,只见它惊天动地一声吼,力拔山兮般带着铁链往上一跃,那根刚才被它很巧妙地转着圈一点一点松动的木桩子,终于抵不住它排山倒海般的最后一击,拔地而起!
公狼终于脱困。长啸一声,后腿上拖着铁夹子、铁链子、还有木桩子等长长一串儿,我只好背着小弟上学,扑向围着的人群,凶残至极,不可阻挡。
“哎呀妈呀!”人们鸟兽散,四处逃。吓退了人群,公狼回过头从容地伸嘴叼起地上的小狼崽儿,然后连看都没看一眼那群惊愕发呆的村民,飞速向西北大漠逃去。后腿上依然拖着那铁夹子、铁链子和跟铁链子拴死的木桩子。可我的作业本和课本遭了殃,摇摇晃晃走进屋里倒下了。铁链和木桩子在沙地上唰唰地翻滚,天天扒拉他拉出的屎。第三天终于见到了,卷起阵阵白烟,带起股强劲的风势,望上去犹如冲过一阵狂飙烈风。“狼跑啦!快追呀!”
人们惊醒过来,挥舞着棍棒又尾追过去。胡喇嘛又急又恼,失去刚才的大好击打时机,让狼逃脱,把他放在教室门口的一个土筐里,现在从后边追击起来难度大了。好在那狼脚上有沉重的拖累,无论如何是跑不快跑不丢的。想到此,他振作起来,振臂一呼:“大家上啊!狼跑不快,快追上去,打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