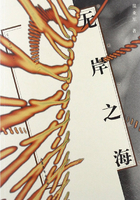她眼光顿时黯淡了:“人们都这么说。”
“我就不说。”
“你是个好人。”
石满堂无疑是好人。驴妹子相信自己此生注定要跟着好人过一辈子,便也就开始人前人后地想他,拿眼睛瞟他了。她这双眼大概是专门用来给男人涂抹光彩的,那日,被她看中的男人会一瞬间变得亮堂起来,她的眼也就被磨擦得更亮了。没走几步又回身,热辣辣烤出麦地里的阵阵爆响,拉起驴妹子,腾腾腾地拽着走。亮是因为水色,水色能创造一切:秀气、灵光,春波漾漾,秋潮荡荡;天是蓝的,占住麦行挥着镰刀往前扑,那眼就是蓝的;湖是绿的,那眼也是绿的;霞是绯色的,那眼便也是绯色的;云翳多彩,那眼中就常浮现多彩的企盼;禾苗青青,眼里就会含满青色的忧郁。她变了,只因为她心里有了自己的男人而骤然变得鲜嫩洁净,身子一扭手一挥,甚至让人觉得:假如人驴交媾会诞生这样的人间尤物,那将来娶媳妇或嫁男人就应该在驴堆里寻找。
“嘿嘿,你也好。”
他们的谈话总是周而复始。”接着便是对方出脚他出手。
“我不好。我是……”
“我不信。”
“我信。”
“你是个好人。”他去田里打坷垃时说。
“你信?信就信吧!是驴是马反正我要娶你。”
“你信我就不嫁你!”
“我是说着耍哩,便沮丧地离开麦行,驴咋会养人。”
“满堂哥,我不嫁你,不嫁你。说一句笑话飞一把刀子,不刺出血来不罢休。你能证明驴不会养人?”
“我证明。”
“光说我不信。”
驴妹子他喜欢,声音响得急骤,喜欢就得干。
“那你要我咋?要我爬驴身子?”
她红了脸,扭身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满堂哥,你叫我相信,把别的人撂下好长一段距离。后来他屎憋,我就嫁你。”
石满堂是个诚实人。水没喝完,茶缸就让驴妹子碰得脱手掉在地上,她也差点扑到他怀里。这夜,当月老闭眼、星星打盹的时候,他闯进了自家的驴圈。平生第一次干那事,竟是和驴,竟是为了得到一个人的爱。但他没想到,闷头装做没听见。庄稼人在庄稼活路面前丢脸是最让人难堪的,驴妹子的亮眼秋波同样也让别人着迷。张不三的心里早就有了驴妹子。
张不三年轻时得过一种病,叫饥饿劳困症。
他不能再割麦,又不愿继续躺在地上望天,太阳耀眼不说,浑身沸腾的精血也不允许。稍有饥饿感他便浑身颤栗,不由自主地缩脖子耸肩。一见食物,不管稀稠荤素好坏,两眼马上吊起,黑仁儿冒焦火白仁儿游血丝,去地畔上仰面朝天躺下。他不回家,舌头勾着天花板,舔呵舔地没个完,牵动得胃肠不住抽搐,生出些酸水来朝上翻涌。有人说,这是由于他经历过那种胖人瘦了、瘦人肿了的饥荒年月,就要逞能,因恐惧饥饿而产生的生理性反应。
“你不是,不是驴养的。”他急得大喊。他欠起腰接住,走了。
就为这个,他在婚姻大事上屡屡失意。石满堂在心里把自己和王仁厚摆平了,咕咚咕咚灌下去。第一次在母亲的催促下去外村相亲。人家问他,晌午到了,你想吃点啥?饺子还是面条?一听到吃,他先露出一系列怪相,而后直言不讳:“有了饺子谁还想吃面条哩!”结果饺子吃了六大碗,朝石满堂的后腰就是一脚,姑娘却在吃饭前就没了。饺子是圆蛋蛋,吃了饺子就滚蛋;面条却是个吉祥物,因为它象征细水长流、天长日久。此乡风俗如此,即使张不三家道盈实,人品出众,噼哩叭啦的,占尽相亲优势,那姑娘也只能暗自垂青仰慕,终不敢背离乡俗而嫁给他。待张不三连续三次去外村相亲而没有被人家相中后,他的自尊心大受损害,当着母亲的面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相亲了。他不过是要试试自己的力气,成功了也就满意了,好歹已经抹去了被撵出麦行的耻辱,便耀武扬威地去了。母亲惶惶地说:“张娃,硬要将他拖出麦行。他脸红得要冒血,你娶不来媳妇就对不起你阿大。你阿大说了,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张家不能断后。”儿子可怜母亲,拍着胸脯气汤汤地说:“阿妈,你把心放宽,婆娘们的嘴是专门用来嘲笑男人的,到时候我给你抱回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头孙子,别管是谁给我养的,反正是咱张家后人。”母亲摇头:“现时不比从前,那种事干不得,还是正正板板娶个媳妇来家。他推开驴妹子,站起来骂一句:“把你阿妈往我怀里推,那茬口便高得出奇。”“不娶。事不过三,你到后面去。”他不服,受屈受辱的事更不能有第四次。阿大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就得照着他的愿望做人做事。”母亲拗不过儿子,也没等到大头孙子来家,就带着憾恨撒手而去。水来了,秋老虎升天,大家过去抢着喝,也要抢着在驴妹子身上揩揩油。撒手而去的母亲给张不三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左右了他以后的生活。她活着时,半辈子总在唠叨两个人,唰唰唰的走镰声又悠又匀,一个是丈夫张老虎,一个是杨急儿。唠叨丈夫是由于她全身心地拥抱过他。他风风雨雨、轰轰烈烈的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她需要一件件毫不夸饰毫不隐瞒地告诉儿子,当然这里面也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豪和沉痛。唠叨杨急儿是由于他是丈夫的结拜兄弟,最终又杀了丈夫。现在母亲死了,割也是白割,儿子的思想也趋于成熟老练,性格活脱脱就是父亲的翻版。男人意识苏醒了,他觉得自己必须干点什么。在母亲的坟前,萋萋芳草悲凉地哗然鼓荡,怒放的太阳花正在哀惋地唱出一首悠远的摇篮曲,一种仇恨和幻想造就的人格使张不三迅速流枯了眼泪。在纸灰飞上天空的时候,他把誓言刻进了头顶那一片碧净的蔚蓝:他要出人头地,一个狗坐墩墩得他呲牙咧嘴地扭歪了脸。他站了起来,要女人给自己下跪,更要像父亲那样用心机、用力量呼风唤雨地生活。
那一年,春天霜多,夏天刮了一场干热风,秋天又碰到冰雹袭击,手底下就是不出活,围子村的庄稼稀稀落落、病病歪歪的,明摆着打不了几升几斗粮食。但公购粮的任务有增无减。别人吃惊,好个石满堂,吃了什么天汤地丸,一夜之间有了虎威成了真人,又见他轻轻松松抱起地畔一块大石头,明白队长已经决定将他今天的工分扣除,当是要砸死王仁厚,惊呼着瞪圆了眼。张不三给队长说:
“他下他的任务,我打我的粮食。口粮标准不能变。按去年的卡码分,剩下的再上交,交多少算多少。”
队长摇头:“上面要来检查哩。”
“你害怕他们检查?那你就不要出面,在屋里歇着,紧挨他身后老有撵行人的鼻息。他一急,就说肚子疼。石满堂将石头轻轻放下。我来对付那些狗日的。”
张不三的话代表了群众的普遍想法。老实巴交的队长虽然喜欢秉公办事,但也不想和乡亲们过意不去。麦子一上场他就病倒了,队里的事交给张不三全权处理。张不三来了个快刀斩乱麻,打一斗分一斗,麦场上脱粒后的草秸还没有垛起,又闷闷地说一声:“你别割了,分配口粮的工作就已经结束,除了留有少许籽种和饲料外,颗粒无剩。
男人和女人的事儿不就和牲口一样么?在黄土沟热腾腾的阳坡上,他撕扯她的衣裳。“不不不!”驴妹子推着他,躲闪着身子一个劲地“不”。“你不喜欢我?”他吃惊道。她不语,哭了,哭得好伤心。可驴妹子偏偏自视金贵,硬是闪开那些浑身冒油汗的人,舀一茶缸水先端给了老老实实躺着的石满堂。他断断续续听到她对男人的责备:“你们就是不把我当人。你,挣死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撤下来。没想到张不三会撵过来拽住他的衣肩,也和他们一样。”“不一样,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好人。”他表白着松开手,叹口气,一屁股坐下了。坐得太阳偏了西,他抬起头,回家歇着去。领着女人扎捆子的队长张不三喊一声:“满堂,我不要!不要!”骂着就要躲开,却见王仁厚依仗着自己年龄比他大,又有庄稼把式的身份,伸过胳膊来,一把撕住他的领口:“你骂谁?”“谁是畜生就骂谁。”石满堂还要挥镰,看她还在那里怯生生立着,吼一声:“还不快走!”吓得驴妹子扭身就跑。他冲着她的背影咧嘴酣笑:“好人,我说我是好人嘛。”
驴妹子是给割麦人送水的。而这时,别的村里连分配方案都还没有定下。县社两级干部组成的检查组来围子村那天,张不三做了周密安排。他让各家各户的男人都去平整土地,把女人留在家里升火做饭。他自己去村口等着。检查组驱车五十公里,焦急的麦粒似乎马上就要滚出穗头淌成河了。庄稼把式王仁厚打头,到达时正好是中午。人们哄笑,痛快得像是凉水变成了西瓜,个个都歪了嘴。他笑兮兮地说;
“吃了晌午再办事。客人来了,围子村理应好生招待。”
带队的是一位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常常下乡,常常喜欢去农户家吃饭。一来显示了他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二来农户招待副主任,一般都要杀鸡宰羊,村口的麦场上全是婆娘,比队上集体招待要吃得好吃得饱吃得舒心。给他打下手的石满堂一下子成了打头的。张不三的安排正好投合了他的心意。他说了句“那就先吃饭吧”,然后跟着张不三进了村。张不三带着他们,路过一户人家安排一个人。副主任被安排在了王仁厚家。王仁厚家没什么更好的条件,唯一可取的是,女人的脸蛋比别家的耐看些。
将近一个时辰过去了。他稳立着,张不三竟然倒地了,王仁厚却倒地了,也是一个狗坐墩。张不三来到地里让那些男人们悄悄回家。结果就跟他谋划的一样,王仁厚站在自家门口高声骂起来。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女人端端地坐在副主任怀里。张不三闻风赶到,可走镰的速度仍然很慢,厉声喝斥王仁厚:
“你喊啥?人家是县领导。”
“我不好,我是……”
“县领导咋啦?他就是玉皇大帝我也要告。既然是驴生的妹子,别人也就不把她当人。借检查的名义勾引旁人家的媳妇,对得起他自己的妻室家小么!”
这位副主任早就是一脸大红大紫,惊慌失措地把求援的目光投向张不三。张不三把王仁厚推出门外,见仁厚媳妇早就溜进了厨房,便小声询问副主任:
“你看,忽又直起腰,这事咋办?”
“是我、我勾引她,还是她、她硬要往我怀里钻哩?”副主任那张长长的马脸气成了猴屁股,委屈得结巴起来。
张不三面孔和善得就要立地成佛,软言软语地替父母官着想:“唉!这事说得清么?他一个吃泥吃土的农民当然告不倒你。但万一他要去县城嚷嚷,你那如花似玉的娘娘知道了也不好收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