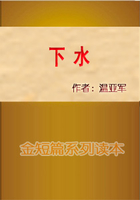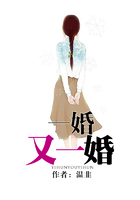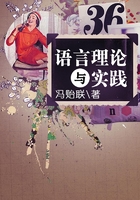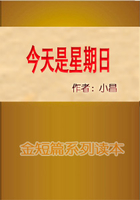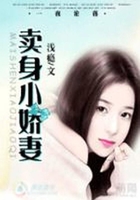19这是为什么
犹如豆荚在暑天里炸开,当整风的“豆荚”一进入盛夏之日,那机诈的“豆粒”便一颗颗圆滚滚地成熟了,并随即不断发出令人心悸的爆裂声……
第一道声音发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了让这一声响得似晴空霹雳,有遏阻流云之势,据说,毛泽东吩咐过好些党内的笔杆子去草拟该报这一天的社论,最后让他觉得满意的还是4月间他已经召见过的王若水写的稿子。他作了某些修改,又冠之以一个十分大众化、又十分赫然醒目的标题:《这是为什么?》--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篇明白如话、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一看就懂的社论里,惟一必须加以注释的是卢郁文其人,因为从表面上,他收到了恐吓信一事,正成了这篇社论论点的缘由。
卢先生是何许人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地主阶级出身,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做了多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半生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实在些,他做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在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里担任秘书长。和谈破裂后,他随代表团的成员一起留了下来。卢先生因收到“恐吓信”而一时风头劲健之时,正做着民革中央委员外,还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在5月25日民革中央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他说即使是在整风运动期间,共产党不应该也决不会对错误的言论放任自流。他还指出,几乎在每一个高级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都有人喋喋不休地提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提及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并不胜任……
在这番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发言之后,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在6月6日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他公开了这封恐吓信。从信的内容看,并没有夹寄上一颗子弹,一根雷管,或是写着“决不轻饶你这条狗命”一类让卢先生毛骨耸然的话,只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给了他敌对的道德评价,诸如“为虎作伥”,诸如“无耻之尤”……
有人以为将此信称作为“恐吓信”是夸大其辞的。在民革中央,在私下,不是一、二个头面人物和中央委员,更以为此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给自己的。“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好似一个浪花在历史的长河里倏然一闪,便没有了戏剧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民主人士被扫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崛起了,俨然成为紧贴在党身上的一件泛出青钢色光泽的坚硬铠甲,仿佛不击穿这件铠甲,阶级敌人就无法向党作出进攻:
卢先生自称,从第一封匿名信公开之后,他在6、7、8三个月间,收到了来自全国16个大中城市的30封匿名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没有气节”、“少了人格”、“不折不扣的奴才”一类咬牙切齿的辱骂外,便是张牙舞爪地恐吓:“不要继续为虎作伥,否则自寻其恶果”、“你的性命难保”、“波匈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共产党不满三年将自取灭亡”
一封盖着石家庄市邮戳的匿名信里有这样一句话:“请不要卑鄙地追究这封信的墨水、纸张,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卢先生据此认为写信的人一定是一个老牌特务。即使这些信没有似公开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往来书信一样被肆意剪裁,可凭着他如此敏锐的政治嗅觉,十有八九,它们都被他犹如挖到金缕玉衣一般兴致勃勃地交出去了,并让公安部门够忙乎一阵……
与此同时,卢先生又自称,他还收到了除西藏外的来自全国各省市的71封慰问信,有的是以工会、学校、合作社的全体名义寄来的,有的是以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慰问,是支持,是鼓励:“如果恐吓者,真要动一动您的一根毫毛,他就要粉身碎骨”,“我们虽然不相识,共同的理想把我们连在一起”,“勇于前进吧,亲爱的同志,随时都有一群青年人在支持你”……
不知他是否像交出匿名信一样也交出了这些慰问信,如果交出了并得到妥善保存的话,它们应该放进博物馆,让后来人在参观一部往往沉重得令心尖发痛的历史时,也能稍稍的幽默一下。
卢先生还发现,自《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出来后,周围的人们对自己的面孔起了显著的变化:
平素相当要好的朋友中间,有的人对他冷淡起来,甚至在背后将他夹在上下牙床之间,唾沫里滚动一阵后,像吐瓜子壳一样吐了出去。相反,有些人平素和他只有一面之交,现在碰到了则格外热情,从那一片崇仰自己的盈盈眼波中,他感觉自己是被一群小行星包围的大行星。乃至对他的老底十分了解的他过去的学生,原来为着他替反动政权帮凶深感憎恶,二十多年来与他压根没有来往,现在也来信问候,言辞之歉疚、温暖,宛如写信人自己是一只迷途知返的羔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于这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有着卢郁文这般良好感觉的,只是凤毛麟角。不久,他被提升为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秘书长。
还在这几天之前的一个炎热的夜晚,当丛维熙从妻子张沪口里听到一份党内文件的内容:“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他已经瞠目结舌了!好似妻子参加了这份文件的草拟,他一下扛起悲愤的“火箭筒”,向她作出一连串的击发: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变成了撞网的大鱼?”
张沪“我自岿然不动”。她正在奶孩子,怀里的孩子显得那么弱小,像只煞是可爱、极易受到伤害的小动物,吮吸态又那么恬静,好似天欲晓未晓之时那沾满晶晶夜露的花萼……一股带乳香的温馨味,撩拨着她的鼻翼,她不由得低下头,在孩子的前额上轻吻了一下。
顿然,一股为人之母的情怀,犹如雨水渗透土壤一样渗进了她的胸间。也许为人之母的情怀与算计生命、摧残生命的“阳谋”比起来,无异于正高唱赞美诗的教堂与红头苍蝇飞舞的公共厕所间的区别;她一下还进不去眼前这个龌龊的现实世界,她一直沉默不语。
最后,她讲话了,还是以一个母亲的善良,来解释眼前这个并非善良的现实世界:
“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当晚,丛维熙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是1957年里他第一个失眠的夜晚。
他想起在中宣部召开的在京青年作家座谈会上,自己这个因出身不好平时寡言少语、且讲话口讷的人,竟当着“红色沙皇”周扬的面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写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言辞之莽撞,以致于一讲完,好友蓝翎便耳语道:
“蔫人出豹子!”
他还想起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阳春三月》,这是根据京郊一个合作社因过分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生活拮据、被迫去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稿子寄给了天津的《新港》杂志,不久就给退了回来,理由是这篇小说存在着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没有以那位编辑冷峻的政治眼光,像掐蒜苗一样坚决掐去这苗头;相反,却以为自己的创作在摆脱流行的理论说教后,这苗头上沾满的是生活之晨的点点露珠。稿子在改名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后,又交给了《长春》杂志,该刊已发排在七月号的头条位置。能抽得下来吗?十有八九来不及了,这新改的题目怕是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道谶语……
天快亮时,他才昏昏沉沉睡去,可枕着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普希金的一则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不过梦境里,那海不是明晰的碧蓝色,而是深不可测的墨黑色;钻进那小口大肚缸里的金鱼,也不是一条,而是摇头摆尾、欢快得好似去踏春、赶集、幽会的一片鳞光闪闪的鱼群……
猛然醒来,他把这一梦境告诉了妻子,张沪似乎这才回到了现实世界里,她不无凄恻地说:
“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丛维熙的梦,便应验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上。
那份感觉,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写来,也显得那般似迷似惘,如泣如诉--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播音员,还在盛赞鸣放的莺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列车上被甩了下来,那时还不像后来中国的好人要习惯将自己当成“坏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还端然端坐在车厢里,只是随身子的猛烈摇晃而惊讶:这列车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转弯?
她有事可径直走去周恩来的办公室。中国威风凛凛的十大元帅,她见了也几乎都能走上前去打声招呼。过去倘若她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什么不解之处,她总去找党,好似孩子有道题目不会做了,总要去问自己的父母。这既出自于她自感与党之间的那种近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系,也出自于她努力追求事实真相的职业品格,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还是《文汇报》伸向中国政治天空的一片雷达天线。
读罢6月8日的社论,她习惯性地拿起了话筒,接话人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她问对方: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
陆定一作了否定的回答。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不会不清楚:
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业已在一年多来阳光朗照、百鸟闹林的中国开始登陆了。但是这并不意味他要误导几个月以前他还颇为心仪的《文汇报》,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从他在“文革”里的磨难经历看,他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高级官员,而不是那类心眼犹如网眼一样密布的政客。何况在这时他也远未料到,在22天之后,《文汇报》及浦熙修本人,竟会被毛泽东由过去几近含在咀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的宝贝,而一下变成蟑螂般地被恶狠狠地踩死在7月1日……
可能的答案是,毕生忠实于党的陆定一,不会发出任何有违于党的声音。虽然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却还未对大鸣大放、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两者之间原本极为排斥的关系,作出冠冕堂皇的决议和解释。
读罢社论,储安平先生则一下明白了这社论的矛头首先是冲着自己“党天下”的发言来的,犹如刀子划过肌肤一般,他明彻而又痛楚地感到,自己在做了几十年的好人之后,一下给混成了个“坏人”。
6月8日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未等章伯钧说什么电话就挂断了。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章伯钧敢去史良面前如是说,当然是两人的私人关系很好,章史两家亦亲密无间。从几件生活小事可见一斑:有一天,史良送来两打雪白的洗脸毛巾。笑眯眯道:“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见后,用宜兴小罐闷好鸡汤叫人送来,她还带话给李健生:“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章诒和更是从孩提时起,对史良的天生丽质、气度与品格,一直羡慕和崇拜得五体投地。可能在她的眼里,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史良,与其说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她更像是个英格丽·褒曼或白杨那样的电影明星。她写道:“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能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
然而,正是当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眼里的“三美”相加的“史大姐”家里,像是有条热线和新华社通着--次日新华社发出通稿,通稿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话,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
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委员活动,已垂垂老矣的李健生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前者的一个女媳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难道李大姐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