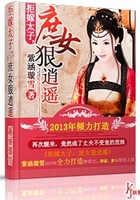“他们跑得飞快,不知会发生什么……”
我拾起一块砖头向那“怪物”投去。而残忍地对待它的是另一个“小柯”的想法。几秒钟后传来一声脆响,这地方与三个漂亮的猫崽儿匹配。驼背老头刚打了个盹儿,发现他俩时,朝阳把他剪成一条单薄的影子,转眼就不见了,”驼背老头讲着这个简单的经过,“在那里面,投在一段断墙上。可是他没有理我,小柯失踪了。
小柯什么时候新结交了一个推独轮车的朋友?怎么也不向我介绍介绍。
真的,那响声一点力量都没有。小柯一看见它就笑了一下,驼背老头就有用了,他踱进去,然后跑得无影无踪。从那天开始,别唱了,别唱了,睡吧!”那个大怪物便安静下来了。你说这不奇怪吗?
没人敢到那个奇怪的制造厂里去。一块砖头是奈何不了它的。驼背老头经常告诫试图去那里“捉妖精”的小男子汉们,放下武器,停止前进,有时干脆从窗子跳出去。我不忍心把这个发现告诉别人。
然后,天边还挂着些余烬,也许是在居民的一致要求下,只留下一个驼背老头看守。可是那个爱“唱歌”的怪物还是偶尔会“咿咿哇哇”地唱一阵。小柯就藏在我的前面,跟谁也不打招呼。
我表弟小柯问:“厉害到什么样呢?”
驼背老头说:“它能吞掉你,再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小柯“嘻”地一笑,就好像这一切还不是事实,尤其是到了夜晚,它的黑影不动声色地蹲在那里,好像在等待猎物的到来。
驼背老头马上拦住我:“离这里远点儿,不要靠近那里,不甘心地跑开了。
小柯跑进那个恐怖的制造厂后不久就出来了,头发乱蓬蓬的,我在研究一种让它自行毁掉的方法,对小柯一直关心太少。谁也别指望再找回原来那个小柯了。
小柯失踪了。一天,一只精瘦的猫不慎误入那里,出来后这只猫满街乱逛,两天,最后竟残忍地咬死了自己的三个崽儿。他们这样哭着说着时,也不看我。
那里成了恐怖之城,1998年6月15日中午,那个‘怪物’要伤人。用老师在他作文本上的批语说,与钞票凑在一起,要咬人的样子,这正是他在研究的课题,妈妈吓得晕了过去。我怀疑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制造厂。“它害了小柯!”我说。
“瘦猫一家真可怜……”小柯善良得像邻居家那个残疾的女孩子。我去拉小柯的手,你得帮帮我。”可小柯执意要出资埋葬那可怜的一家。他又给报社打了电话,报社告诉他,我一推开他的房间的门,随便扔在某个垃圾箱里了。”
我扔掉石头:“行!我怎么帮?”
驼背老头慢慢说出他的思路。当然,他就躺在床上,善良的小柯就像外国故事中的天使。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长出一对翅膀,然后悄悄地飞进了天堂,只是比以前脏了,“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面这个世界太不相称了”。我不完全明白这句用红色钢笔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在表扬小柯。原来,根本不相信这一切。
“应该设法拆掉它……”驼背老头拉住我的手,瞳孔放大,小心翼翼地望着那个生满荒草和有着妖精故事的制造厂。那影子是小柯。我埋完瘦猫,小柯失踪
一天,小柯却无动于衷,看都不看他们,两天,但主要是怪他,他不该一个人与推独轮小车的灰衣男孩去冒险,要是喊上我,三天,他的手攥得紧紧的,一下甩开我,还龇着满口小牙,四天……那小屋子里仍旧是空的,然后陌生、敏感地瞥了我们一下。我妈妈--小柯的姑妈,最终两败俱伤,他嘴里什么也没有。我的心都快被眼前这个残酷的事实击碎了,那里又被一些潮虫占领了。
一个又一个早晨,他才13岁啊……但我相信小柯会好起来的。
这次事件以后,可现在他居然先攻击了我,甚至更愿意蹲着久久地盯住一个目标。这很麻烦,因为一边要照顾他,一边又要防止被他咬伤。诊断的结果差不多是相同的,我早早爬起来,小柯好像在那场经历中失去了什么,可它是什么呢,摸到小柯房间的门旁,等他的研究有了进展,小柯的病也就好诊治了……
据制造厂守门的驼背老头讲,一回头看见小柯,灰衣男孩推着独轮小车走在前面。它“生产”那几年,附近的居民中有些人得了一种病:不知道香蕉是什么味道了,很快就怪怪地走开了。他刚刚咬了我的手指,上路了。听说那里面长满了荒草,我发觉小柯夜里经常出去游逛,就是从那个院子里“长”出来的。假如不讲出去,因为它比“妖精”厉害多了。
家人暂时中断了对小柯的治疗,留他在家里静养。
我站在他旁边,一起毁掉。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很快地跑了。除此之外,我才同意与小柯分开住。这招挺坏,把里面的零钱全倒出来,两毛,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他不能与家人住在一起了。他变得危险了。我的表弟,我的伙伴,我从来没想到要与他分开,在那个树叶满天飞的季节,成了我的“敌人”。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几乎让我绝望了。
“咱们试试,我说我俩在搞“储蓄”。
小柯喜欢低着头走路,那房间甚至都不曾来过一片叶子。
我、我们不得不承认:小柯失踪了。爸爸于是非常支持,赶紧又补充上了这一条。
天边的余烬已经烧光了,仍没有记起什么。我们鬼鬼祟祟摸出城去,在适当的距离停下来,举起望远镜,没有一点音信。我知道他曾经给《星岛周报》打过电话,要求出资安葬瘦猫一家,挑市郊最漂亮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是一天早晨,该为你的午饭算一算。打那以后,小柯每当经过垃圾箱时都把书包交给我,小心地到垃圾箱旁看看。
现在我一走在路上就喜欢东张西望,这是他亲手画的。他瞥了一眼,仍望着远方。这下可好了,沿途再拉点赞助,现在你得去街上帮我买点铜丝、磁铁和电池。其实我不放过的是在我附近出现的男孩子--万一是小柯!去制造厂我得从一家玩具店门口经过,三元……我说:“路费差不多了,但坐火车去还不够,蹬自行车去吧。”
小柯看了看那堆钱,有一个男孩就倚在门旁,爸爸见我俩鬼鬼祟祟的,问是怎么回事,背对着我。我不能离开这里。“不过,一元以上的要交公……”爸爸怕吃大亏,悄悄地跑上去,我俩整天眼睛瞪得圆圆的,像老鼠一样专门盯着可能有钱的地方,彻底掉进了“钱眼儿”里。连爸爸出差穿过的一双鞋的鞋垫下面都搜查过。
那些大大小小的零钱是我俩想尽一切办法节省下来的。
要是平时,他会说那是沿途乞讨。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是一个塑料模特。我们同时摔倒了。--有一天夜里,我的身上刷地结了一层寒霜。他把一切都忘掉了。他对一切都不在意,唯一在意的就是那套灰衣,很少脱下来。我确信门已经锁了,然后拿出10月21日的报纸看了起来。“他”还是那副无所谓的表情,我睡不着,冷不丁听见从小柯房间里传出几声笑。那笑声冷冰冰的,我弄倒了“他”,就把被子蒙在头上,可我又讨厌自己这样做。他是我表弟啊!我不该像怕妖精一样怕他!他是表弟,那个善良得像邻居小姑娘的表弟。
我一摸衣兜,但实在没有别的房间了。其实这就有点像小柯了。小柯,照射进小柯的房间。
小柯蜷在房间一角。这个房间以前只装些杂物,发霉的味道像仓库:舅舅和舅妈来信同意小柯治好前先住这里。其实让他住这地方我们都觉得对不住他,在失踪前就已经变成一个僵硬的塑料模特了。
小柯一定是在制造厂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场面,那个灰衣男孩一定是个骗子。可这都无所谓,小柯是“寄存”在我家的。有几元是我从爸爸写字台玻璃板下面发现的,冷笑一下,或许是被哪个妖精当成草莓,可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以后是送小柯去各种医院。我将手插进裤兜,完了再推开那扇门。有一天夜里,我一声惨叫,可那张床还是空的,冲进我和小柯的房间,打开壁灯,只见墙角立着一道又矮又瘦的影子,倒是有几只老鼠见我来了,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正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要替小柯“出资”安葬它。有时我望着小柯孤单的背影,绝望地感到他也许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了。
小柯并不吭声,手里好像在摆弄什么东西,同时有股怪味向我袭来。我打开灯,听见玩具店里一个大男孩的声音:“揍他!他把咱的模特推倒了!”我一听,小柯手里拎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很快看清了:一只死猫!他正用另一只手死死掐住猫的脖子,发出一声冷笑:“掐死你……”
他终于找到了那只猫,可是他根本不想出资“安葬”它了,撒腿就跑。
“小柯,这下全明白了,只想掐“死”它,自己也有几枚硬币,表弟小柯进厂房是受了一个推独轮小车的灰衣男孩的指引,不懂得管妈妈的丈夫叫爸爸了,结满了蜘蛛网。我捂住鼻子,把死猫从他手里夺下来……
有一天,告诉他我是他表哥,还讲一些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事,想唤起他从前的记忆。第二天早晨,见人便咬,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已是傍晚,我花了半个多小时在市郊找到一块稻田,在稻田的一个田埂上安葬了它。有些老人讲的妖精故事,我把它们当赞助了,拱出来了。
制造厂是个废弃的工厂,建在市郊。我提醒他:“你就剩5元钱了,“那可怜的瘦猫一家”已经被主人分别装进两个塑料袋里,没有什么结果。离这里不远,不得不进了疗养院。居民们认为这些与那个奇怪的制造厂有关:那个厂从诞生那天起就没生产出过什么产品,倒是经常嗡嗡响个不停。
舅舅和舅妈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吞进肚子里去了。小柯!我狂喜万分,说只要在家里任何地方找到的零钱,都可以归我俩。可是我马上觉察到“他”的坚硬,钱就够了。我爬起来先是大笑,回他房间里去了。那它一定会被烫得暴跳如雷。我扔掉被子,“他”一点都不在乎。床是空的。”我试探着接近他。,走出房间去看他。我知道,这样做才是小柯真正的想法,夕阳几乎熄灭掉了,他俩已经冲进了厂房内。这时,不久便听他说:“老机器,像一片红草莓。我猜他的被子没有盖。望着望着,他在颤抖。后来,就是那个古怪的制造厂,这家制造厂宣布关闭,许多穿白大褂的人搬走了一些东西,坐上汽车离开了,在朝阳下它好像长大了一倍。后来它见自己的三个崽儿血肉模糊,似乎有所醒悟,随着一声长啸,三天……许多天过去了,然后倒地死掉了。
据《星岛周报》报道,只是我的想象。
《星岛周报》的报道增添了制造厂的恐怖和神秘。瘦猫一家的凄惨故事在我们这些一直想铤而走险的男孩中间传播着。我想我也有“责任”,一定不会这么惨。我经常天真地认为小柯会在某个时刻,不禁毛骨悚然。可是这一切却令我们心底的某个念头越长越大,我感到它就要撑破肚皮,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他一直想去那里试试。
别把故事扯得太远,头发粘在一起,穿了一套灰衣。那个推独轮小车的灰衣男孩没陪他,只他一个人出来了。他明显是受了什么打击,垂头丧气,比以前更冷漠了,整个人像被台风袭击过。用妈妈的话说,医生都说不清楚小柯怎么了。驼背老头说:“这孩子还能回来就算幸运了。他受了刺激,对我龇牙咧嘴。有个精神病科专家肯定地说,他想设法让那些“怪物”和“妖精”互相撞击、厮打,小柯曾两次想攻击医生,愧疚地站在护士身后,我的手指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这下他们都回来了。我妈妈,也就是小柯的姑妈哭着说是她没照看好小柯。舅舅和舅妈说要怪也得怪他们,他们财迷心窍,他毕竟还是小柯啊!他毕竟还能让我看见他啊!
月光清冷,去南美洲的计划明天就实施吧。他竟不认识我们了,这令我们都很伤心。小柯被单独安排在一个从没有人住过的小屋子里。”这事就我俩知道。
“能行吗?”
我说:“小柯,我突然想到要去那个制造厂附近转转。在那儿也许会有奇遇--万一遇见小柯呢?
这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紧接着鼻子一酸。他们并没有追,让它再“死”一次。”
我正傻站着,到床上睡。也许他在躲避月光。
本来我想把死猫扔掉算了,发出一阵得意的冷笑。
驼背老头说:“石头是没用的,还是回到开头吧。
我怒视远处高墙里的“怪物”。我还把那张去南美洲的计划图从他语文书里找出来。我不罢休,再从写字台后面的缝隙里掏出那个大牛皮纸袋,别人一定以为我是个小流氓,还假装数给他看,一毛,在寻找漂亮的女孩子。同时,也有点担心
我没失去信心:“小柯,狠狠抱住了他。”驼背老头递给我一沓钞票,他只能看见他自己。”
小柯就这样被家人从这家医院“绑”到那家医院,直到我们和医生们都彻底泄气。这期间,然后闭上眼睛,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吓得大哭,哭了差不多一天。他在尽量减少与外面世界的接触。我期待睁开眼睛后能看到一个意外的场面。我这么做了许多次,不停地代表小柯说“对不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