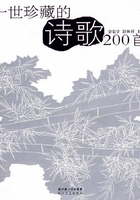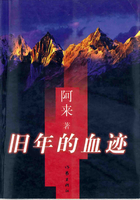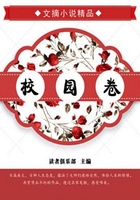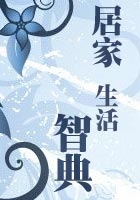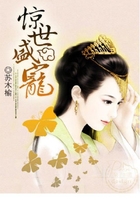永恒与当下
面对凶手高举的凶器,姨父还在心平气和地与他探讨何谓真正的绘画。“不仅我们自己所创作的,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来的每一件作品,都会毁于大火、腐朽于虫蛀或消失于漠视。”“这一切的一切都终将灰飞烟灭。”(208)这正是关于永恒与当下的探讨。沧海桑田,世事轮回,万物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所谓的永恒实际上也囚禁在时间的监牢里。那么追求在画中保留永恒就成为一种妄念。这种近乎残酷的真相摧毁了凶手心中的信念,他丧心病狂地杀掉了姨父。因为既然一切都会毁灭,那么橄榄对自己画艺的骄傲自得就变得愚蠢滑稽。所以说姨父不是死于权力争斗,而是文化理念的冲突。
小说开头以“我是一个死人”的口吻说:“我出生之前已经有着无穷的时间,我死后仍然是无穷无尽的时间!活着的时候我根本不想这些。一直以来,在两团永恒的黑暗之间,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与永恒的时间相类比,人类只是仓促地行走在其间的过客。
爱和遗忘。有没有至死不渝的爱情?时间的巨大侵蚀作用使爱情的永恒受到怀疑。“只要爱人的面容仍铭刻于心,世界就还是你的家。”黑在漂泊的十二年中,发现爱人的面容早已模糊,“惊恐中,我努力地试图记起她,但终究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她,人是会渐渐地忘却那张久未见面的面孔的。”
每一次战争,每一次朝代更迭就意味着画册命运的改变。或者毁于战火,或者为迎合新的君王而被涂改。新的历史和旧的历史就这样在画册中重叠。
传统与变革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非常有尊严的文化,它有自己的文化内质,有独特的趣味和价值,可是也有其偏执之处,它对外来文化无一例外地排斥和抹杀,就是它的狭隘。奥斯曼大师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他宁愿刺瞎自己的双眼,也不愿改变自己的绘画理念。他一生置身画坊,埋首画作,从黑的眼光看过去,他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幽魂”,过着“半圣人、半痴呆的生活”。但帕慕克并没有一味地指责,而是带着敬意写出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的根植感。
谋杀案的发生实则是不同绘画观念的撞击,再加上权力争斗,嫉妒、野心、必然会有死亡发生。姨父坚持衡量一个画家的本领,看他是否发掘出了新的主题及新的绘画技巧。而奥斯曼大师则认为能一丝不苟地模仿前辈大师才是真正的画家。
姨父说服苏丹让他以法兰克画法秘密绘制画册,这在奥斯曼大师看来,不仅是对他权威的挑战,更是对他绘画理念的侮辱,对宗教信仰的亵渎。而那些为了金钱半夜前去姨父处作画的细密画家更是被看成了寡廉鲜耻的叛逆。因此奥斯曼大师并不急于指认凶手,而是要求参观苏丹的宝库,在三天的破案时间里,他陶醉在一本本旷世杰作里流连忘返。实际上他已经抱了玉石俱焚的信念,准备把那几个精心培养了二十五年的背叛者送去酷刑拷问。他用前辈大师毕萨德刺瞎双眼的金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进入永恒的安拉的黑暗,也守住了对绘画理念的执着。
书中引述了诸多例子来印证失明是一个画家的最高境界:谢赫·阿里大师凭借记忆画出了更为辉煌的画册;失去双手和眼睛的杰玛·列丁用口述的方式画出了关于马的画册等。这些带有浓烈的神奇色彩关于失明的故事,最靠近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们以忠贞得近乎决绝的姿态维护着内心的信念,容不得半点玷污。但与此同时,它们在整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格局里又显得固执得不可理喻。这也是一个全球化命题,对于发展比较缓慢的民族或者国家来说,究竟是该坚守传统还是变革创新?是坚守民族文化还是拿来主义?改变传统会不会从此丢失了传统,走上被文化殖民的道路?作家似乎也没有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在小说结尾处,他借着谢库瑞之口说出了对两幅画的梦想:用法兰克画法画一幅肖像,用赫拉特画法画一幅母子图。这代表着东西方艺术融合的最高境界,但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小说结尾处,英格兰国王送给苏丹一个带有精美雕塑的巨钟,苏丹却在一个夜里假装梦游砸毁了它,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巨钟象征着异教徒的力量。回想姨父编制手绘本时,努斯莱特教派对说书人和咖啡馆中人的残杀,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书人的故事亵渎了信仰。还有高雅见到最后一幅画时内心的恐惧,“画中蕴含的深重罪孽我们一辈子都洗刷不掉,他断言,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会下地狱遭受火炼。”(475)传统的力量或者说宗教的力量的强大可见一斑。它们融铸在人们的血液里,对抗着外来的任何变革,维护了完整的传统。也正是它们使得曾经无比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凋萎。
文化冲突
作家曾有过的二十年的绘画经历使他对细密画艺术充满了热爱。“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他不厌其烦地给读者描绘每一幅细密画的图案、色彩、故事,“一位伟大的画家不仅会用自己的经典画作影响我们,最终还会改变我们的心灵视野。”(195)但当一位画家的画作成为世界的美感规则之后,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它因被严格模仿而凋萎。“真正的绘画也正藏在这无人能见,也无人能表现的痛苦之中,它就在那些最初人人都会说坏的,没画好的,没有信仰的图画里。一位真正的细密画家明白他必须达到那个境界,但与此同时,他也害怕到了那个境地后的孤独。”(201)“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69)“绘画是思想的寂静,视觉的音乐。”(71)“这些图画美得让人误认为它们是自己遗忘的记忆,望着它们,就如同阅读文字一样,你会听见它们对你的低语。”(253)这些燃烧着激情的语言背后是一颗对故乡对绘画艺术诚挚的热爱之心。他在绚烂的文字中完成了对故乡,对故乡曾经辉煌的艺术的礼赞。但同时,这礼赞里不无忧郁,因为这些是已经濒临消逝的文明,是永远也不能重现的辉煌。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些极具民族色彩的文化也因其竞争力不足而日渐衰落。这使我想到莱昂·达马斯(leondamas)的诗《出卖》(solde):“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可笑/在他们中间/我像个同谋/像一个恶棍/跟他们一样的刽子手/我的双手现出可怕的红色/流淌着来自他们的/文--明。”(转引自《后殖民批评·导言》,[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杨乃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59-60页)
在后殖民批评话语里,文化交流的结果常常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鲸吞或蚕食。在细密画和法兰克风格的绘画争斗中,虽然主张用法兰克风格绘画的姨父惨遭杀害,但凶手橄榄内心的挣扎和他画在最后一张画中的自己肖像都已表明,法兰克风格的绘画将成为一种必然。细密画对宫廷或者说苏丹的依赖性也决定了其行之不远。小说中,奥斯曼大师去世后,鹳鸟升任画坊总监,继任苏丹是一个对艺术毫不感兴趣的人。于是绘画艺术“如一朵灿烂的红玫瑰般凋萎了。”“就像入夜后家家户户关起房门,城市陷入夜幕一样,绘画也已无人理会。人们无情地遗忘了,曾经,我们透过截然不同的眼光看过世界。”(499)姨父以生命为代价编辑的画册被拆散进不同的书里,细密画家们忙于绘制地毯、布匹、帐篷的装饰图案以维持生计。黑“始终沉浸于忧愁当中”,偶尔欣赏画册,“仿佛停驻在一个早已尘封在记忆中的甜美秘密。”
橄榄一直在苦苦追问:我是怎样一个画家?什么样的画家是优秀的画家?小说通过他来关注整个细密画家的命运,进而关注细密画艺术的存在状况和命运。和其他细密画家相比,文化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时代和环境的局限注定了他只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牺牲品。为了维护姨父和他们的手绘本而杀掉高雅,震惊于姨父离经叛道的理论而杀掉了姨父。他很想超越自我,却又很难摆脱二十五年来传统留在他身上的深刻烙印。所以他始终在矛盾中挣扎,一方面,他抗拒姨父的绘画理念,同时,在实践中又接受了这种理念。两种文化或者说两种绘画理念就像两股烈火此起彼伏地烧灼着他的神经。与其说哈桑杀了他,不如说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烈火焚毁了他。
对《我的名字叫红》来说,谋杀和爱情故事不过是一件好看的外衣,它提醒读者激情地阅读下去,对人性的探索和文化冲突的思考才是作品的坚硬内核。
故事起于谋杀,止于真相大白,黑与谢库瑞的爱情纠葛也随之功德圆满。一场谋杀案改变了诸多人物的命运,也凸现出文化冲突的尖锐。同时,文学与生活中的主要主题:爱、恐惧、嫉妒、忏悔等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这使得这部小说色彩斑斓,绵实丰赡,精巧中盘根错节,焕发出奇幻的美。
三、穿着情色外衣的人性拷问:解读《洛丽塔》
一个敏感的四十岁男人疯狂地爱上十三岁的美丽少女。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尚的职业,相貌英俊,言谈不俗,因为爱上她而走上乱伦、杀人的不归路。而她也因此小小年龄就在社会上流浪漂泊,饱经忧患。
——这就是备受争议的《洛丽塔》。它的作者是著名的俄国流亡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品写于一九五四年,先后遭到四家出版社拒绝,甚至有出版商说,要是印出来,我们都要去坐牢了。好不容易出版后,也是屡遭禁毁,命运一波三折。
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洛丽塔》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目为情色淫秽的,有视为心理分析的,有看作文化政治的等。人们震惊于作家大胆淋漓的性爱描写,有陶醉于作品诗意感伤的叙述节奏,有惑于情节设置的丝丝入扣……作为一本传世奇书,它给读者展开了一个极为辽阔的诠释空间,几十年来,人们不知疲倦地对它津津乐道。
虽然纳博科夫一再说:“风格和结构是一本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但是《洛丽塔》备受争议的阅读史还是让人不得不涉足它的主题和思想,尽管很可能南辕北辙。本文认为,解读《洛丽塔》的关键钥匙在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身上,他曾深陷欲望的泥潭,也用忏悔使洛丽塔永生。这似乎昭示了我们,要想战胜人性弱点,在渺茫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里体现人的价值,其唯一途径是爱和艺术。这使作品跳出了情色外壳,跻身一流小说的行列。
在欲望的阴影中行走
自荷马史诗始,旅程便成为一种原型,奥德赛在命运的海洋上完成流浪的宿命,唐吉柯德在幻想的大地上遭遇词与物的分裂,而亨伯特和洛丽塔则是在一辆破旧的汽车上深入乱伦的深渊。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穿越了美国大半国土,行程两万七千英里。他们的行走更像是一场逃亡。因为浩渺的空间中,亨伯特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安顿他的小仙女和他可怜的爱情。不论行走到何处,他都处在现实中,面对陌生人恶毒的眼光,会有人对他的小仙女虎视眈眈,他只能假借父女之名偷偷摸摸满足欲望。与“灵”相比,“肉”始终处在僭越的地位。
亨伯特是恶魔吗?他对洛丽塔是欲望还是爱情?这是理解《洛丽塔》的一把关键钥匙。如果我们先入为主,第一眼就把他视为罪犯、疯狂的恶魔、性变态者或者精神病人,那这本书就没法儿读下去了,更无法深入到这本小说的精髓。
生活中的亨伯特相貌英俊,学识渊博,讲授欧洲文学,出版学术专著,是众多女子心目中的理想情人。而在他隐秘的内心,黑暗的深处,他痴迷那些未成年少女,“对每一个过路的性感少女的顽固欲望又把我搞得憔悴不堪。”这使他成为一个双面人,儒雅冷峻只是他的外表,而肮脏淫乱则是他的内心。他就像是一个被魔鬼纠缠的天使,被往事、欲望和现实疯狂折磨。
亨伯特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忧郁痴情的人,他所具有的人性弱点在很多人身上同样存在。他原本以为,遇见洛丽塔,是上天的恩赐,是他又一次燃起生命之火的希望,他飞蛾扑火一样跳进这一场注定没有希望的爱情中,用他的全部----名声、地位、金钱、灵魂,来爱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却不料,这只是上天对他的责罚,他被这场爱弄得一无所有,遍体鳞伤。而洛丽塔也因他而毁掉了一生的幸福。他们的世界同时在欲望中沦陷。
他就是人类的镜像,明知自己的行为有违伦理,仍然一意孤行,任由自己在欲望的泥淖中挣扎。他有机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慈爱的继父,可他却放弃理智,任由自己在欲望的泥淖中挣扎。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性的软弱、愚蠢、贪婪和不知节制。
亨伯特的生活早在十三岁就已支离破碎,他十三岁时曾有过一段心醉神迷的爱情,初恋情人安娜贝尔的早夭,使那个阳光灿烂的夏天成为他永远的创痛,他一再说“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他深深陷在那个夏天的创伤里无力自拔,在爱的悲悼中度过了晦暗的青年时期。想要用婚姻拯救自己,却又遭遇平庸妻子的背叛。失败的婚姻又加重了他对生活的绝望。他因此患上严重的忧郁症,并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从事学术,结果约定的那家突然遭遇火灾,他被安排在夏洛特·黑兹家里。但他并没有想要留下来,只是出于礼貌前去看看,直到见到十二岁的洛丽塔——那个他命运中的精灵。
记忆和现实在那一刻重叠,安娜贝尔在洛丽塔身上复活。如果说一直有一股潜藏的暗火在他血管里奔涌,那遇见洛丽塔就“呼啦”一声燃成了燎原大火。她是他的小仙女,是上天为了弥补他夭折的初恋而送给他的丰厚的馈赠。为了继续接近并拥有这个小仙女,他愚蠢地选择了与她的母亲夏洛特·黑兹结婚,这样的婚姻注定不会带来幸福,因为他每天睡在多情的黑兹太太的身边,心心念念的仍是顽皮淘气的小洛丽塔。亨伯特变成了可怜的偷窥者和十多岁的痴情少年。他观察洛丽塔的一举一动并把他的感受写进了日记,而正是这本燃烧着深情的日记本把黑兹太太送进了地域之门。
有一天,黑兹太太撬开了他的抽屉,看到了他写给洛丽塔的深情款款的日记,这使她几乎崩溃,她愤激地宣布离开,并在外出寄信的途中遭遇了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