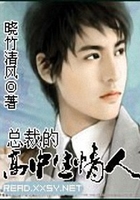吕全点头:“怪不得他见到那朵墨菊时吓得要死,原来杀害墨菊的就是他本人。”吕明阳道:“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是他杀的墨菊,为何又被别人杀死呢?墨菊本没有亲戚,谁会为她报仇呢?本来我已想到了一个人。”
他翻过第四张纸片,上面出现的是谈古的名字。
吕明阳道:“这个人家中有一盆墨菊,想来那日庙门上的那朵花也出自他家,以这个人的风度,极有可能以前和墨菊相熟相恋,他知道墨菊并没有与人私奔,多半便是死于李宵之手,于是便想为墨菊报仇,可为什么要用老鼠来杀人呢?直接用刀子不是更痛快?况且李宵尸体里那条毒蛇如何解释?又是如何钻进李宵胃里的?而放蛇的人又是谁呢?”
还有最后一张纸片,吕全翻过来看了一眼,见上面写的是吴玉年的名字,他又是一怔,道:“吴举人也有嫌疑?”吕明阳道:“也有。他追求李兰兰,却被李宵拒绝,他怀恨在心,说不定也会狠下杀手,而且他在江州住过几年,很可能也见过墨菊,爱上了她。既然得不到真墨菊,那么想找一个模样酷似的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是他做的,前日为何又告诉我李宵的真实情况,好让我们去江州城寻找线索呢?这不是将他自己暴露出来了么?”
种种疑问,围绕在吕明阳心头,他不住的来回走动着,想要找出一个最适合的答案,吕全不再打扰他,退了出去,吕明阳来到窗前,负手而立,嘴里喃喃的道:“一定有什么地方疏漏了,可会是哪里呢?”
突然他眼神一亮,马上叫来吕全,吩咐前往张凤如的家。吕全不解,吕明阳一边走一边道:“李宵死时,可否也是这个时辰?”吕全看看天色,点点头。
吕明阳笑道:“这就对了,此时我们不妨也做一下李宵,去那屋子里睡一觉。”吕全大惊,道:“那屋子是凶屋,大人若去,只恐……”吕明阳淡淡的道:“只恐我也学了李宵?你放心吧,老鼠都已赶尽杀绝,不会有事。”
听得大人到来,张凤如鞋也没穿好就出来迎接,吕明阳摆摆手,叫他依然回屋睡觉,自己与吕全来到那屋子前。这里依旧有人守着,但只是一个人,另一个衙役正在睡觉,吕明阳吩咐吕全在外面等着,自己一个人进了屋子。他点燃了灯,在屋子里又仔细的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他觉得有些疲倦,就在床头坐了下来。
那张床吱的响了一下,吕明阳突然心头一闪,暗道:这屋子里所有地方都看过了,只有这张躺着死人的床,因为被老鼠弄得狼籍一片,没有好好看过。他立时来了精神,将灯拿近床边,仔细的从床头看到床尾,又在床里面的墙壁上摸了半天。
这一次他的眼睛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用手在墙壁上敲了敲,突然面露喜色,正要退身起来,突然觉得脖子里仿佛落下了一些什么东西,他用手一摸,是一些粉末,指头搓了搓,有一种滑腻的感觉,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从床铺顶上落下的。此时天色已凉,床顶已将蚊帐撤去,只留有轻纱做的顶子。他举灯细看,却是什么也没有,用手摇了摇床,便又有一些粉末落下来,可能是太多时候没人住而留下的灰尘吧。
吕明阳看完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开门出来,吩咐衙役继续看守,自己带了吕全回衙。
等到他们出得张宅,大街上已是暗黑一片,时候已近后夜。天凉如水,夜风渐寒,让人思绪一清。吕明阳快步走着,似已扫去了近日来的愁云,成竹在胸的样子。吕全在后面跟着,虽没见吕明阳说话,但也知道案情已有了进展,不由得也替他高兴。
一阵夜风吹来,将吕明阳的帽子吹得歪了歪,他抬手去正冠,突然有一抹微光从手指间闪过。他心头一怔,忙将手指凑近眼前,果然有微光,这是哪里来的呢?
那手指间依然有滑腻的感觉,他记起来了,是方才落下的粉末在他手指间发光。可这是什么东西呢?吕全见他不走了,看着手指发怔,忙上前来,也见到他手指发光,咦了一声。吕明阳将手指凑近他的脸,道:“你看这是什么?”吕全用鼻子闻了闻,又用手指沾了沾,道:“这好像是萤石粉。”吕明阳道:“萤石粉?是不是在暗处会发光的萤石粉?”吕全道:“是呀。”
吕明阳喃喃的道:“他屋子里如何会有这种东西?”他猛然转身,道:“回去。”
这次他没惊动张凤如,一个人又悄悄来到了那屋子里,吹灭了灯火,躺在床上。果然,灯光一熄灭,床顶部位便发出了轻微的光芒,与他手指所发的光是一样的,都极微弱,但在黑暗中看来却是很清楚。那光芒隐隐约约的像是映射出什么东西,却看不明白。
吕明阳心中像是有两扇门一下子敞开了,他从床上跃起,急匆匆奔回县衙。他吩咐吕全天亮后马上去李应龙家,如此这般。吕全点头。吕明阳又叫过周虎,让他速去找那个天竺人,请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写了几封短信,让人天明后一一送去。
做完了这些,吕明阳脑子里又将明天所能遇到的情况想了一遍,觉得没有一丝漏洞了,才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抬眼看了看那已将发白的夜空,心里很有一点苦楚,他知道,明天将会是一个悲惨的日子,虽然他并不想让这个日子变成这样,但事实如此,他必须要尊重它。
“人,竟是如此可怕。”他在心里叹息着。
五
月夜下高朋满座
酒席前点破机关
这个夜晚终于来了,天空一望如洗,没有一丝云彩,那轮并不十分圆满的明月将地面上照得通亮,地上纤尘不起,空气中带着桂花的香气,极为凉爽,正是一个品酒赏月的好天气。
现在张凤如家中就有人品酒赏月,但他们的心情却是一一不同。
连主带客总共是五人,吕明阳坐了主位,张凤如在客位相陪,然后依次是吴玉年,谈古,明尘,陈龙垂手立在吕明阳身后,几位衙役代替了仆人,来往斟酒布菜,这使得今晚的气氛有点不安。
吕明阳举杯在手,说了几句客套话,大家一饮而尽。但看各人的神情,仿佛都各有心事。
张凤如干咳了一声,道:“大人光临寒舍,实在是不胜荣宠,使得寒舍蓬……”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见吕明阳突然脸色一沉,将酒杯在桌子上重重一放,哼了一声:“客气话就免了,今晚下官请各位到这里的意思,可能各位也都知道。就是为了李应龙一案,不,应当说是李宵一案。”
他这句话一出口,桌子上的人脸色都变了,张凤如目瞪口呆,吴玉年有点摸不着头脑,谈古嘴角微微颤动,而明尘则双手合什,闭上了眼睛。
吕明阳环视一下在座的众人,缓缓的说:“这李应龙原是江州富户李宵,因十几年前的一场大火,避居在此,原本想要逃过仇人的追杀,但是重阳那天夜里,他仍旧没有躲过一劫,死在前面的那间屋子里。而你们几位,当时都是在座的。”
吴玉年急道:“这么说大人是怀疑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了?”吕明阳摇头,道:“也不尽然,比如吴举人你……”吴玉年松了口气:“我想大人明辨是非,绝不会冤枉好人。”吕明阳眼睛一立:“你也是被怀疑的人。”吴玉年张口结舌,道:“我……我没杀人呀……”吕明阳道:“你与李家小姐暗通款曲,李宵不允,你便杀了他,这也是有可能的。”吴玉年急得站了起来:“大人可不要信口开河,小人久读圣贤书,绝做不出这般事来。”
吕明阳冷冷看了他一眼:“那你就老老实实坐着,休要多口。”吴玉年如霜打的茄子缩在椅子上。吕明阳沉默了一下,缓缓道:“这桩案子,光怪陆离,颇多曲折,其中有些地方我也不太明了,只有让凶手自己来拔云见日了。”
他的目光四下一转,最后停在谈古脸上,道:“谈先生,你想说还是不想说?”谈古冷笑一声:“说什么?”吕明阳道:“说你是如何用老鼠杀死李宵的。”
这一句话出口,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张凤如道:“不可能吧,谈先生性情高洁,风骨雅润,怎么会用老鼠杀人?”吕明阳道:“说实话,我也是不信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谁也改变不了。来人!”
有个衙役点点头,轻轻搬来了一个木箱子,放在众人面前,众人见这箱子用一把大锁锁着,看不到里面,不知是何物。吕明阳道:“久闻谈先生乃当代乐坛圣手,今日可否再将重阳那天所奏的几支曲子演奏一遍?我在信中请先生带琴来,先生怕不会忘记吧。”
谈古从背后取过瑶琴,平放桌面,眼睛看了看众人,道:“这有何难。”说着他十指一抚,一股流美孤高的琴声便从弦间淌了出来。这是一曲《阳春白雪》,众人凝神细听,只觉得曲子峭拔傲立,正如一位绝世高人,遗世独立,飘飘然有羽化登仙之感。
一曲完毕,大家听得如醉如痴,但又觉得奇怪,为什么吕明阳指明他是凶手,却还要他奏乐?吕明阳轻轻拍了两下手,道:“好曲,敢问重阳那天,先生还弹了什么曲子?”谈古看着他,却不回答。张凤如想了想,道:“先生弹了四支曲子,分别是雁落平沙……”吕明阳打断了他:“我问的是李宵睡下之后,他弹了什么曲子?”张凤如道:“好像是一曲《铁马冰河》”吕明阳盯着谈古的脸,道:“好,下官就想听这首。”
谈古没有动,他的手指如同僵了一般,眼睛盯着琴弦,脸上肌肉不住轻颤,使得他那一部美髯如波涛般起伏不定。
吕明阳眼睛中发出了光,道:“这首曲子谈先生想必弹得极好吧。”谈古突然哈哈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很惨,将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谈古笑完,咬着牙道:“好,我弹。”
他双手一起,琴弦上便发出一阵金铁交击之声,如银瓶乍破,似铁骑突出,状如雷霆密雨,踏碎了万里冰河,众人仿佛已不是在花前月下,而是置身于大漠寒风之中,处地于千军万马之内,耳朵里再无别的声响,只有这股冲击心灵的杀伐之音。
可是就随着这一阵急雨般的琴声,那箱子里突然也发出了一声清脆的金石之音,谈古的琴声越急,箱子里的声响越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箱子里随琴而舞。谈古弹到情动处,铮的一响,七弦尽断。只听裂帛一声,场中立时静了下来。而那箱子里的声音也随之沉寂。
吕明阳吩咐衙役将箱子打开,箱盖一掀,大家抬眼向里一看,几乎要吓个跟头。里面正有六只大老鼠仰头盯着众人,那一对对小眼睛血红如同恶鬼,正要择人而噬。
谈古并没有向里看,他仿佛知道里面是什么,目光中只露出一丝不屑之色。吕明阳道:“这箱子里就是那些吃人的老鼠,而在箱子里,我垂了一些响簧,只要一碰,就会发出声响。大家方才都听到了,谈先生以前弹那曲阳春时,箱子里并没有动静,而为何这曲铁马一出,箱子里老鼠便疯狂大动,恐怕只有谈先生可以告之一二了。”谈古道:“那有什么,老鼠被琴声所惊,故此慌张而已。”
吕明阳冷笑:“只怕不那么简单吧,这些老鼠只吃人肉,绝非野生,而会养这些吃人老鼠的,也就只有谈先生。”谈古也冷笑道:“强词夺理,你有何证据?”吕明阳道:“若无证据,你怎么会心服?你那屋中香气弥漫,别人道你是焚香抚琴,可我却知道,便有十个人一起抚琴,也用不着点那么多香。你每天洗澡,还把屋子弄成香房似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让人嗅不到你养老鼠的味道。而且那些香中掺有艾草,烧起来后能使人头晕,其目的就是不让苍蝇之类的飞进房中,引人怀疑。重阳那天,你将老鼠装入纸盒,连同瑶琴一起放入琴箱,带来张府。然后借口沐浴更衣,在无人发觉之时,将老鼠连盒子放进了李宵就寝的床下。”说着他取出一张烂纸放在桌上,正是那被咬破的纸盒。
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谈古面无表情,道:“一派胡言,敢问天下,会有人在家里养老鼠么?”吕明阳还没回答,只听一个声音道:“也许在座的人里就有一个。”随着话音,吕全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两名衙役,手里抬着一个大木箱,那箱子周围尽是斑斑血迹。谈古闭上了眼睛。
吕全正是奉了吕明阳之命,在谈古出门赴宴后,带人到了他家里,一查之下,果然发现有一个地穴,里面腥骚恶臭,令人掩鼻,正中放着这个大木箱子,从里到外尽是血迹。另外吕全还从地穴里发现了几个纸盒子,与吕明阳在那屋子里发现的质地相同。吕全说着递上一个纸盒,吕明阳吩咐衙役取过那破烂的纸盒,对照之下,果然是同一种板纸。
吕明阳一笑,道:“谈先生,现在还有什么说的?”谈古道:“无话可说。”吕明阳厉声喝道:“谈古,你外表儒雅,可心中却是如此恶毒,竟想得出此等骇人听闻的法子来杀人,就算他与你有杀父夺妻之仇,也用不着这般报复吧。”
谈古突然扬声大笑:“我恶毒?对,对,我是恶毒,但对付李宵这种猪狗不如之辈,这种法子算是便宜了他。”吕明阳喝道:“你这般恨他,就因为他杀了墨菊?”谈古也大叫道:“对,就因为……”他突然住了口,盯着吕明阳:“你如何知道?”吕明阳一笑:“你先不要管我如何知道,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的故事,尤其是你与墨菊的故事。”谈古盯着吕明阳,眼睛中不知是愤恨还是忧伤,陈龙怕他暴起伤人,手握刀柄,站在他身后,看紧了他。
过了片刻,谈古突然长叹了一声,举头看着遥远的夜空,目光仿佛比那漆黑的天宇更加深远。他的声音像是从地底发出的一般,讲出了一段凄惨悲凉而又哀怨缠绵的往事。
早在十一年前,谈古已是一位东南知名的琴师,名字叫鲁鱼,他云游四方,这一年来到了江州,听得人说万花楼里有一位墨菊小姐,琴画诗书,极为精通,他便去见了一次墨菊,谁知二人一见之下,都是情愫暗生,谈古的风流气质,给墨菊留下极深的印象,芳心暗许之下,对他也极为重看。
当时谈古虽然名动四方,但袋里却没有多少银子,只因他一向视钱财如粪土,所以没想到这种阿堵物在风月场中竟是如此重要,他立志为墨菊小姐赎身,等到他凑齐了银子时,再到万花楼中,却知道两个月前墨菊早被人重金赎走了。这个人便是李宵。
谈古虽然痴情,但却是一个明理的君子,他认为如果墨菊从良之后如果幸福的话,他就会永远在江州消失,再也不来打扰她。但他还是忍不住在李宵宅边的一个客栈中住了下来,每天在楼上凭栏而望,希望再看墨菊一眼。可没过几天,他终于看到了墨菊,而墨菊也看到了他,她突然流下泪来。又过了两天,墨菊竟偷偷跑到他屋子里,对他说了一切。原来她过的并不幸福。李宵娶她只因为她与以前的大娘子生得很像而已,而且这个人有点变态,总喜欢让她做一些不可启口的事寻求刺激,她已经受不了了。
自从那一天之后,墨菊就再也没出过门,因为她来的时候被一个管家看到了,那个人就是胡七,他对李宵说了,李宵就将墨菊关进了柴房,谈古在客栈楼上看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对李宵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从这一天,他便不再出门,而是在夜深时向李宅中那所柴房的方向挖了一条地道。由于客栈本就靠着李宅,所以没过三天,他就将地道挖到了柴房地下。
而那天,刚好是重阳节。
说到了这里,谈古的脸色突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变化,那是一种可以将人冷到骨头里的恐惧,他的声音都颤抖起来:“我将地道挖到了那里,从地下钻了出来,满以为能见到墨菊,但是我见到的竟是……竟是……老鼠吃人的惨剧。”
几十只大老鼠,围着墨菊那曾经迷倒众生的躯体,在疯狂撕咬着。墨菊浑身是血,但奇异的是,那些可怕的老鼠竟没有去咬墨菊的脸,那张脸依旧美丽如昔。
“可能上天有眼,让我再见一眼美丽的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