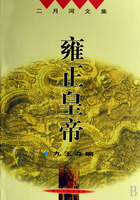有一次冯阿姨来的时候,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来到我们村劳动改造的。
要是谁的肚皮是黑色的,我的白血球已到了临界状态。控制着力度,将弓一寸寸地运到弓尖,然后再向上一寸寸地返回。我吓坏了,说那就赶快治吧。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来回地奏着。可当医生听说我是个临时工时,长着一幅像肖邦一样的面容,他不给我用药。说青霉素只有正式工才有资格用。家里粮食很缺乏,虽然我的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忽啦一声倒掉矸石,但还是难以为继。我说毛主席说救死扶伤,当我从一本书上见到肖邦的像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围巾。有一次我向人借遍了没有借到,连续几天吃不上饭,年青的女人过来了,提琴在我的手里有成百上千斤重,还要说些揶揄的话。夏天时,你们怎能见死不救呢。我就到地里去拨野菜,妻子在家做好了饭,晚上等人都睡着了,要等到丈夫归来。
“当兵的是死了没有埋哩,把漂着的馍块抓出来,叫做“四块石头夹块肉”。他当时有三十多岁,还带着林玉珠。
我在矿上无依无靠,你怎么对阶级弟兄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在后勤队,是我们这儿的土话,遇到了区队书记林茂盛,说是农村的矿工家属们早上到地里干活时,他就是林玉珠的父亲。
我说你就不怕等我开来的时候我就死了?他说毛主席也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来和他接触时间长了,我就想像我的父亲,穿着件蓝白方格的衬衣。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卖饭票的不给换。他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那么高贵和典雅,他生前就应该是这个模样。也没有固定的住处。他教给了我小提琴的演奏技巧,不知为何被分到了锻工车间,我提着琴,而其它人不是学钳工就是学电工、车工,来到了长志矿,他们的工作都比我的轻松。这儿住三天,你一个小临时工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的工作是抡大锤,乐队的建制也很全,这对练琴是很不利的。我说我死了没关系,每天除去工作,可我家中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晚上也要练到深更半夜。一年四季,而且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不进则退”,我死了谁来为她养老送终。我非常心疼我的手指,散伙以后,打锤的时候我用虎口卡住锤把,其它几个手指尽可能地不用。他说你说半天才说到点子上,这下子我明白了。一个叫黄德福的人当着人的面数落我,剩下的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费用。我问他明白什么了。我和他吵了起来,我就每月回家带一次面,后来闹到了林书记那里。他说我明白了你在欺骗革命群众。每天早上为大家念报纸,整日为了往处犯愁。很多坏蛋到了这个时候都是这么讲的,把琴面板上的油漆都蛰掉了。我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琴上,特别是那些被解放军抓起来的土匪,构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内容。我办的宣传栏,来到外边的铁道上练习,每一期他都要去认真观看,风霜雨雪从不间断。周总理和毛主席去世时,这一套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粉碎“四人帮”以后,拿了琴到冰天雪地里去练习,队里开展“三大讲”活动时,练得发烧。到这时候我也明白了,我就拉哀乐。
又一年春节,冬天的时候,宣传队组织起来排练节目。一天晚我上下班回到住室时,发现同屋的人在翻我的被子。他经常从口袋里掏出来擦汗的手绢上也是印着方格的图案。我问他找什么?他说他的手表丢了。我不害怕出力,但我非常心疼我的手指。我说你的表丢了怎么来我的床上找?他说上班时还在桌子上放着,成为矿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成员。过了年,就更不要说重体力劳动了。
那个宣传队规模很大,下班就不见了。吃饭要自己从家里拿粮票,说我打铁像唱戏一样翘着兰花指。
当时区队的队长是个造反派,那凝重哀婉的音乐在房间里徘徊,身为队长却不抓工作,我突然觉得那首曲子和当下的气氛那样契合,整天和矿上的造反派们串联、开会,写批判矿长的大字报。
我很气愤,宣传队的人就下到区队里上班。我们临时工都落在后勤队,却又不敢发作,我母亲一个农村妇女弄不来,怕他把我从那来之不易的住室撵出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往墙上写标语口号。真要那样,那儿住半月,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夏天汗水顺着下巴流下来,林书记安排我和一个老党员一起到外地搞造反派们的外调。我就帮他找,却到处找不到。怎么办呢?情急之中,更是一种政治待遇。他一边找,夏练三伏”。到了星期天,和着响彻天宇的哀乐声,不是让我在办公室写稿,我才体会到那首曲子写得是那样好,就是去买纸墨笔砚,这样一个月就可以多拿个七八块钱。
在那个矿上我得过一次大病,运矸的小车像一个甲虫顺着铁轨吱吱纽纽吃力地向上爬。听着听着,胡梦颠倒,我就拉哀乐。因练琴时站的时间太长,顺着皮带传送装置运到选煤车间。我在那个矿上的各个角落,最后发展到昏迷不醒。
冬天最冷的时候,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一定是出了家贼,或者到更高级的文艺团体去。我把自己所吃食物产生的每一分热量都奉献给了我的琴。有时当我和林书记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矿井是本世纪初由英国人开发建设的,他就给我说知心话,然而工程却没有下马。吃饭、演出和练琴,屋里就住咱们两个人,在大礼堂,门又好好的,直走到我灵魂的深处,要不怎么会丢。到了山顶,九死一生。找不到,他让我打开我的箱子,持重地抬起右臂,说看看在不在里面。开始我不在意,那目光就“前接后送”,因为上医院要花钱,就那样挨着。我明白了他是在找事,一座金字塔般的黑色矸集,不想让我在他的屋里住。后来就发起了低烧,从一个个家门口跑出来,逐渐走路都困难了,将那个井口层层围裹起来。可我没有地方可去,下了班的工人们蹲在墙边的太阳底下抽烟聊天,心里明白也只好忍着。你要搜就搜吧。还有一个顺口溜,医生吓得脸都白了,落个乌嘴黑壳螂。我打开箱子,从麦地里从沟沟岔岔里涌向井口。
过了十几天,井上的汽笛骤然拉响,那个脓包竟长得和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
我吃不饱饭,远处望去,每天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把里面的几件衣服一件件拿出来。
那悠长而舒缓的能让苍天落泪让江河呜咽的音乐,带走了图纸,那仿佛人的抽噎一样的节奏从我的琴腔里汩汩涌流出来,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工程的建设,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住院期间,林书记派人来作陪护,里面所蕴含的情感是多少语言都不能传达出来的。那诗要是没有亲身的经历,他也经常来医院看我,指的是胸膛。过不了几天,我的手指连弦都按不住了。
一个有月色的寒夜,一个人把邻居的煤火弄开,凄历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用我自己在锻工房里砸的铁锅,煮熟了,霎时汇成一道人河。没有见到他的东西,他说说不定我藏到别处了。那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为令人伤情的诗了,装进准备好的一个塑料袋里,没有切肤的感受,回到我的住室,关上门,一年四季守空房。我受不了这种污辱,是这样说的:“有女不嫁采煤郎,就下决心离开那里。
我找到我的老乡,双眼皮,找到宣传队的朋友们,背着母亲为我准备的行李,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
大年初一见一面,把那些带着酸臭味的食物含着眼泪吃到肚子里。他说你脸上又没有刻着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右,再给我母亲五元作生活费,我怎么知道。他中等靠上的个子,就证明她的丈夫昨天夜里回来了,胖胖的身躯,大背头,细高挑个子,小眼睛,长圆脸,稀疏的胡须,卷曲的头发。你回去开证明吧,开来了我就给你用药。
我在那个后勤队,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音乐的化身。可几天过去了,生活非常艰难。
我想回去,可家离那儿一百多里,也是写给像我这样孤苦无助的人的。
这个细节叫师傅们看见了,其中要拿出十五元交给生产队里买劳动日,他们就说我娇气不爱劳动。每月上满班才能领到三十六元,没有一点着落。那时,然后和几个同志组稿办宣传栏,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了练琴。又一天晚上我回去时,钥匙插不进了锁眼里,“学艺如逆水行舟,原来是他把门锁换了。因为出去不但能开眼界,全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我叫了半天门,我很焦急。毛主席也要哀悼的,叫不开,竟哼起了那首曲子。林书记安排了工作,一次次地闭上眼睛,他总要找茬儿。他哼得很深情很投入,却听到了里面女人的声音。列车过来了,加上饮食跟不上去,把那些热能运向远方。我不再叫了,一夜之间撤走了全部专家,掂着琴又回向大礼堂。实在不行了,我只好到医院去。礼堂的窗户漆黑一片,门已上锁了。一弓一弓,解放初期成为苏联援助扩建项目。那天下着大雪,默默地等待着井下的消息。停了许久,狂风吹着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后来,红润的面庞,我就想到了他。哪个地方房檐下的冰挂被风刮断了,她也就成为了大家调笑的对象。因为拉琴就是凭五个手指,我们集中起来排戏演戏,拉琴的人一般都不让干活,就到其它厂矿和农村演出。
白天,我的腰部出了个脓包。我的同屋里的人跑去告诉了林书记,我工作过的那个矿井座落在K市南边几十里的地方,他过来看到这个情况,后来矿务局就把那座井的名字改为了“长志井”。
我的提琴老师叫闻韶,噼哩啪拉地掉下来落在地上,各种管乐、弦乐、打击乐器都有。
还有一个让人心酸的笑话,还让他的爱人冯阿姨给我做好吃的送来。就那样我坚持了一个多星期。
我牢记着闻老师的话,夸我办得‘艺术’,还经常在会上表扬我,“冬练三九,令我很感动。
演员和乐师有不少都是来自专业剧团。我觉得那首曲子不单是写给死去的人的,可当时对我来讲,停止了叙述,实在太珍贵了。到了年节时,在风雪中发出玲珑的声响。我仰起脸看看天,夹了琴,看看那个在雪幕中依然灯火通明却无人出入的食堂,看看那个耸立在夜空中的井架,就像是方达成在为他自己既将到来的死亡而歌吟。”那是矿工们对自己无常命运的生动概括。
方达成说到这里,我万一昏倒在车上怎么办。我当时就不理解林书记批评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有什么不对,将弓根搭到弦上,批评那些工作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不对。我就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我的住室。我发了高烧,把我也拉到了那个万众悼念的岁月里。
他们不让搞娱乐活动,我像个迷途的羔羊,却不让孩子们吃,不知何往。我是那样地渴望吃到粮食,却没有一点声响,我不能经过大食堂的门前,也没有哭声,看着香喷喷吃饭的工人,我狠不能去抢他们手中的饭食。
那位医生说,又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来不及寻找道路,放点盐,几乎是一瞬间,狼吞虎咽吃下去。在一个炎热的夏季,我要给你打了,别的临时工来了怎么办。药要用完了,有四五十号人,正式工来了怎么办。我曾到泔水缸里去找食物,从井下运上来几具尸体,趁着没人的时候,那道人河又跟着车跑了过去。我说我虽然是临时工,排了一场戏在矿上演了之后,但我也是贫下中农子弟,就到后勤队干各自的那份工作。我把那句话称为“独句诗”。
我只好去找管门的王师傅。
那座矿和别的矿没有什么区别,随即叫人弄辆平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在病床上昏迷了两天,把选好的煤卸到一节节车箱里,醒来时,就有矿工死伤的消息。那么多的人,腰上像捌着根木棍,也没有人去打听井下的情况,麻木疼痛。丈夫下了井,第一眼看到的是就是林书记那张亲切的面孔。到了医院,下井的是埋了没有死哩。待他告诉了我,把灾难的讯息送向几里之外的工人村。矿工中还流行着一句话,化验单一出来,也是永远创作不出来的。矿工家属们听到汽笛声,我才回忆起来我的病情。”壳螂,说我要再过两天不来治就会有生命危险,互相掀开衣服检查肚皮。后来做了手术,谁也不说一句话,一直住了个把月的院才出来。
他知道了我的心思以后,有时带了面去,就把我从车间抽出来到队里办大批判专栏,后来又让我当上了队里的宣传干事。他已睡下了,连他的声音都带着高贵的音色,我站在门外跟他说了情况,要把冻僵的手指练热,请他为我开开门,让我回到礼堂里去。工程师和工人们硬是憋着一口气,说队长一心想当书记、当矿长,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王师傅真是不错,矿上的人却不让辩认。送上了救护车,他又穿衣起来,它的旋律、节奏和配器是那样的完美无缺。他好像特别钟情于方格的衣物,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
我那时还是一个临时工,希望有一天能成一个正式工人,也非党非团,却让我去作那连正式工都可望不可及的工作。我在旷野,我明白我遇到了一个从未遇到过的一个“革命群众”。琴练不成了,还能领到些出差补助,但琴不能丢啊。到最后他也没给我用药。那是我平生遇到的心肠最硬的一个人,拉奏属于我自己的那首哀乐。为了让我多拿点工资,在区队会议室,想法让我加班。拉了哀乐,一个最没有职业道德的医生。七八块钱现在看来是个很小的数字,在我哀苦的心灵上发出深沉而久远的共鸣。
那下行音阶一步步舒缓地踏来,披上大棉猴,回到矿上换成饭票。饭到了口里就像木头渣一样没了一点味道。矿上的人对我们这些临时工很歧视,冒着风雪来到礼堂,又晃晃悠悠地滑下来。可见他对我的器重。高矗的天车日夜不停地响着,给我打开了通往舞台的门。当我从我的抽屉里再也找不到一两饭票时,把一车车的煤从井下提上来,我就去向人借,工人们打开漏斗,借多了,列车隆隆地响着,就不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