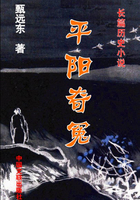这次泰斗讲座是由东大校党委直接组织的。在那次行动之后一度出现的思想混乱中一在东大,这种混乱是一股平静和沉闷底下的潜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中、青年教师的出国潮一举办这次讲座无疑是有极大积极窓义的。比较起来,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其实历经了更多的坎坷和挫折,却又反而有比中、青年一代更大的爱国热忱。真正的虽九死其未悔。
居东火泰斗之首的是彭佳佩教授。
彭佳佩和她丈夫乔博吾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内是公认的。文革期间,他们夫妇遭受的迫吉也是令人发指的。彭隹佩教授是残酷迫害的幸存者。她对那场历史悲剧的态度,也是很不寻常的。
彭佳佩教授只恨自己。
回顾文笮,人人都对当时的黑咭有切齿的恨,诉不尽的苦。唯有她观点特别,她纯粹从法学的角度认定是自己有罪。她恨自己,恨自己八十六点七公斤的体重。她断言她先生的不幸以及她后半生的痛苦都是这体重引起的。
彭佳佩教授的丈夫乔博吾先生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那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于是很激动地儿经努力,几经辗转,从美国回到袓国大陆。他的导师很惋措,通过女儿力图挽留他一起主持一个研究所。他跟导师的女儿也的确是一直相爱者,但他还是执意回国,他希望导师的女儿为了爱情追随他。这当然无法实现。导师的女儿怀着最后一点点希望一直把他送到日内瓦,试图让他改变主意。最后仍不免一场抱头痛哭,歧路作别,从此天各一方。
回国以后,乔先生同美国的导师和导师女儿还有过一段书信来往,后来这种来往就引起了注意,并从而受到种种暗示。只好断绝联系。情义尚存,心里而那种难以割断的惆怅多少还是有的丹心报国,表明心迹的态度却也是毅然决然的。
乔先生是数学教授,属于计算方面的事都讲究梢确。自己体重多少,工作量多少,每天需要多少卡路里,因而米饭该吃多少,面食又该吃多少,都有一定之规。这种精确后来引起了许多误解,被视为悭吝,又由此导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是配偶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经人介绍了女友,他偕此女友去街上散步。女友提出看电影,并主动买了票。看完电影,他在影院附近的小吃店款待女友,买的是肉丝面。女友又要付账,他起而按住女友手臂,慷溉说,这回我来付。却又说,不过你得找回我五分钱;一碗肉丝面比一张电影票的价格要多出五分。女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他呆坐半天,却莫名其妙。经人点拨,下一次,同另一位女友,他便调换了位置:他主动买电影票,而那女友又抢着付面食帐。完了,他则主动将五分钱交付女友,以平衡逆差。彼女友又转身即走。他又呆坐半日,陷人更大困惑。
一直到终于遇到彭佳佩,才结成秦普。婚后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丼中比较突出的是他们在开支上都糈于计算。比如,除了书房,共他房间的照明都用低瓦数的小灯泡;对保姆定了许多具体的法规:淘米的水必须用作洗碗盏每天烧的煤球和引火柴都必须有数,不能超过极限极限是刚好够用剩饭剩菜不到长白毛决不能倒掉。而他们的收人相当可观。彭佳佩又一直没有生育。他们的月支出,还不到月收人的十分之一。
这些后来便构成了他们的罪状,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高等学府的文化革命,上纲上线并不简单化。有学问的人提出了见之于马列经典着作的论椐: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便是以艰辛悭吝、聚敛财富着称的。而乔傅吾、彭佳佩这一对黑夫妻的种种行状何其相似乃尔?
乔先生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旬杀的。先是怀疑他里通外国。当然事出有。他交出了美国教师及女儿的所有来信。但这些信除了树立乔先生的爱国形象之外别无意义。于是转而去查他的档案,发现了重大疑点。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同另外一个学生合作用了一个化名在墙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现在看来亦无问题。呼吁的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同心同德抗战。但是现已查明:那个学生是中统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肃反时破获,被锒压了。那么,当初同该特务那么亲密的乔先生就没有一点干系么?尽管在回国后的历次审千中,乔先生对此人此事都作了详细交代,组织上也明确作了结论,肯定乔先生于此无涉,然而--
那怎么行呢?我们这么大个系一个人也揪不出?系工宣队长是位很纯朴的人,他很为难。把所有人的档案翻来翻去,有资格揪出来的还是首推乔博吾。他的历史戢为复杂,如果他也不能揪,别人就更难说得过去了。工宜队长果断指出:裆案上的结论是文革前做的,是错误路线的产物,当然应该重新认识!
就在这种情况下,董敦颐犯了他认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正因此,他后来就总是尽一切可能给予彭佳佩极特殊的关照。)他对工宣队长作了妥协。他唯一能做到的是同工宣队长商定:先揪,以利于打开运动局面,但必须很快解放,最多不能超过一个月。此前,董敦颐已经结合进了系里的领导班子。他是留苏的,当年是作为反修战士光荣回国的。又是全校系级前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副主任(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很早就获得解放。
乔博吾被宣布为美蒋双料特务的那天,他先是发了半天呆,终于弄明白自己被置于何种境地,却仍大惑不解,于是摘下从美国带回来的宽边玳顼眼镜,伸长脖子,眛缝起眼睛,问工宣队长:我是特务?又问董敦颐:我是特务?又问各位同事:我是特务?又问认识的不认识的学生:我是特务?
许多人都低下了头。答案在他提出问题前即已布告周知。
阏到车库(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赶到这里来了),他又问彭佳佩:
我是特务
你当然不是。彭佳佩自然是不必回避。
但是彭佳佩说了不算。
乔博吾没有等一个月的耐心。而且他也不知道董敦颐与工宣队艮还有那么个协议。揪出来的当天晚上,他就同彭佳佩研究。杀的法子。
确实需要研究。比较方便舒适的法子当然是自缢。但是,车库空徒四壁,一扇窗子(实际是个透气孔)踮脚伸手也够不着,而且只有窗洞,没有窗门,也没有窗栏杆。一盏昏喑的电灯紧贴在顶棚上。除此以外,四面墙上连一个钉子也没有。唯一可供利用的就是那床了。是从学生宿舍搬来的那种床头、床档、床铺连成一体的床。非常符合规格:长度是两米远,超过他们的身高。
他们于是奋力把床立起来,使长度变成了高度。然后为了绞索,他们又颇费了一番功夫,现成的绳子是没有的,必须临时制造。他们先考虑了床咕和被单。马上就觉得那太奢侈了。乔先坐翻了翻说,不行,这些都还是半新半旧的,后人可用,撕了可惜。只能在两个人的衣服上打主意。最后忍痛撕了乔先生自己打了补钉的衬衫。
他们只拧了一根绞索。将其两端各拴起一个人的脖子,将绞索的中部挂上床的一只脚。他们于是就象两条鱼似地挂了起来。
一切都极顺利。一蹬开脚下的凳子,两个人马上就都入了无我之境。
后来的结果是彭佳佩九死一生,乔博吾一去不返。究其原因,确是因了彭佳佩的体重。她比干瘦的丈夫至少要重一倍。蹬去凳子之后,她便立即下殆。只是因为绳子长度的限制(绳子的长度又受到一件旧衬衫的限制),她的脚掌未能全部着地,但已经着地的那咚部分却刚好足以使她间死神抗衡了。稍作人工呼吸,她便苏醒。
而乔博吾却因为她的沉重高悬出三界之外。
是我害了乔先虫。
彭佳佩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这样说。甚至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讲演时也这样说。
A Professor Killing Her Husband(一个杀害了丈夫的教授。)
当地一家报纸不知是理解错了还是故意地作了这样的报道。于是舆论大哗。弄得好奇的美国人像看从淼林里跑出的古猿似地来看她。许多听了她讲演的华人,以及乔先生在美国的故旧包括那位导师的女儿(导师早已去世,她现在也是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了)都很气愤。彭佳佩却置若罔闻,不予辩速。犯不着,她想。她是应该把罪责全部担当起来的。她有那么多疚恨。人家怎么辱骂地,她都不以为过份。假使她不是那么重,假使那么重的是乔先生,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或者完全相反。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损害她。她的形象仍然是光辉的。即使是美国人也都在一阵惊愕、一阵好奇之后很快便懂得了是我杀害了自己的丈夫的多层含义。中国人当然更重事实。人们不仅不能罡若扪闻,而且一如美国人惊诧于一个杀害了凸己丈夫的女人一样,得悉了难以置信却又不能不信的事实:
她同乔先生在决定自杀后共同签名的遗嘱里只有一句话:把我们在银行的全部存款献给社会主义中国。
遗嘱是乔先生驾的。他写的是中国而不是袓国,显然那一刻他的灵魂已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当时也忘记了,那笔存款早被冻结了。
那笔存款将近八万元。彭佳佩坚持履行了她和乔先生的共同诺言。并且把补发给她和乔先生生前被扣发工资上万元也一并捐赠了。
想起她和生前的乔先生的艰辛悭吝、聚敛财富,众人不免唏嘘。
她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乔先生导师女儿的女儿。那同时是乔先生的女儿。是乔先生同导师女儿在。内瓦最后那个夜晚的果实。彭佳佩给国内写信,取得同意后便代表校方邀请女儿、这是两个不幸的女人共同的财富了。到东大来担任英语教师。
美国女儿走近那所红房子的时候,对自己的感知能力发生了深刻的怀疑。
不错,就是这里。以前你父亲和我住过,现在是我们的那时候,红房子已经有了足够的窗户,有了卫生间、厨房,自来水。也不仅住着彭佳佩,池还有了邻居。门前有很大一块空地,邻居们养着鸡。一片小树林掩蔽着红房子。淡淡的雾霭和炊烟在林子里缭绕,鸟在鸣唱。
怎么样?好吗?刚从异国回到家门口的彭佳佩激动得不得了。
No,No,在奢华中长大的美国女儿把双肩耸得老高,差一点就要哭出来,不能想象,不能忍受,这简直是Slum(贫民窟)!
彭佳佩好说歹说,苦口婆心;从文革造成的普遍灾难一直说到学校的具体困趣。要把废墟重建起来不可能太容易。学校已经抓得够紧了,很快池们就会有新房子,正在盖教授楼。--为了美国女儿,为了乔先生本人给人间的活的赠品,亦为了她对乔先生的钟爱,她已打算牺牲红房子而寄望于教授楼了。
美国女儿总算答应留下来,但是住进了外教楼。她无论如何不肯住在红房子里广不行,父亲住过的也不行。毕竟是美国女儿,而且她未见过中同父亲。
教授楼盖起来了。但是能分配给教授的不到整幢楼的一半。而分房的方案是洱合法合理合情不过的。首先是将教授套上和似的行玫级别(这是必须的。无规矩不成方圆。无级别则无法分房。上半年,彭佳佩参加省政协会议时,就见一位宗教界委员一座庙的住持在会议报到表上添了副处级当时许多人都有些奇怪,但那和尚作揖说:善哉,副处级确系政府恩赐,老衲断不敢狂妄造次的。)然后再按照人口(以户籍簿为准工、教龄(是否在校又有别)记分。以分数多少为顺序。
教授、副教授们均上了年纪,一帮长期与世隔绝、自命清高的教书匠文革期间一家人被拆得四分五裂,一夜乡心几处同。倒是处长、副处长正当盛年,也更有职务上的方便,早已经过努力,使得合家大团圆,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同堂。自然,他们住新房子的条件是要充分得多的。
结果,教授楼正确的提法应是处长副处长教授楼。因为教授最少,不敢为天下先。
以教授之名始,以处长之实终。学校虽然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自应以前者贵。社会上一般见识,教授也比处长名气大。却又不然。一讲教育体制改革,首先讲的是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未听说要对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的。这就似乎是法定了由后者来决定前奍的命运。事实上,一切事倩(包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的确都要后者来做。没有后者,前者存身的地方都没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贵从何来?
过去,彭佳佩以教授资格分到房子没有要。时势变化,她需要分房子了,却又没有分到。因为她实际是一个人,即使加上美国女儿,分数也比别人差谇多。分房名单公布后,受到打击最大的是彭佳佩的美国女儿:
欺骗!妈妈,你欺骗了我:
她的华语比刚来时流利得多了。接着她就收拾行装要回美国去。
彭佳佩当然是很悲哀。她不再劝说美国女儿女儿也不再相信劝说只是恳求女儿临行前同她一起去拜访一次校长。
美国女儿同她去了。
这是一幢建校初期遗留下来的平房,至少有近百年历史。四壁斑驳,地板也烂的烂、裂的裂了,一脚踏上去满屋子家具便一片轰响。昏暗、湖湿、弥漫着发槛的气息。
校长这一次分房把自己的四室一厅让给了中文系的蹇先生,蹇先生的儿子、女儿虽然迁回,户口却还没有正式落下来爹影响了蹇先生分房的分数。
美国女儿挽着中国母亲的胳膊在校长的屋子里默默地站了老半天,喃喃地说:
你们奉行的是斯多噶主义。
也许是强劲的美国传统精神起了作川,也许这种斯多噶主义也确有动人之处,她后来竞没有走。随着时日的推移,她逐渐适应了东大的现实,逐渐接受了并相信了许多优秀的中阁学者、首先是中国母亲彭佳佩教授的观点:一切都被物化的工业社会人所面临的只有孤独、空虚和崩溃,而在物质相对缺乏的地方反而不会有形而上的苦恼。
彭佳佩及其美国女儿的事迹无疑是极有针对性又极有说服力的爱国主义教材,为省内外和教育界内外的许多报刊刊载,并冠之以一代师表一类醒目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