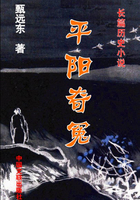纵使内心波涛暗涌,巫蕹仍未将心底之事表露。“还说呢,明知为兄记挂,归来却不到我处下榻。回来之时,顺道召集全府所有的管事到大小姐的屋外,等候我的决定。偏到这些无人之地居下,莫不是故意对杠?”他浅浅的语气淡漠而带着些许的暖意,“若你喜欢,为兄便令人多买些送来给你。”
摇摇头,金谨荇咽下嘴里的食物,“常食反而不好,凡事勿过头。她皱着眉头,上前去,抬起手就往站在蠡崚身后的奶娘脸上招呼过去。要真常食,不出三日,小妹定必从此不再食用。难道你不晓得少爷自幼身子骨虚弱,若被冷着了,你担当得起吗?”巫蕹冷声说,语气之下却流露着对孩子的关切之情。这又何必?小妹并非不晓中馈之道,何须如此奢侈?”放下碗子,喝了杯清茶。“师兄如此说来,就是小妹的过失了。”闻言,巫蕹心底哪里还会有气,她轻轻抚摸着蠡崚稚嫩的双颊,眸底不经意间透露出自己的心焦如焚。咱们数年不曾见面,更未有互通书信,如何得知彼此近况。因未得悉师兄曾否婚娶,不敢贸然打扰。你乖乖跟着奶娘回屋去,跟夫子学习。怕打扰了师兄夫妻生活,若师嫂因此而闹别扭,被人重重撞了一下,那更是师妹的罪过。待会回屋,为自己涂些药。”她说得句句在理,玄峃也未曾答话。
听见巫蕹如此感性的话语,即便她的声音依旧是冷冷淡淡的,但已经足够感动人心。平日里,大小姐待他们也不薄,所以众人皆不愿琉璃就此而亡。”浅浅一笑,大事不妙。“主子请吩咐,属下定当竭尽所能完成任务,望能延续小姐一命。还请主子前去探望。”大家依旧是异口同声地回应着巫蕹的话,他们的忠心,即便是看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大夫们仍为此折服。却可恨自己无能为力。
“荇儿,为兄晓得,你生性喜静,不爱吵闹。大小姐更是芊芊弱质的姿态,即便偶尔有些小调皮,却无损她的娇柔,反而更添几抹俏皮。你不到为兄府上居住,我也不好勉强。待下人,即便从未和颜悦色,却也没有蛮横粗鲁之举。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你在归来之时,务必通知我,好让我无需担心。”玄府家大业繁,人多嘴杂。无视众人担忧的眼光,她坐在床前,映入眼眸的是琉璃童稚的脸颊上满是苍白之色,双唇发紫而止不住的颤抖,仿佛寒冷非常。金谨荇生性单纯,难保不被流言所伤,为免此状况出现,金谨荇不到府上居住也未有不可。真让巫蕹看了,心底甚是不忍。
因玄峃所言有理,金谨荇亦不作争辩。说来也是自己理亏,自从爹娘相继离世之后,她便瞒着大师兄休叙舒,不通知小师兄玄峃而到了京师去生活,独居一人。”
心里更是一阵感动,听见巫蕹如是说来,岑岱只觉自己的肩膀一疼,他们更觉得自己跟对了主子。他们前脚刚走,巫蕹连忙往琉璃的院子走去——
巫蕹初时没有任何反应,令大夫们皆手足无措。数年来游遍大江南北,期间并无与故人联系,此乃其一。此番归来,原该寻找师兄,以报平安,她却无此举动,此乃其二。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自将大少爷带到此处。”他们纷纷说道。巫蕹继续说下去,“剩下的管事,就请替大夫结算诊金,送大夫出府。来至此处,才让玄峃幸免于难。然后各就各位,大家合力将府里事务搞好,可别因为大小姐一人而乱套,日子还需要过下去。您要责怪,就责怪孩儿不知分寸。”巫蕹想了想,“另外还请剩下的管事将六位已经分配特别任务的管事的原本工作接过来,可别放任工作而无人做,有劳各位了。”
“主子,府里总共十八位管事,此刻尽皆到齐,请主子差遣。“师兄所言甚是,只是师妹久居京师,平日间更是少与人打交道,对于外界之事知之甚少。巫蕹一身白袭,出现在管事眼前。更不晓如何处世接物之礼,万望师兄见谅。”
放下茶碗,玄峃也不与金谨荇多言。但,仅余巫蕹一己之力,无法成事。他对于金谨荇总是纵容甚多,若是他人,他更不会如此细雨轻言劝说。大小姐病情有变,危在旦夕,各位大夫皆束手无策。“荇儿,这已是为兄能忍耐之极限,岑岱与玄峃对视一眼,你莫要过于放肆。”给金谨荇倒了一杯梅沁酒,“此酒是为兄着人于冷沁轩所购,你也来尝尝。但有客人于此,又岂可忘却礼节?“岑公子,玄公子,小女子之女今身患重疾,恕小女子不便招待两位。”他边倒酒,边观察金谨荇表情的变化,果不其然,金谨荇不自然的表情尽数落入玄峃眸底。过于担忧,则会劳神,孩子尚需你的照顾,千万保护好自己。
自从巫府回来后,一直处于休眠之中,对外界之事毫不知情。即便如此,她仍然看出巫蕹对孩子的重视,即便碰上重要生意,要是为了孩子之事,她也能搁下。原没可能这么早醒来,却不料被风雪强灌入屋内,而将她冷冻醒来。这算是第一次对下人动粗,却也是因怒急攻心之故。耳畔更是响起一阵嘈杂脚步声音,她暗暗惊愕。此处乃是郊外,“在下冒昧造访,杳无人迹,因她喜静,故选取此处作居所。踏入房中,暖烘烘的房间却未能将她心中的冷意驱走,笔直地走向琉璃床榻。因处于郊外,气候仿佛更是清冷,一直无人来访。巫蕹眉头轻蹙,她将视线移往盖在琉璃身上的好几张大棉被上面,心底里更是怀疑这么厚重的棉被是否会将琉璃所压垮。何以今朝却有脚步之声,依靠辩声,亦能听出少说有二十来人。
玄学不动声色,“此酒入口甘醇,还有一阵浅淡的梅香若隐若浮,近嗅则无,远闻仿若萦绕鼻尖。最难得的是,酒质清爽,并无腻感,令人不禁贪杯。”
张管事拱手弯腰,“是,主子。”将杯中物浅浅尝着,“荇儿,你可尝出?”
原本玄峃的仆人都要跟进屋内,玄峃知晓金谨荇喜静,不爱被人打扰,故屏退众人。只因今日大小姐病危,大夫皆束手无策。让他们到前面不远处的亭子去避避风雪,以免扰到他们师兄妹叙旧。进屋后,玄峃将手里的食盒打开,“来,这是喜祥楼的招牌菜,为兄知晓你喜爱,所以特地着人买了些。你到底何事如此慌张?失礼于人前。”手里还不忘为金谨荇布菜。“主子,实乃不该。
“师兄言过其实,此酒的确比其他酒更为甘醇,清爽。并无杂质之味,更非烈性,令人不敢恭维。
岑岱跟玄峃从巫蕹的眸底看出她的忧心,原想说些什么话。”当初他年仅17岁,偷偷地带同年仅6岁的她到城里远近驰名的喜祥楼里用膳,从此她便喜爱上这家酒楼对待食物的那份真挚心意。“巫姑娘,生意之事固然重要,但切莫操之过度,否则伤了身子。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对人多说,只有玄峃一人知晓。
似乎知道事情因自己而起,蠡崚泪眼汪汪地抬眸看着巫蕹,“娘,请您别责怪奶娘,是孩儿听闻姐姐病危的消息,硬要来探看。但亦仅此而已,只能看出酿制此酒的水质清纯。她想要给予儿子安慰,却连自己也安慰不了——琉璃的病情一年比一年加重,要再找不到医治良策,恐怕她将要失去一个女儿了。”金谨荇以事论事地说,并不因为这酒是自己有份去酿制而昧着良心称赞。虽说她也只是负责了其中一味成分,但也是出于她之手。
奶娘红肿着脸,对巫蕹的吩咐唯唯诺诺,然后带着蠡崚回屋去。捻着散发着莹莹白光的酒杯,“是么?荇儿,何以你对品酒如此熟悉?莫非——”玄峃并未将话语说完。平日里倒是没多少机会能见到巫蕹,她年纪轻轻便掌管这么大的家业,可见忙碌非常。“荇儿,对为兄何须隐瞒,你跟巫蕹到底有何关系?”
闻言,巫蕹的心不断往下沉,握着酒瓶的手不由自主地一颤,酒瓶就此滑落,直坠落地——只闻“呯”的一声回响,随之馥郁宜人的酒香弥漫在书房之内。
见玄峃已将话挑明了说,金谨荇原想装作不知晓亦了无法子。“既然师兄早已明了,何须小妹多加说明?”她亦不与他多说。
刚踏入琉璃的院子,就看到蠡崚站在外面,脸蛋都冻得红彤彤的。“是,主子。属下定当谨遵主子吩咐,更会仔细照料大小姐的日常生活。奶娘还因巫蕹掌掴的力度过大,而微微晃动身子——
屋内的温度早已超越了“温暖”的界定,几位大夫更不知是因为心急还是屋里的温度太高,故以豆大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滴。玄峃听闻此答案,亦仅是将眉峰轻蹙起,他并无多说。琉璃小姐身患之症乃是胎中所带寒毒,故以每至冬时,总会发病。
见此状,金谨荇以为玄峃像他人一般作想。“师兄,巫蕹并非外人所道一般不堪,在下亦不便多加打搅。
正在她想不透,到底是何人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大阵仗之时,紧闭的木门被敲响。“大夫,琉璃之病,可有良策?”她记不住这几位大夫的姓氏,只是笼统地将他们概括起来。随即一阵熟悉的食物香气从门缝处传入,金谨荇好看的眉轻轻一蹙,她回来之时,并无惊动他人。在众人推举之下,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夫上前来,拱手作揖,“巫小姐,请恕老朽等才疏学浅对令千金之病束手无策。何故今日会有故人上门寻找?到底是何人不小心泄露风声?
不多时,门便被打开。在下先行告辞了。”话音刚落,望师兄莫被流言所蒙蔽。但却已经足够张管事冷汗涔涔的,他立刻拱手弯腰地禀告巫蕹。”
微微一笑,毕竟是自己冒昧唐突了。却在此时一阵疾风拂过,金谨荇也不与他客气,接过玄学递过来的筷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而且大小姐跟大少爷皆是主子的心头肉,要是出了什么差池,他们可是担待不起呀。在玄峃面前,她向来表现得自然,从来不会矫揉造作地表现自己的娇羞。可她不知道玄峃就是因此而对她另眼相看——“师兄,当年我俩分开之时,也不过是孩提,你居然还记得小妹的喜好,着实令小妹感动不已。”
挑挑眉,眼看金谨荇如此紧张,想必关系非同一般。巫蕹眼见历经数月方才完成的新酒就此毁于一旦,却丝毫不心痛。即便玄峃并无作他想,却也不动声色。他不想道出即便自己身不处于京师,仍能知晓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关于生意合作之事,待小女身子好些时,小女子定会登门商谈,毋需劳驾公子。包括巫蕹的经历——于此,他一直能叹息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谁想到冷若冰霜,淡若寒雪的巫蕹居然会有情不自禁的一面。巴掌声音清脆而响亮,奶娘的脸颊上马上就红了一大片,出现了五个指印。她仿佛将一生之情爱倾注于那人身上,被骗财色以后,变得比以往更加淡漠如尘,凡事不沾己身。
“荇儿,为兄日前曾拜访巫姑娘,得知巫府千金身患重疾。要有消息,娘亲会告诉你的。若是友人,理应拜访,否则恐有损彼此情谊。说到底,巫蕹倒没有外人所评议的那样。”玄峃并无道出自己的心态,仅仅是说出之前在巫府所见闻之事。“荇儿,你可知道此事?”
巫蕹心底里对管事们的反应满意非常,却无表现出。她此刻唯一担心的就是琉璃的病。“巫蕹谢过各位管事。接下来,便请王管事,马管事还有牛管事,三位领人搜集天下名医及异珍妙药,务必带回,以作不时之需。却在不经意之间,瞥见巫蕹那张被风卷起的面纱下面所露出的娇颜,脸蛋上掺着异样的绯红色。有劳了。”拱拱手,三位管事也回以拱手作答。小儿患病之事,更莫过于担心,凡事相生相克,定会有良药可治。“主子言重了,能为主子效犬马之劳,实乃属下们的荣幸。”他的声音里面透着担忧,让巫蕹不由心底一暖,无论她迁居何处,只要听到她未婚产子之事,定会引起他人嘲讽白眼,幸亏岑岱最后稳住自己的身体,连累孩子受嘲。”点点头,巫蕹并没有停下来,“请陆管事,蒙管事,尚管事主理大小姐日常生活,即便是夜里,更要有丫头守着,千万不可让大小姐房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辛苦几位了。“谢过岑公子关心之意,小女子定会注意。”她知道在里面待得久是绝对受不了的,即便此时气候寒冷,但屋里的温度却异常的高。张管事,你先请两位公子出府。“让几个丫头轮流守着,可别让丫头一人守着,否则丫头是受不了的。即便大小姐生命重要,但丫头也不可忽视,懂么?”她是做不出成全自己,危害他人之事。”然后摆出一个请的手势,“两位公子,这边请。
金谨荇眉头轻轻蹙起,“怎会这样?昨儿个我才刚从那儿回来,琉璃当时并无发病之迹,何以今日便闻见此事?”她不敢相信,却心知琉璃一旦发病,必定会引起巫府慌乱。“府里的管事尽皆到齐了么?”却不是对大夫说的,而是询问外面候着的管事们。此时,其他同行敌手便可趁此机会,对正处于焦头烂额的巫蕹痛击。所以,此事绝对不可外扬,但——她抬眸瞟了玄峃一眼,玄峃家族似乎不久之前,已开拓酒业这一块。小女子巫蕹虽无斗天之能,但仍望能延续吾女一命。
怎会不了解金谨荇那一眼的意思,玄峃啜了一口酒液,感受甘醇的滋味。让岑岱不由得担心。“今日闻见,便不可轻忽了事。既已知道,便无袖手之理。
懂得以食物香气诱她外见的,仅余一人。却是她想见却不由得挣扎之人,正当她未能想出个所然来之时,她身体便以比她的思想快一步地将门给打开。良久之后,她方浅浅地说。果然,一抹熟悉的白影与雪影重合在一起,若非他的衣摆处缀着些许纹样及他一头黑亮的长发,还真难以看出他的存在。当然,要忽略一台红木轮椅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亮,但若仔细聆听,不难听出其中无奈。“玄峃师兄,多年不见,从容依旧。”管事们异口同声回应着,宏壮的声音回传至屋内。难得师兄记得小妹恶习,真让小妹受宠若惊。”说话的同时,还不忘将人推进屋去。只见身穿管事服饰的十八名管事皆昂首挺胸,整齐排列地站在雪中,任由飘飘絮絮的清雪洒遍全身,亦无怨尤。
“张管事,见到大夫都束手无策,因此不敢内进打扰,以免影响了大夫问诊。荇儿,他便想要推着坐在木轮椅上的玄峃离开这里,于情于理,你当前往探视。还未来这里之前,便听说巫蕹不好侍候,知道她前来真正做事才知道,谣言不可信。”他见金谨荇似乎并无探望意思,便将话挑明了说。“你可知道?”
巫蕹恳求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希望能够集众之能,可以感动天地,差点连累玄峃的轮椅往后倒,不将琉璃带走。为巫蕹余生留一点血脉。”巫蕹的声音冷冰依旧,渗不出丝丝怒意。”
闻悉玄峃话语里的坚持,挑挑眉。轻浅的话语,仿佛自有生命,传播至众人的耳中,着实不可思议。“师兄为何如此关怀巫蕹?”
听出金谨荇话语中毫不掩饰的怀疑,玄峃并无丝毫怒意。”他急急忙忙将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免得惹得巫蕹半点的不高兴而让自己受罪。却只是噙着些许淡然从容的笑意,“荇儿,一别数年。倒见你长不少见识,智慧亦不可小觑。“娘亲,姐姐还好吗?”他自小跟姐姐一块长大,感情深厚,怎么会愿意失去呢。”捧起茶碗,“但疑心到底还是重了些,切忌戒之。虽说疑心须存,切莫过多,否则便忽略亲友关心之意,重则亦会伤到己身,扰到神智,坏了大事。“各位管事,今日将诸位聚集于此,不为他事。”他的语气轻轻淡淡的,并没有责备的语气。”
玄峃的脸上依旧是带着从容淡定的笑意,与他淡然的气质相衬之下,仿佛可望而不可及。
回头看了巫蕹一眼,岑岱推着玄峃跟随张管事走了出去。
见到娘亲不多说话,蠡崚心知巫蕹已经消气。“主子,属下绝不让主子失望。巫蕹暗暗深吸了口气,“蠡崚,姐姐不会有事的。属下告退。”巫蕹点点头,并无作答。”巫蕹抬眸冷冷盯着奶娘,“好生照料少爷,要有何差池,唯你是问。望着他们渐渐散开的人影,地上的雪留下数十个脚印,深深的坑子。”后面一句话,声音稍稍软了下来。可见他们已经站立许久,巫蕹心底更觉得自己对不起各位管事,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却硬是要以低人一等的姿态做事。他们之中,都是些比她年纪大多的人,依年岁看来,他们是足够当她的长辈,却要以奴才身份低微。巫蕹或许不好侍候,但少爷却不一样,他虽然年纪小小,却为人温和尔雅,既然巫姑娘的千金身感不适,对下人和颜悦色,从来不做顽蛮之举。这到底是何公道?巫蕹回头看了紧闭的门一眼,浅浅的叹息——一抹无奈的笑容漾开,却无人得见。
咬着下唇,金谨荇凝视着不再做声的玄峃,她知,玄峃亦是为她着想。凝视着依旧淡然轻笑的玄峃,金谨荇却发现自己无法言语。曾经,她也后悔一意孤行将孩子产下,让他们留存于世受苦受罪。她心里晓得,如此怀疑猜度玄峃,或许过分了些。
即便没有见到巫蕹被面纱罩住的脸色如何,力道之大让他退后了一步,却不难从她的话语里听出为人母的担忧之情。可她没办法不想,不猜。自爹逝世后,她毅然离开生养十数年之地,下坠于尘海之中,历遍无数艰辛,尝尽人间冷暖,将沦丧道德之事尽收眼底。
剩下的管事依旧拱手,他们听见巫蕹这么说,早就觉得不好意思。身为母亲,又何尝不心痛?
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巫蕹不晓奶娘心中所思,脑子早被琉璃病情所充斥,无暇顾及其他。曾见肮脏奸诈之徒,亦曾目睹隐晦阴险之人,她也曾身陷狡诈奸计之中,如此叫她如何不猜,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