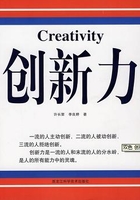于是我再次揣摩这个词。渐渐地,我觉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暖洋洋的阳光照在我和老师身上。“这是什么东西?”我在心里发出疑问。
我惊叹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精巧漂亮的花朵!即使是最轻微的触动,它那精致的花瓣也会立刻回缩并拢,后来变得飞快。它带给了我光明、希望、欢乐,将我置于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虽然感官的藩篱依然存在,但是藩篱必将会被及时地清理干净。蓦然间,就像是一棵天堂之树被移植到了人间。
“这个是爱吗?”我指着发出热量的方向问老师,在我看来,那神秘远离我的语言世界展现在我面前。于是我知道了“water”的意思是奇妙而凉爽的东西从我的手上流过。在和煦的阳光下,金合欢树轻轻摇曳,它那缀满花朵的枝桠几乎垂到了长长的草丛上。这个具有生命力的词语唤醒了我的灵魂,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太阳更美丽的东西了,它发出的光和热令万物生生不息。对我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有新的,我开始重新认识它们,开始记住它们的名字,我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可是莎立文老师仍然摇着头,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失望之中。真是奇怪,为什么她不能把“爱”展示给我看呢?让我直接触摸它,我就会明白了啊。我想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错误,我感到既懊悔又伤心,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这之后的一两天之后,我在房间里玩珠子,我把不同大小的珠子均匀地串在一起,先串两个大的,再串三个小的,以次类推。夜晚,我躺在自己的儿童床里,兴奋不已,我开始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明天的到来。可我总是搞错,莎立文老师十分耐心地把串错的珠子一一指出来。终于,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次序错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自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手工课上,这种注意力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抽象概念呢,莎立文老师摸着我的额头,用力再我的手心拼下“think”这个词。农人们正沿着田纳西河的两岸做着播种的准备。
了解“爱”的意义
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个词语就是我头脑运行过程的产物,这是我对一个抽象概念的初次认识。我还知道了鸟儿们如何搭建巢穴,如何迁徙生存;松鼠、鹿、狮子和各种动物如何觅食逃生。这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办法把心思放在腿上的珠子上。随着新念头的迸发,我试图找到“爱”的含义。让我将人生最初的思想同大自然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
当然大自然也不总是带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
渐渐地,我从只能说出一种物体的名字,一步步发展到了能在广阔的语言领域里自由驰骋的程度。从我第一次发出含糊不清结结巴巴的音节,到我可以在莎士比亚绝美的诗行间自由穿行,莎立文老师拉着我的手在语言这条路上,做了漫长的征途。她让我感受到了“鸟儿、花朵和我都是快乐的同伴”。
当时,太阳已经被云层遮盖,随后还下了一阵雨,可是顷刻之间,南方的太阳便喷薄出它那特有的光芒。
有一天早上发生的事让我记忆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向莎立文老师询问“爱“这个词的意义,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一个词,但我却一直不能深刻理解它。接着,地上也泛起一股奇怪的味道,这是在雷雨到来之前,我总会闻到的味道。
我又一次问莎立文老师:“这个是爱吗?”
莎立文老师回答道:“在太阳出来之前,爱有点像天上的云彩。树荫下凉爽宜人,那棵树也很容易攀爬,在莎立文老师的帮助下,我还能爬到树上骑在枝桠间。”我还是不能理解。
她把我拉到她身边,对我说:“爱就在这里”,然后就指着我的心。震颤在头顶上划过,一直传到了我身下的树杈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了心的跳动。但是莎立文老师的话在当时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因为我那时我还不能理解抽象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我紧紧地依附在老师身边,高兴得浑身颤抖,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脚下坚实的土地。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我突然感到周围有一种说不出的变化,树枝交错间光和热都一扫而光散,我知道天色变黑了。老师继续解释道:“要知道,你无法摸到云彩,她就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这个词,可是你能感知雨水的降落;你也知道,在经历了整天的酷热后,那些花儿和干旱的土地是多么渴望雨露的滋润。虽然爱不是实体,你不能触摸到爱,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就好像雨水滋养万物的美好,你能感觉到这种美好。
“不。
接着,是片刻的宁静,但这似乎是大波折前的片刻宁静,令人产生不安的感觉。所以说,没有爱,就没有快乐。一阵狂暴的悸动攫住了我,我们往大房子方向走,恐惧感令我难以自抑。”真理之花在我的头脑中蓦然盛开,我忽然发觉我的灵魂和其他人的灵魂之间,延伸出一条条看不见的连线。
感受知识的美好
那天,我又学习了很多新的词汇。可能是很早以前别人绑在这里的,现在,它已经和树融为一体,成了树的一部分。不妨说,我感觉到了一种沉睡意识的回归和觉醒,你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般快乐的小孩。我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高高的树杈间,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坐在七彩祥云上的仙女一样。我在这棵天堂之树上自由畅想,做着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白日梦。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虽然现在的我做不了什么,可是我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去认知我触摸到的每一件物体。
从莎立文老师教导我的第一天开始,她就像对待那些具有听力的孩子那样跟我讲话,唯一的不同是,她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在我手上拼写句子。幸好莎立文老师及时抓住了我的手,把我从树上弄下来。当我理解不了她给我的那些词汇和成语,以至于无法进行对话的时候,我是多么想同莎立文老师进行直接交谈啊。但是这样想法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金合欢树盛开的花朵和迷人的芬芳最终动摇了我。
当雏菊和毛茛大肆开放的时候,莎立文老师牵着我的手穿过田野。对正常的孩子来说,学习语言并不是个费劲的事情,他们很容易就从别人说出的词汇中接触和学习到语言。但对于一个聋哑小孩而言,掌握语言必须要经过一番缓慢而痛苦的学习过程。我知道了阳光和雨水如何滋润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木,令它们长势繁茂,开花结果。但无论是哪一种过程,其结果都会令人无比愉悦。随着知识的增长,我对我所生存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感兴趣。
这样纠结的情绪持续了好几年。对于那些失聪儿童来说,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最简单的成语和表达方式真是太难了,你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或者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掌握它们。紧接着,我就认出了这是金合欢花的气味。那些有听力的孩子可以从不断的重复和模仿中学习这些语言。
我离开了大房子,极其渴望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在家里听到大人们的交谈,这些谈话无形中刺激了他们思维的发展,而交谈的话题也是他们感兴趣的,因此无须刻意学习,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种天生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在失聪儿童那里是行不通的。虽然已经记不全了,但是有几个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父亲,姐妹,老师,这些词语把我带进了一个缤纷的世界,“就像亚伦的魔杖,一挥之下,遍生花丛”。
“爱是什么?”我问道。我全身蜷缩在树杈之间,仅仅的抱住树干,任凭枝叶在我身上鞭打。
除此之外,与人交流对我来说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仅仅眼盲的人或者仅仅耳聋的人而说,掌握对话的技艺就已经很难了。我摸到的东西越多,了解这些东西的名称和用途越广,我对自己同世界血脉相连的感受就越强烈,我自信和快乐也随之越来越多。而对于那些既盲又聋的人而言,可谓是难上加难了!他们不能辨别语气的快慢、声调的高低,这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朦胧意识,也无法观察讲话者的面部表情,而通常一个眼神就能展示出讲话者的心思,但这些信息,盲聋人是接收不到的。
因为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恐惧感,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爬树。”莎立文老师回答到。
莎立文老师发觉了这一点,于是她决心不让我身体上的缺失影响我的学习。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了发现之美,在芬芳林木的拥抱中,在每一片草叶上,在我小妹妹棉柔蜷曲的小手上,我找到了美。她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教我,告诉我怎样参与别人的对话。最后,一路上金银花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这实在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终于能同人交谈了。我坐在树枝上一动也不敢动,翘首企盼莎立文老师快些返回。又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我能够把握谈话的内容了,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
我断断续续地感到了身边强烈的震动,仿佛有某种重物坠落。
一开始的时候,莎立文老师就把我的手放在了水管边上。有一次,天气很好,我和莎立文老师散步到很远的地方,但返回的时候天气就变的燥热难耐起来。当一股清冽的水流喷涌到我的一只手上时,当莎立文老师给我讲述一件新事物时,我就只能“听”着,单纯的接受,几乎问不出什么问题。因为那是我的意识是模糊的,我的词汇也是贫乏的,但是随着接触事物的增加,我学会的词汇也越来越多。路边有人压水,我们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棵野生樱桃树下。我问询的范围变宽广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周旋于同一个主题,我渴望深入了解这个事物,熟知它的方方面面。坐在树枝间的感觉妙不可言,于是我们打算在这吃午餐。有时候,一个新词会勾起我一连串对之前对经历的一些记忆。
在学习了如何与人交流之后,接下来我的学习重点是“阅读”。每当我拼写单词的时候,莎立文老师就会拿给我一些卡片,这些卡片上面印着凸起的字母。
我闻着莎立文老师手里的紫罗兰,一边拼写单词,一边用手势比画,我想问的问题是:爱是这些可爱的花朵吗?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独自在凉亭里阅读。我学得很快,我知道每一个词语都代表着一种物体,一种行为,或者是一种特质。比如“doll”,“is”,“on”,“bed”这几个词,每一个词都有其自身对应的物体和形式。这是因为我以一种陌生而新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我有一个拼写板,最初,我能在上面拼凑出一些短句。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当时,我在花园里发现了几株刚刚开放的紫罗兰,于是我把花朵带给了莎立文老师。浩瀚未知的气氛将我紧紧围裹,一阵惊骇感袭遍了我的全身。莎立文老师想要亲吻我,表示她的欣喜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母亲,我不喜欢被任何人亲吻。随后,周围的树叶大肆抖动起来,我身下的樱桃树发出一阵震颤,如果不是我用尽力气紧紧抱住树干,迎面而来的一股狂风就会把我掀到地上。于是莎立文老师就用胳膊轻轻地揽住我,在我手上拼写“我爱海伦”。
1887年的夏天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激发了我灵魂的觉醒。于是,我就用“is on bed”表示把洋娃娃放在床上。在造句的同时,我也学会了句子的含义和正确的语法结构。有那么两三次,我们停在路边的大树下歇息。在当时再没有什么比这种造句游戏更让我开心的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了彻底的孤立无助,某种力量切断了我同朋友和坚实大地的联系。我和老师每次都一连玩好几个小时,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我们当做练习造句的道具。
现在,我已经熟练掌握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接下来,我更多的是希望学以致用。
渐渐地,我从认字卡片上的字过渡到了看书,我把自己看做一个“初级读者”。我想我已经学会了新的一课,我明白了大自然时常会向她的子民突然而公然的发起战争,在她温柔的外表下,藏着一双锋利的爪子,向人们发出出其不意的攻击。我在书中疯狂地搜寻着那些我认识的字。我摸索着来到花园尽头,我知道那棵金合欢树就在篱笆附近小路的拐角处。一旦发现了认识的字,起初是慢慢地,我高兴得就像玩了一场捉迷藏游戏一样。就这样,我开始了阅读生涯。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做算术题,或者描述大地的轮廓。慢慢的,我开始读一些系列故事,后来我还能把这些故事“复述”出来。树摇晃得很厉害,在风雨的裹挟下,我身边的小树枝噼啪作响,似乎在嘲笑我的渺小。
在莎立文老师教导我的过程中,并没有让我系统地学习某些课程。所以,当我满怀热忱地认真学习时,更像是在玩耍娱乐,也就是说,我是怀抱兴趣去学习的。我摸索墙壁走到壁炉前,蹲在地上捡起了娃娃的碎片。莎立文老师会把教给我的每一样东西用一个故事或者一首诗表达出来。她让我坐在树杈上,乖乖的不动,等她去家里拿饭回来。不止这样,只要碰到令人高兴或者是有趣的事,她都会细细地讲给我听,她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因此,我是幸运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枯燥乏味的文法,艰涩的算术题和困难的名词解释让许多小孩子产生畏惧心理,但却并没有对我造成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还都成了我最珍视的回忆。我们双双坐在温暖的草地上,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是多么的温暖。
我拨开繁茂的花枝,走到了巨大的树干下面,先是犹豫了小会,但是最终还是作出了决定,我决然的把双脚放在了树杈之间的宽阔地带,并且开始向上攀。当我们回到家里,我碰到的每一件物体似乎都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触动。保持攀登姿态相当吃力,因为树干非常粗大,树皮还磨破了我的双手。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坏的洋娃娃。可是我依然斗志昂扬,沉浸在征服困难的喜悦之中。我继续往高处爬,在树的高处竟有一个小凳子。
至于莎立文老师为什么能给予我这样超出常人的关爱之心,我无法做出解释,我想我只能感谢上天让莎立文老师来到我身边,教导我,爱我。于是,我一下子站起来,本能地伸出双手,仿佛在探寻着穿过凉亭的春天的气息。除了爱心以外,老师还具有极其出色的描述才能,她能迅速地掠过那些乏味的细节,而且从来不唠唠叨叨地问我前天都学了哪些东西之类的问题。她总能把枯燥的科学原理讲得无比生动,让我去理解而不是硬性接受。我的不安已经达到了极限,很怕大树会因为抵不住风雨的袭击而轰然倒地,到时我就和大树一起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