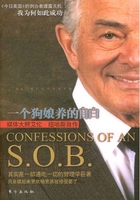霍布金太太,是一位慈祥孤独的女人。她婚后不久,孩子刚刚出生,丈夫就去世了,她含辛茹苦独自挑起了抚养女儿重担,盼望女儿快快长大。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成了他的精神支柱、生活的依托。然而女儿17岁时,长得亭亭玉立。突然生了一场急病去世了。这本该是多么年轻、多么快乐的豆蔻年华,疾病如同风来花谢,使母女无法再相聚。霍布金太太心痛欲绝,常常孤独地徘徊在鳕鱼角的海滩,独自悲伤。
有一天,一群在海滩上玩耍的盲童引起了霍太太的好奇心。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些孩子是帕金斯盲人学院学校的学生。他们引起了她的同情与兴趣。1883年秋天,她向该校申请义务工作——当孩子们的义母。
霍布金太太甜美、温柔,凡事容易紧张。而安妮快乐时情感奔放,痛苦时排山倒海,不加压抑地倾泄情绪,还有钻牛角尖的执拗脾气及丰富的想像力。她们是两个性格极其不同的人。但这些都无关紧要,霍布金太太需要的是施爱的一个对象。安妮和她逝去的女儿年龄相仿,才华四溢,又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十分惹人爱怜。
于是,安妮有了假期可以回的“家”了。夏天一到,霍布金太太就来接安妮去鳕鱼角那栋风吹日晒的灰色房屋。在这里,安妮得到了梦寐以求“家”的温馨和自由。无忧无虑,充满蓬勃生气地享受她的青春。在晚年安妮的回忆中,那是一段缤纷灿烂、生命闪烁发光,并且不可言传的美好时光。只是日子过得太快、太快了。
转眼到了1886年,安妮19岁了。这是她在帕金斯盲人学院的最后一年。日子在勤奋用功读书和一连串考试中飞逝而过,接着就是毕业典礼,在8名毕业生里,安妮的成绩遥遥领先,独占鳌头。大家公推安妮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辞。
毕业典礼那一天,早晨一起床,安妮的心就咚咚急跳。她匆匆忙忙吃完早餐,根本就食不知味,然后赶忙奔回房间,看到一件崭新的高雅亮丽的礼服挂在衣橱上。这全世界最美丽的衣裳!这一套礼服,是霍布金太太为安妮的毕业典礼亲手缝制的,针针爱心,线线关怀。
霍布金太太微笑着说道:“快穿衣服吧!待会儿还得卷头发,还要花许多时间哩!”
安妮百感交集,她从衣架上取下衣服紧紧抱在怀中。白色上好的布料薄如蝉翼,两袖长及手腕;袖口和裙据镶了三圈蕾丝花边,三圈豪华雅丽的花边;沙沙作响的轻柔丝织篷衬裙,撑着长短合宜的圆裙。安妮心情愉悦不由自主地踏着幼年时依稀记忆的轻快舞步,拖地的白色衣裳像浪花一样起伏。
霍布金太太笑到:“安妮,冷静一点好不好?不要这么兴奋,演讲还没有开始哩!过来,我来帮你打扮打扮。”
安妮说:“妈妈,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快乐!为了我的毕业典礼,您为我缝制了礼服,又为我买了白皮鞋。”这是一双样式高贵的白皮鞋!
小时候,安妮就一直认为白鞋子是为童话里的仙女们特别订做的,只上天上有,人间能有几个幸运儿穿?平凡人只配穿黑鞋、褐色鞋子。而现在这双白皮鞋是专门为安妮订做的。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快乐!”她喃喃重复。
霍布金太太故意调笑她:“我当然不知道了!”其实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帮安妮穿戴好,让她从容愉快地去赴生命中的大宴,不就是尽了母亲的心意和责任了吗?整个早上她精心地装扮安妮。洗澡是第一件事,然后霍布金太太在安妮身上洒了几滴清雅芬芳的香水,也洒在花了她几天几夜缝制的花边礼服和白色丝袜以及白色小山羊皮皮鞋上。然后花很长时间卷头发、梳头发,最后从安妮头上套穿完礼服才算大功告成。
“好了,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霍布金太太捧出一条粉红色的宽柔的丝带来,那是霍布金太太最幸福日子的痕迹。她的女儿曾经活泼健康地系着这条美丽丝带,参加高中毕业典礼。
“还是您留着吧!”安妮脱口说出,她知道霍布金太太珍藏丝带,常常怀念着女儿。
霍布金太太不说话,她默默地用丝带系住安妮的细细纤腰,仔细端详着说:“多可爱!”
安妮轻快地走到镜子前面,看到一个气质高雅,衣饰纯净的窈窕少女。“真的是我吗?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霍布金太太笑着提醒安妮说:“该走了。”
她们走过波士顿街道,到达毕业典礼会场德雷蒙教堂。
自从郝博士成功地教育盲、聋、哑的萝拉后,声誉远扬,名震全国。从此各界社会名流争相支援,赞助帕金斯盲人学院,使它历久不衰。因此每每遇到学校毕业典礼,这些波士顿的捐助者都要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
安妮看到座无虚席,人潮挤满了会场,倒抽了一口气,她一直以为只有几位老朋友和爱护她、教导她的师长们来呢,没有料想到会有这么多来宾,她愣住了,脑袋里一片空白。本来背得烂熟的演讲词,竟然一个字也想不起来。
贵宾席设在高了几个台阶的讲台上,中间有一空位留给毕业生代表,霍布金太太带着哆嗦发抖的安妮走向讲台。
“妈妈,我好害怕,我连演讲词都想不起来了。”安妮的上下牙齿格格打颤。
“没有什么好怕的,船到桥头自然直。”霍布金太太安慰安妮。
她们走到台阶,看到莫老师站在那儿,她看着安妮。
“安妮,祝福你,我们都以你为荣。”莫老师将粉红色的玫瑰花别在安妮胸前。
看着恩师亲切的笑容,安妮的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她微笑着谢过了莫老师。走向安纳诺斯先生,他等在那伸出手,挽着安妮走向台上。走向讲台中央为她保留的贵宾席上,虽然他们曾经预演过,但安妮依然紧张得全身僵硬,好像校长要拖她上断头台。而且此时的她还是想不起来演讲词。怎么办呢?真是丢脸。人们会交头接耳说,看,她就是慈善机构出来的贫寒学生,见不了大场面。不!绝对不能让人贻笑大方!安妮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典礼开始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站起来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就转向安妮说:“让我们大家鼓掌,欢迎安妮·莎立文小姐代表毕业生致辞。”
听到州长说“安妮·莎立文小姐”,安妮如同电击,该轮到她了。她站了起来,向讲台中央走去。
州长开始鼓掌,台上台下来宾也热烈地回应起来。如雷的掌声震得安妮如梦初醒,短短的几秒中,她恢复了镇静,重拾了自信。
掌声稍歇,安妮吞了口水,进出“各位贵宾”几个词。一开口,她便如释重负,记起了她的演讲辞,她昂头挺胸面对着听众。
“我们就要踏进忙碌的社会,参与创造更美好的、更快乐的世界……”她满怀信心,演讲如流水般潺潺而下,娓娓动听。
“……我个人的小小进步,推而广之,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美化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停住脚步;我们要时时刻刻充实自己,好为明日的尽善尽美奉献出我们努力的成果……”
最后,她以简洁的“谢谢各位光临”结束,所有来宾都起立鼓掌和赞赏。
接着是一连串握手、赞美和酒会。在这个过程里,安妮真的好幸福。她感受到了爱与关怀,她由衷的感谢这个世界。
傍晚典礼结束时,安妮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动,她如痴如醉,心中充满了快乐与兴奋的回忆,但愿这个辉煌灿烂的时刻永驻。无奈光阴似水,将来成为现在,现在成为过去,永流不息。
她小心翼翼的解下腰上的粉红丝带,心里默默想着“何时再穿这些?”她脱下美丽的白鞋,用干净的软布擦拭,再放进盒中。
她抚摸着上衣的每一颗珠扣,恋恋不舍地解开,把绣满花边的衬裙摊在床上仔细欣赏。“这些都是霍布金太太的精心杰作。她是多么呵护我,花了多少心血,多少钱!”
钱!一想到这里,安妮猛然清醒过来,她现在已从帕金斯盲人学院毕业了,不再是学生身份,不再是受人照顾的未成年者。她已经长大,应该独立赚钱养活自己了。否则……久久积压在安妮潜意识里的恐惧,突然溃堤泄洪。她痛苦起来:“我不要回那里去,我不要回那里去。”想到这些,安妮打个冷颤,恐惧从脚底上升,从心窝外溢。她赶紧套上厚重粗呢上衣,但还是觉得全身发冷。
其实几个月以来,她也曾经想过这些现实问题,但人的惰性使她一拖再拖,直到现在已无法回避。她已经20岁了,没有很高的教育程度,没有特殊谋生技能,一个半盲的女孩,又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安妮虽然垂头丧气,但她还是自我安慰说,天无绝人之路,何必先自寻烦恼?虽说半盲,但是老天慈悲,还是赐与了视力,可以读一点、写一点,还可以自己行动自如。晚餐铃响,她心灰意冷地走向餐厅。德士堡的阴影一直困扰着她。在餐厅门前,她打起精神,强颜欢笑。朋友们祝福她,她怎么忍心叫她们失望,为她的前途发愁呢?
毕业后,安妮和霍布金太太一起回鳕鱼角过暑假。她的日子不再像往日那样无忧无虑了,想到将来前途茫茫,她一筹莫展。秋天一到,霍布金太太又得回帕金斯盲人学院当义工。帕金斯盲人学院已无法收容安妮,该怎么办呢?
安妮想到她可以做卖书的生意,挨家挨户去卖书,散播文字的种子,去接触不同形态的人们,这不是一件高尚而有趣的工作吗?可是想到汪汪狂吠的狗,砰的一声关门,让你吃一鼻子灰的人们,倾盆的大雨……还有卖不掉书,赚不到钱的日子,又该怎么办?
或许她可以在波士顿的大饭店找个洗碗的工作,洗碗不需要太高的教育程度,况且她心灵手巧得很。但是,餐厅只请男工洗碗,她长叹了一声。
眼看暑假即将结束,安妮天天烦恼得坐立不安。到了8月底的一天,她收到帕金斯盲人学院校长安那纳诺斯先生的来信。
亲爱的安妮:
别来无恙?寄上凯勒上尉的来信,请仔细看一看。凯勒上尉为他又聋又哑又盲的小女儿寻求一位女家庭教师。你有兴趣应征吗?请来信告诉我。
请代问霍布金太太好!
祝快乐!
你的朋友安纳诺斯
接受挑战
当安妮读完了凯勒上尉的信后,感觉非常沮丧。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一点儿也不喜欢。呆在南方一个古旧小镇上,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和情趣可言呢?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轻弹手中的信。“谁要去当家教!”但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毕业以后,这是惟一能糊口的就业机会。第二天,她坐下来写了一封回信:“亲爱的安纳诺斯先生,谢谢您的培育和关怀。经过慎重考虑后,我接受您所提供的职位……”
为了教好这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学生,安妮决定重回帕金斯盲人学院一趟,因为她知道要与聋哑盲者沟通是一件困难无比的事,所以她想要回去仔细研究一下萝拉的学习资料作为参考。整整一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忙于翻阅关于萝拉所有的记录,加以细心研究。收获令她兴奋不已,然而她并不十分清楚事实真的有多困难。
当时也有许多人试验教类似萝拉的残障儿童,都告失败了。但郝博士却成功了,所以安妮一直觉得郝博士是位天才。
可是记录里有一段让安妮读得很心寒,它记载了萝拉早期的老师伯乐小姐的故事。伯乐小姐负起教导萝拉的责任,她非常喜欢萝拉,与萝拉共处了3个月。但突然有一天她去找郝博士,希望让她不再教导萝拉了,她说:“萝拉真是个好女孩,但是我再也无法忍受那可怕的沉默了。”
读到这一段,安妮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她自问:“我受得了吗?”
1887年3月3日,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塔斯甘比亚,火车站广场停了辆马车,有两个人坐在车子里。他们就是来接安妮·莎立文的凯勒太大和她的继子詹姆斯,两个人都满脸倦意。
詹姆斯先打破沉寂,底气不足的说“如果她根本没来呢?”
凯勒太太信心十足的说:“她会来的,安纳诺斯先生说她诚实可靠,她只不过迟了两天罢了。”她叹了一口气,“也许她坐的火车出了毛病,唉!詹姆斯,她该来的……如果她不来,海伦怎么办?”
詹姆斯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火车声,他说:“6点半的火车要进站了,这是今天最晚班的火车了。”
凯勒太太紧张得喘不过气,她在心中默默祈祷:“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她能来!”
车厢里走出几个人,有一个人看起来好像就是那个年轻的女家庭教师,但看起来狼狈不堪。詹姆斯在心中对她品头论足:“她像一只落汤鸡。”詹姆斯说的没错,安妮坐了3天3夜的火车,历尽折腾。她双眼布满红丝,精神萎靡不振,长途跋涉使得她困顿不已。
本来她买了是直达快车票来此地,没想到愚蠢的售票员划给她的票竟是从波士顿到塔斯甘比亚中间每站必停的慢车。终于到达了,她挺着胸,勉强挤出一丝职业性的笑容,对着面向她走来的年轻人。
他问:“莎立文小姐吗?”
他打招呼的口气令安妮的微笑停住了,安妮一向善于察言观色辨认别人的轻蔑语气。她想:“我不会喜欢他的。”
她冷淡地回答:“是的。”
他轻狂的语气依旧:“请过这边来,我的继母在马车里等着你。”
当凯勒夫人见到安妮后,她高悬半空的心才放下,两个年轻的女人相视微笑着,她们一见如故。“她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好像很善良的。”安妮心里想。
几分钟后,马车驶入一栋绿色窗帘点缀的白屋,屋前一片花园,百花锦簇,这就是凯勒家的庄园。安妮根本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大房子,只是她急切地问:“海伦呢?她在哪儿?”她现在迫切想见见自己的小学生。这时,凯勒上尉走过来。
“你好!安妮小姐,我是海伦的父亲。”凯勒上尉和安妮打招呼。
安妮以点头作答,继续问:“海伦呢?”
他指着门口:“她在那里,她觉察到这几天大家都忙着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惹得她发脾气。”
安妮看到了海伦。海伦站在门口阴影处,绿色的爬藤遮住她。她的头发像黏成一把的干稻草垂在肩上,一双肮脏的小手死劲地揪着藤叶,一片一片撕碎,上衣钮扣没有一个扣对,鞋子上沾染了尘土和泥巴。
海伦感觉马车开进门来。她全神贯注地等候,思量着从哪一边跳上去。
安妮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没有人关心这个小孩?”后来才知道海伦太调皮捣蛋了,根本不听任何人的管教,有人一靠近她,她便狂暴发怒。
安妮一踏上台阶,海伦马上就转过身来,她知道有人从大门口向她走过来,她感觉穿过脚底增强的振动频率。海伦等待着妈妈!这几天妈妈经常出门,海伦无法用言语表达她的喜怒哀乐,只能用行动表示,她张开双臂,跳进怀里,安妮接住了她。不是妈妈!海伦像一只被网罗的困兽,用力挣脱出陌生人的怀抱。安妮一紧张,把她环抱得更紧了,没想到,这一下就惹火了海伦。
詹姆斯大叫:“快放手,她会伤着你的。”
安妮吃了一惊,赶紧松手,心有余悸地问道:“难道我做错了吗?为什么?”
凯勒太太向她解释:“是这样的,安妮小姐,海伦不让人家抱她,自从病了之后,她就不曾亲过人家,也不让人家亲她、抱她。哄她。”
“有时只让她妈妈亲一下。”凯勒上尉补上一句。
詹姆斯坐在台阶上,幸灾乐祸嘲弄着安妮。“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你是来教一只小野兽,你就是一个小野兽的家庭教师。”
“说够了没?进去。”凯勒上尉严厉下令。
凯勒太太看出安妮疲惫困顿不堪,便说:“亚瑟,请先带莎立文小姐到她房间,其他的事待会再说吧!”
安妮感激地向凯勒夫人微微一笑,随着凯勒上尉走上楼梯。
安妮在上尉的背后说:“海伦该不会受惊吧!我看她愣了一下,就想挣开,看来她好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