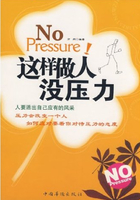离开家乡
再过几分钟,安妮·莎立文就要离开这个家,乘着马车,再转搭火车,远离而去。这让她感到非常兴奋!
“我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不在乎哪里是我的家……”安妮心里想着。
安妮知道乘马车、搭火车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她,一个只坐过一次马车的小女孩来说却是一件不平凡的事。虽然那一次坐马车给她留下的事痛苦的回忆,当时辘辘滚动的轴轮在脚下颤震,马儿们向前飞驰,而奔驰的方向却是母亲将安息的墓园。
但今天的情况迥然不同,尽管她不知道她将去何方,但她一点也不介意。很久以前,父亲曾带她去过离此地5里路的邻镇西乡,她只知道她将要去的地方比西乡更远、更远,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不过,何处是栖身之地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吗?因为世界是光明的,将来应更有希望,这是一条单行道,不许回头,只有勇往前进。好好努力吧!她把此时此刻无限感触深藏心中。
安妮环顾四周。宁静安详的村庄,祥和朴实的家宅,空寂的碧绿原野,乳白的农庄与红色的谷仓相映成趣,烘烟叶的气息随风缕缕飘散。但毕竟这不是她的家。
她只是一个寄人篱下,不受欢迎的人。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已经去世,亲戚们其实都不想要她,但为了面子和仅有的一点责任心,他们收留了她。今天她就要摆脱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生活阴影了。
如果马车不来怎么办?没有马车,她就走不了。怎么还不来呢?安妮目不转睛地眺望着马路,全神贯注,望得两眼发疼了还不见马车的踪影。她先揉揉左眼,再揉揉右眼。希望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但路上还是空空荡荡,连马车的影子都没有。
安妮决定闭上眼睛给自己许愿:数到100,马车就一定会出现的。她开始数,小心翼翼的,生怕数漏了,但刚开始数没几秒,苏达希堂嫂——也就是收养安妮的人就出现,她重重地敲门,大声喊道:“原来你躲在这里啊,从早餐时我就一直找你。”
安妮不理不睬,继续数着“32,33,34……”苏达希堂嫂开始唠唠叨叨、聒噪些没意义的话,打断了她的数目,但安妮置之不理,她强迫自己聚精会神起来,继续数。
“今天就乖一天吧!这个要求不会太过分吧,安妮!”
安妮没有回答,苏达希堂嫂也并没有期望她的回答,因为安妮一向爱沉默不语。
“我得告诉你,安分一点,听话一点,不要撒野,听到了没有,你弟弟吉米还小,听爱伦说,他臀部的疮还没有好。你带着他着时要背他,帮他拿东西,要好好照顾他……”苏达希堂嫂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我们是一家人,可以一直很容忍你。但那位好心的汤姆斯先生,你要好好对待,他与我们非亲非故,人家可不欠我们什么,却老远跑来带你去坐火车,在他面前要表现得体些,不要把咱们的脸都丢光了,还有……”苏达希堂嫂叽叽喳喳说过不停,而安妮还是默默数着数。她们各怀心思,根本没有注意到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
“98,99,100!”安妮急急地睁开眼睛。马车正好在大门口煞住。
“好灵验。”安妮高兴极了。
“安妮,安妮,我在这儿!”她注意到从车厢里探出一个小男孩的头,热切地叫喊。是吉米。
“安——妮——”吉米再一次高喊。亲情涌满心头,哽住她的喉咙。自从家破人亡,离散以后,他们姐弟俩已经好几个月不曾相见了。
这时安妮的堂哥约翰·莎立文大步走上大门台阶,
“汤姆斯先生,您好。”
“莎立文先生,您好。”
两人握手寒暄后,约翰将安妮的小包袱交给汤姆斯。那是安妮仅有的一点财产。
这时,苏达希堂嫂堂嫂突然用有力的手托住安妮下巴,将安妮的脸往上扳,安妮无法逃避,只好直视她,苏达希堂嫂泪水汪汪的,安妮很奇怪为什么她会有这种亲呢的表现。苏达希堂嫂用另一只手揽住安妮的腰,拉拢她,要亲她,安妮连忙把头甩开,她并不喜欢着突如其来的亲昵之感,她在猜测苏达希堂嫂堂嫂的真正心意,为什么她要亲我呢?要为我流泪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哼,最后一天,你总该听话一点吧!”堂嫂看到安妮的反应后,不屑地数落起来。听到这熟悉的语调,安妮心里才觉得落实了些,自我保护的戒意慢慢松懈下来。刚刚像演戏似的,搞得她浑身不自在。
约翰告诉安妮:“这位汤姆斯先生就是来接你和吉米的。”安妮朝他看了一眼,这人正含笑看着她。
“安妮,你好。”陌生人很有修养的和她打招呼,并伸手准备跟她握手。但安妮偏垂下目光,满不在乎地走过去,爬上马车,坐到吉米旁边。“哼,谁稀罕!我才不跟陌生人握手呢!”安妮心里想到。
堂嫂说:“安妮,给这位先生请个安呀!”苏达希堂嫂又开始啰哩啰嗦,讲些毫无意义的话。
安妮不理不睬,转向弟弟说:“吉米,吉米,真是太棒了。”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再也不要回来了!善感的吉米体会到姐姐的感受。他微笑着,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安妮挺起胸膛头不回,脸不转的奔向了人生的新旅程。
马车驶过放牧山,走在陌生的乡间小道上。吉米兴奋不已,不时叫安妮东看西望。“安妮,快看那房子!那个红砖房子,有4个烟囱!安妮,看到没有?每个角落都有个烟囱。快看那边湖中的天鹅,它们在水里不冷吗?”
多半的时候安妮都会焦急地喊着:“在哪儿?快告诉我。”她的眼睛不好,视力时而同常人一样,影像清楚,时而又一片模糊。今天的视力真是令人失望。远远望去一层云雾,朦朦胧胧,看不清东西。她的眼睛有严重的毛病,几乎要瞎了。
可惜马车跑得太快,还未来得及欣赏沿路风景,他们就到春田火车站了。
“都下来吧,孩子们。”汤姆斯先生开心地催促他们下车。身材高大的汤姆斯微笑着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抱下吉米,安妮则自己跃下马车。
然后,汤姆斯去买了一长串车票。
吉米好奇地问:“都是我们的车票吗?”
“是啊,因为咱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要不要保管火车票?”汤姆斯微笑着问。
“好哇!”吉米开心地伸出小手抓住身旁魁伟大汉的手。
这样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手牵着手走下车站的月台,安妮则紧跟在后。
坐火车开始的时候的确有趣,但时间一久,兴致慢慢消散了,周围情景就变得平淡乏味了。
安妮望着窗外,渐渐的困意上来,她闭上了眼睛。
吉米开始低声呻吟:“姐,好痛,好痛啊!”
汤姆斯问:“怎么回事?”
安妮刚刚几乎睡着了,现在猛醒过来对汤姆斯说:“你应该看看他的屁股,长了一个碗大的肿瘤。他们说那是‘结核’。你知道吗?我妈就是生这种病死的。”说完又闭上眼睛。
汤姆斯顿时心生同情起来。可怜的小男孩,长了致命的瘤疮,几乎瘫痪了。瘦巴巴的小女孩几乎成了瞎子。一想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更是让人怜悯。唉!
老天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他不觉满怀同情的看了安妮一眼,安妮一点也不在意,她的心早已覆盖了厚厚的铠甲,谁要人们自作多情同情她,同情安妮·莎立文呢。
日落时分,列车员巡回叫着:“德士堡到了,请准备下车。”他们3个人蹒跚地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下火车。车站上几乎无人,遥望远处才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汤姆斯带着两个疲劳至极的小孩往前走过去。
那是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黑色车厢悬在长满铁锈的高轮子上,摇摇欲坠。令人狐疑不安的是它没有窗户。而且安妮注意到车厢顶盖留了些气孔,一把链锁牢牢拴住车厢后的一扇窗户上。虽然安妮并不了解,但她深深感到这辆马车不同寻常,气氛阴森诡异。
汤姆斯先生拿起一把钥匙打开门,说道:“进去。”安妮看到里面边,有两排木板长凳。
安妮和吉米觉得它令人毛骨悚然,两个小孩子都犹犹豫豫不愿意进去。
汤姆斯吆喝道:“上去!难道要我抱上去?”他走向吉米。小男孩吓得躲到安妮后面,紧紧抓住安妮裙摆,籁籁发抖。
“你们统统过来。”汤姆斯先生想着家里摆在桌上等着他的晚餐要凉了,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听着!我得走了,我把你们交给老丁了。你们不用怕,他会带你们去的。”他指着马车夫说。那个脸上布满皱纹的丑老头,露出烟草熏黄稀稀疏疏的大钢牙笑着。向安妮和吉米点头招呼。
看到淳朴善良的笑容,安妮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她爬上马车,汤姆斯把吉米抱到她身旁。“再见。”汤姆斯用力砰然关上车门。
汤姆斯眉头深锁,目送马车驶去。身为政府官员,他依法执行任务,但他不忍心看着两个天真无辜的小孩坐“黑玛丽”。
“黑玛丽”就是专载醉汉、小偷、杀人犯等的囚车。只怪政府没有经费!只好让他们乘坐这样的车,好在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马车的来历。想到此,汤姆斯才稍感安慰,掉头离开了。
虽然光线难以射入马车气孔,寒气丝丝袭来。但安妮和吉米现在却无心他想,因为他们必须全神贯注的使自己坐稳在滑溜溜的板凳上。马车在德士堡镇崎岖的马路上颠簸,一不小心他们就会从凳上摔下来。
不久,马车奔向一个大门。大门吱嘎而开,车子驶进,停在里面一个院落里。
老丁从座位上跃下打开了车门,两个小孩跌跌撞撞地下了马车。四周暮色苍茫昏暗,黄色大门徐徐关上,将安妮和吉米关在里面,与世隔绝。
老丁把吉米的小手放在安妮手中。安妮茫然望着老丁。
老丁说:“带他一起进屋,就是最靠近我们的这一栋,我先去把马儿们放回马廊,马上就回来。”
1876年2月12日,这一天是华盛顿生辰纪念日。也是安妮·莎立文走完一段旅程,来到人生的一个中转站的日子。
安妮与吉米走上石板台阶,他们将寄身何处?
这个地方是马萨诸塞州的德士堡镇。收容他们的机构的正式名称是马萨诸塞救济院,但一般人们称呼它为:贫民救济院。
美好的回忆
安妮和吉米来到一间灯光幽暗的大厅。有个人坐在屋子的那头,忙着在写笔记,看到他们后开心地叫起来:“乖,过来一点,让我看看你们。”他的声音和瘦小的身材活像一只英格兰蟋蟀。
“你们是莎立文姐弟,对吗?”安妮和吉米点头,背后传来马车夫老丁的脚步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此时人生地疏、无依无靠,片刻前才见面的老丁仿佛是他们的百年知己。
“老丁,来得正好。”那人在桌子后面兴高彩烈地招呼,然后不停地翻本子,直到空白的一页才停手。
“我叫郭兰杰。先让我提出几个问题,再安排你们的房间和床位,先从你开始。你叫安妮·莎立文,对吗?”
“是的。”安妮回答。
“你几岁了?”
郭兰杰等了半天,没有回答。
“几岁?”还是同样的问题。
屋里还是一片寂静。
“生日是什么时候,这总该知道吧?”
安妮回答:“7月4日。”她不红心不惊地撒着自己编织的谎言。7月4日是美国开国纪念日,这一天总是洋溢着兴奋,爆竹烟火劈啪庆祝,小孩娇嫩地欢笑,嘴里冰淇淋缓缓融化,沁出浓郁的甜香。这是一个象征幸福快乐,充满希望的佳节。事实上,她的生辰是4月4日,但反正大家谁也不知道,那么假设7月4日沾个喜气又何妨呢?
郭兰杰记下了。
“可是安妮,你到底几岁呢?8岁、9岁、10岁?我想8岁吧!”郭兰杰猜错了。虽然安妮又瘦又小,但其实她马上就满10岁了。
“好,你的资料齐全了。我们问完小弟弟的几个问题就一切完备了。”
郭兰杰转向老丁,感慨万分地说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到德士堡来,真叫人心疼。这儿除了收容的那些弃婴,他们两个年纪是最小的,真可怜!”他最后看了看记载安妮和吉米的那一页。名字、籍贯、出生年月日。该写的都写上了。郭兰杰心中默默地想,除了命运,又是谁安排这两个小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呢?”
这一切都缘于安妮出生以前。她的父母是爱尔兰人,那是时候正赶上爱尔兰闹饥荒,有20多年五谷不收,遍地荒芜。贫困的小佃农家只好把家里东西一样一样地卖掉,最后卖到无立锥之地,穷得三餐不继,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只剩下两条路:一是留下来等着饿死。二是远离故乡,另谋生路。
1860年,逃荒者像澎湃的海浪般涌进美洲新大陆。莎立文家族的托马斯和爱丽丝夫妇也是其中之一。托马斯带着妻子到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叫做食禄岗的小村子。因为他听人说这个地方工作机会较多,容易糊口。
果然不错,托马斯很快在附近农庄找到了打短工的工作。开始时莎立文夫妇还感到孤单寂寞,但没过多久,爱尔兰人一批接一批,陆陆续续移民到该地。见到这么多的同乡,孤寂感也就随之消散了。
1866年4月14日,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牧师给小孩子洗礼时问给婴儿取什么名字时,爱丽丝虚弱地微笑低语:“简。”但“简”是受洗名,从这以后,大家都喊她“安妮”。
莎立文一家幸福快乐,虽然他们还是很穷,但已不再挨饿了。
安妮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托马斯便天天讲故事给她听。通常是晚饭后,他拉开椅子,把安妮抱到膝上,说:“今天要听些什么故事?”其实根本不用问,父亲讲的每个故事她都喜欢听,其中以《小红帽》为最。其他爱尔兰的神仙故事、民谣、诗歌……她也都很喜爱。
讲完了故事,托马斯就会把安妮高高举在头上,荡秋千般地摇晃着,在屋内快步绕圈,逗得女儿咯咯欢笑。这个时候,他总会大声说:“我的小安妮多可爱,我们莎立文家多么幸运!我们有爱尔兰好运保佑,谁敢来欺负我们!”
家庭变故
但是终有一天,厄运来临,莎立文家的幸运之神也随之远离,不再眷顾了。
3岁未到,安妮的眼睛就开始发痒,眼皮上长满了细沙状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由软变硬,由小变大,扎得安妮眼睛又痒又痛,安妮只得又揉又擦,但谁知道,因为这些擦揉,刺伤了眼球。安妮的眼疾一天比一天严重。
莎立文夫妇尝试了许多治疗方法和偏方。听邻居说用天竺葵泡水洗眼睛可以治好,爱丽丝便去摘生长在窗前开着红花的大竺葵叶子,用大锅煮沸。她用这些苦汁洗涤女儿的眼睛,结果安妮痛得拼命地哭叫,眼疾依然没有治好。
莎立文家并不富有,根本没有钱去看私人医生,只得等候福利机构的巡回医生来带安妮去治疗。医生来了,翻了翻安妮的眼皮,便拿出一把小刮刀,刮着眼皮上的小颗粒。安妮痛得尖叫乱抓,医生态度粗暴地喝住:“抓紧她,不许动。”
托马斯必恭必敬,走上前去说:“大夫,请您帮帮忙,请您治好我女儿的眼睛。”
“给你一些眼药膏,一天涂两次,挺有效的。”医生的话显得颇具权威。
莎立文夫妇对医生有莫大的信心,于是就安心离去。
望着他们走向街中的背景,医生摇了头,叹了气。他知道小女孩的眼睛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了。颗粒性结膜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砂眼,他不忍告诉莎立文夫妇这个病名。“砂眼”是那些有钱人才生得起的富贵病。需要阳光、新鲜空气及整洁的环境,需要肉类、鱼类、蔬菜和水果等滋养品来调养,需要花很多钱才能医好。而假如那女孩的父母有钱,她根本不可能染上这种不干不净的毛病。“砂眼”偏爱贫民窟,喜欢在肮脏的地区散布。
医生情不自禁地摇着头,不要想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吧!
祸不单行。安妮感染砂眼后,爱丽丝也生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