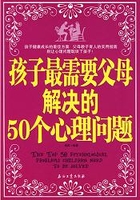路真的越来越窄,后来几乎要侧身行走。我开始担心是否迷路了,但是马克·吐温先生安慰我说:“不用担心,这片荒野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已经走进了地球形成之前的混沌中。我发誓大路就在我们视线可及的那一边。”他说的不错,大路就在离我们不远处,问题是,我们与就之间横着一条小溪,而且溪水相当深。
“如何才能渡过小溪呢?”正当我们无计可施之际,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的身影出现了。
“你们稍等,我们来接你们。”梅西先生与马车夫立刻动手拆掉了附近的一道篱笆,搭成一
座临时小桥,我们这才得以顺利渡过小溪。
日后,我再没有经历过如此愉快的散步了。当时我曾一度为我们的冒险感到担心,继而一想,只要马克·吐温先生在场,即使真的迷了路也很有趣。这一次散步就此成为我生命中一段珍贵的回忆。
我们在马克·吐温先生家住了几天。在临走的前一个晚上,马克·吐温先生为我们朗诵他写的《夏娃日记》。我伸出手去轻触他的嘴唇,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音调,犹如音乐般悦耳动人,大家都听得出了神。当他念到夏娃去世,亚当站在墓前的那一幕时,大家都流下泪来。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我们不得不准备回家了。马克·吐温先生站在阳台上,目送我们的马车远去,直到我们走了好远好远,还能看到他在不停地向我们挥手。马车上的我们也频频回首,望着那逐渐变小的白色建筑,直到它在苍茫的暮色中变成一个紫色的小点。
车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可世事难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面。
马克·吐温先生去世之后,我们又再次来过这所住宅,但已经物是人非了。那间有大壁炉的起居室内,已显出缺少人整理的冷清零乱,只有楼梯旁的一盆天竺葵独自开着花,似乎在怀念过去那段令人不能忘怀的岁月。
我最爱的贝尔博士
一般来说,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不是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就是联想到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只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的朋友。
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贝尔博士,可能是因为在我的生命中,他比莎立文老师还要出现得更早些吧。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而他却向我伸出了温暖友谊之手。正是由于贝尔博士的帮助,安纳诺斯先生才会把莎立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贝尔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莎立文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莎立文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众所周知,而且他这种热心还有家传渊源!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人,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人教育的读唇法。
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发明更重要。”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知者莫不敬佩羡慕。贝尔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贝尔博士那栋位于波多马克河入海口河畔的楼房典雅而美观,景色非常漂亮。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俩并肩坐在河边,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看上去非常惬意。当偶尔传来稀罕的鸟叫声时,贝尔博土就问:“父亲,这种鸟叫声应该用什么符号代表比较好?”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贝尔博士对母亲也非常孝顺。当我认识他时,他母亲就已经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快聋了。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立文老师到郊外去玩,我们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他的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虽然他是这么说的,可是当我们下车之后,正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贝尔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我爸妈好像都在睡觉,请安静点,轻点儿进去。”
于是,我们三人都脚尖着地,悄悄地走进去把花插在花瓶里,然后又走出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贝尔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能结识这样一家人,我感到非常庆幸。我常常去拜访他们。贝尔博士的母亲喜欢编织,尤其擅长编织花草图案,她会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女儿。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她们都把我看成自家人。
因为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因此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还是一位雄辩家。只要他进到房间,保证很快就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且每个人都很愿意听他讲话,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他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不过,他也有一件事情是异常坚持的,那就是在聋哑教育方面,他坚持认为口述比手语更好,他说:“当一个聋哑人用手语表达时,必然会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从而产生隔阂,他们也因此而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平。”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项研究,还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由他创立的。他因为发明电话而得到一大笔钱,但是他把这些钱捐了出来作为聋哑人奖学金。为了使聋哑儿童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努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在日常闲聊中,博士经常会把话题转到和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有一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他很小的时候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但是直到1866年才梦想成真,而在这之前他的失败简直不计其数。当时我还只有12岁,所以觉得他的话就像神话故事般,听得着了迷。尤其当我听他说人们将能通过深海电缆千口遥远的东方联系时,印象更是异常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房子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对正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尔逊先生说:“华尔逊,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电话时所说的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尔逊当时吓了一大跳。
听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我说:“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
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贝尔博土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如果没有贝尔博士发明的电话探针,那么大概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至今还找不到呢!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我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尔博士和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欣赏明月的情景。那天晚上,和我们一同住在船上的还有纽康博土,他兴趣浓厚地给我们大谈月食、流星及彗星等现象。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立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而我总是回答说:“可我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啊!何况又有哪个人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土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立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我完全理解您的好意,可是如果一个男人娶了我这样的妻子,那不是太可怜了吗?而且我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只会给丈夫增加负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务事,但我相信会有心地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愿意和你结婚的话,你会改变主意吗?”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的,我后来确实曾为结婚的事情动过心,这些就暂且不谈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了飞机,显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想研究飞机制造。据他预测,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即将来临,纽约和伦敦之间在十年之内将会开辟出航线,而且在大型建筑的楼顶上将出现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每一户人家都有车库一样。贝尔博土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作为主要战场,那时候潜水艇在海上的作用将比巡洋舰还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些乐观的科学预言时,总是感到异常兴奋,但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些预言会那么快就应验。因此,当我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能利用海洋调节气候时,真的是大吃一惊!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1922年8月3日,贝尔博士离开了人世,遗体就葬在雷山顶上——这地方还是他自己挑选的。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随后还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
流星飞舞
在电人雷鸣的时候,
在星云交会的地方。
当我得知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一阵麻木,当我清醒过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永远的丧失了一生珍贵的朋友,永远。
不轻言失败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生活的进展帮助很大。
我在大学读书时,就经常这样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使用,为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总会有一两件事情是适合我去做,而且只有我才能做的。但这又是什么事情呢?我要好好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一位朋友倒都替我想好了,他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至于费用你不必担心,由我负责筹募。你觉得怎样?”
当时我回答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我暂时还不考虑这件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立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最后我们实在是穷于应付,干脆就不再和他争辩,而他竟然错误地认为我们是默许他了。于是在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没来得及起床时,这位朋友就已经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去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友朋,并宣称我计划投身于盲人教育事业,而且打算立刻操办此事。
休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洛奇先生由于当时碰巧有事而不能前来,就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大家为此事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马克·吐温先生下结论地说:“洛奇先生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在这种事上投一分钱。
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了。”
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建议我担任主角,到各地做旅行表演;也有人提出,由我出资,将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一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亏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和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却从不对我加以干涉。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真正能为盲人做贡献的机会终于来了。那是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一天,一位自称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找到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人学院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我们还曾一同去议会请愿,要求成立特别委员会保护盲人的权益。这个请愿案最终被顺利通过,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于是,我的工作也就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卞,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这些盲人制作的手工艺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了一家专卖店。后来,在马萨诸塞州各地也开设了几家相同的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