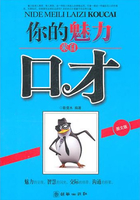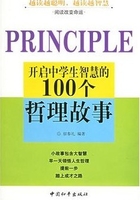对于人的头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生理学和脑科学的角度,二是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以下内容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创意思维主体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创意思维的影响。
大脑是怎样运行的
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头脑在认识外界的事物之前,是空无一物的,就像一块干干净净的“白板”;当需要认识的东西——如自然的事物、社会的活动或别人的思想观念等——进入头脑之后,便能够清晰地印在这块“白板”上。外界有什么样的东西,“白板”上就有什么样的东西;反过来说,“白板”上所有的东西,也一定能够在外界事物中找到原型。按照“白板论”的观点,比如说,我闭上双眼,任何东西都看不到,处在“一片空白”的状态;然后我猛一睁眼,那么处在我视域之内的所有东西——图书、稿纸、眼镜、水杯、圆珠笔等都会毫无遗漏地通过我的双眼进入头脑。而我的头脑对于来自外界的“客人”则是一视同仁,兼收并蓄的。如此一来,便很难产生“创意”“发明”之类的事情了。
然而,就是人的头脑,头脑的实际运作情况并非如此。人脑是地球、宇宙的全息照片。这是脑科学研究者作出的一个重要推论,并引起巨大反响。
根据全息论,人脑跟全息照片是同一原理。全息摄影能将整体的任何部分、任何片断都摄下来,产生一种真正的三维空间效果。假如你拍摄一张桌子,然后把照片撕碎,每一个碎片显示的不是这桌子的部分,而是显示桌子的整体。科学研究者和心理学家们考虑,全息照片应当与人脑相似。他们坚持认为,人脑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作的——它的部分,甚至小到一个脑细胞,都可能反映整个大脑的活动。而且人脑是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的全息照片。约瑟夫·契尔顿·皮尔斯在《奇妙的幼儿》中写道:“新生儿的大脑,作为一张全息照片的碎片,必须接受地球全息照片的感光,并与地球相互作用,以达到清晰化,或者说调整好人脑照片的焦距,如果把一个初生儿的大脑隔绝在屋子里,不让它与地球相互作用,那么清晰化就不可能达到……人脑越是长大,越是精致,全息效果也越好,人脑与地球相互作用的智慧或能力也越大。”
另一位心理学家普里伯姆把这种全息摄影的纪录进一步引申,他认为:假如人脑中真有这种全息照片,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各种信息频率在人脑中储存事物。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线性的或空间的方式把这些信息读出来。线性的方式是在一段时间内陆续进行的,空间方式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存在于大脑中,它们是从大脑中读出来的……全息照片的每一部分包含着整体。这样,全部信息都在其中了,只是观察角度和观点略有不同罢了。
既然我们的大脑是对地球、宇宙的全息摄影,底片就存于脑中。那么摄影、摄像就一定是大脑运行的重要方式了,也可以说,通过使大脑摄影、摄像、拍照,可以数以百倍地提高用脑效率。那么大脑的摄影、拍照功能又是怎样运行的呢?
人脑的大部分记忆,是将情景以模糊的图像存入右脑,就如同录像带的工作原理一样。信息是以某种图画、形象,像电影胶片似的记入右脑的。所谓思考,就是左脑一边“观察”右脑所描绘的图像,一边把它符号化、语言化的过程。所以左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质,它负责把右脑的形象思维转换成语言。
被人们称为天才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当这种思考完成以后,我要花大力气把它们转换成语言。”可见,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首先需要右脑非语言化的“信息录音带”(即记忆贮存)描绘出具体的形象。
左脑的功能可以为电脑取而代之,那么人对大脑的开发的必然选择就是开发右脑,启动全脑了,而右脑的功能突出表现为类型识别能力、图形认识能力、空间认识能力、绘画认识能力、形象认识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就是“像”,有的心理学家将其称为心像或心理图像。
可以说,右脑最突出的功能就是像的功能,它能够大显身手、大显神威的就是摄像、显像的功能。
“思想”是左脑的功能。那么右脑的以呈“像”为主的功能,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思像。思像主要指的是右脑的运行状态。
如果说右脑有个软件的话,那么这个软件就是思像,是思像软件,它区别于左脑的软件——思想,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啊!
提出思像这一概念,还有一层意思:我们说思像是右脑的软件、思想是左脑的软件,并不是说思想与思像、左脑与右脑就毫不搭界,彻底区别开来,而是思想与思像,左脑与右脑是相通相联的,其逻辑语言功能也好,显像功能也好,并非单独左脑的运动或单独右脑的运动,而是左右脑并用的全脑的启动。如果把左脑、右脑割裂开来看,那就错了。它是有理智、能思维、可以进行创意活动的总司令部。因而,思像这一概念的提出,简单地说,一是考虑了右脑的像的功能,二是同时考虑了左脑的语言逻辑功能,其中以像为主,也就是说思像包含着“思”与“像”两重意思。“思”指语言逻辑,“像”指思像。这样,思像反映的就是以启动、开发右脑为主而带动、激活全脑的用脑过程。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脑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大脑尤其是右脑的认识不断深化,美国艺术家兼教育奈德·赫曼提出了一种新全脑理论,同时开发出相应的全脑技术。这种全脑理论重视了脑部的边缘系统。脑部的边缘部位是个相当小而复杂的组织,分跨在大脑的左右两半边。这部分组织在人脑上是看不见的,只有将脑部细细解剖开,才可以发现。边缘系统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被称为“大脑中的大脑”。这种新全脑理论不是将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脑,而是分为左上脑、左下脑、右上脑、右下脑4个象限。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多项全美大奖,被誉为是“划时代的贡献之一”,并且相应的全脑训练已在全球推广。
头脑中的调色笔
经验证明,我们的头脑并不像一块“白板”,而是更像一块“调色板”。头脑把外界输入的各类信息经过调色处理之后,进而画出一幅幅色彩鲜艳的图画。这也是头脑能够产生创意思维的现实根据。
每个人的头脑都拥有许多种调色笔,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种是:实践目的、价值模式、知识储备等。
(一)头脑中的实践目的
就是我们在思考事物或者解决问题时所要达到的目标,其语言表达式就是:“为了……”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预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这个目的指导着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并且自己能够意识到目的的存在,并能想象目的实现以后的美好情景。
我投稿发表文章,是为了交流学术观点,或者仅仅是为了拿到稿费;你报名参加函授,是为了学到知识,或者是为了获得文凭;他夜以继日地搞些小发明,是为了造福社会,也许是为了讨好女朋友……于是,我们的头脑就产生了“偏心眼”:对于符合自己实践目的的事物和问题,将会给予加倍的注意;而对于那些与实践目的无关的东西,那就对不起了,一律拒之于千里之外。
在某国警官学校,毕业班学员正端坐在三楼的教室里,神情紧张地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只见考官走进教室,迈向讲台,对学员们说:“全体注意,现在考试开始!请你们立即跑步到一楼,然后跑步返回教室!”
学员们尽管迷惑不解,但是只能服从命令。他们赶快跑到楼下,并接着又跑回三楼的教室。学员们刚坐下喘息未定,考官的问题已经出来了:“请问:从一楼到三楼,共有几级楼梯?”
这次警官考试是意味深长的,能够考满分的学员大概不会有很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楼梯只是上楼下楼的通道,能够达到这个实践目的就行了,而没有必要关心它究竟有几级;但是对于一名警官来说,他应该具有比常人更为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打破通常的“实践目的”对自己眼界的约束,以便发现与“侦破案件”这一实践目的相关的各类信息。我们读《福尔摩斯探案》时便经常看到,福尔摩斯的创意思维主要表现在,他能够从普通人所忽略的蛛丝马迹中找出案件的关键线索。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熟知非真知。”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请想一想,为什么“熟视”却“无睹”?某些事物一千次、一万次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域内,我们却“视而不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事物不符合我们的实践目的,头脑感到没有必要去理睬它们。比如,你家碟子上的花纹是什么样的?希特勒的“纳粹党标志”是左旋的还是右旋的?类似的问题有许多,你大概都回答不上来。
再想一想,为什么“充耳”却“不闻”?某种声音一千次、一万次地回响在我们的耳畔,我们却听不到。原因同样在于,那种声音是实践目的之外的东西,头脑没有义务去感受它。比如,你家冰箱多长时间工作一次?每次工作多长时间?你在读小说或写文章的时候,还能听见身边闹钟的“滴答”声吗?对于这类问题,创意的主体,你的回答大概都是否定的。
(二)思考之前的知识储备
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在一次讲演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芝加哥市需要多少位钢琴调音师?”然后,费米自己解答说:“假设芝加哥有300万人口,按每个家庭4人,而全市1/3的家庭有钢琴计算,那么芝加哥共有25万架钢琴。每年有1/5的钢琴需要调音,那么,一年共需调音5万次。每个调音师每天能调好4架钢琴,一年工作250天,共能调好1000架钢琴,是所需调音量的1/50。由此推断,芝加哥共需要50位钢琴调音师。”
这是一个典型的“连锁比例推论法”,在解决实际问题和获得思维创意的过程中经常被采用。在这种推论中,需要很多预备性知识做基础。比如,你应该知道“有钢琴家庭”所占的比例、调音师的工作效率、工作时间等。
在进行任何一项创意思维之前,我们头脑中总要有一些预备性的知识。头脑把这些知识当做铺垫或者跳板,然后构想出改进物品或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自身就隐含着某种价值观念,并构成一种特定的框架,从而对头脑的观察范围和思考偏向作了预先的规定。凡是与这种规定相吻合的,头脑会予以加倍关注;而与这种规定无法沟通、风马牛不相及的,头脑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们拒之于大门之外。
所以,每个人头脑中所思考的事物和问题,都受制于自己的知识水平。正如每个人喜欢读的书不同,除了欣赏趣味之外,其差异点主要是由知识程度决定的——谁都不愿意去读一本自己根本就读不懂的书。由此看来,头脑中的知识既是创意的必要前提,又有可能成为创意的制约因素。
(三)思考之前的价值模式
在各种各样的外界事物和观念中,有些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们有用;而另一些则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对我们没用。有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有价值的”;而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没价值的”。相应地,用处大的东西,其“价值”就大;而用处小的东西,其“价值”也就小。于是,头脑在对外界的事物、信息和问题进行接收和思考的时候,便依照其价值顺序进行排列:首先处理价值最大的,其次处理价值中等的,最后处理价值小的,而对于没有价值的东西则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同一种东西,在你看起来很有用,价值大,但是在我看起来则没有用,毫无价值。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价值观上的差异。当人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就会把外界的事物或观念按照其价值的大小排列出一个顺序,也就是排列出一个主次、轻重、缓急的次序。这种次序,我们就称之为“价值模式”。
价值模式的差异对于创意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的价值模式不同,对于同一个事物或者同一个问题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些时候,创意就是从那些不同的看法中出现的。在中国人看起来,美国人的想法(实用性的)是一种创意;而在美国人看起来,中国人的想法(审美性的)同样是一种创意。其原因都在于双方的价值模式有差异。
对于个人来说,价值模式的转变就意味着一种新创意的产生,意味着他面前的世界“旧貌换新颜”,他的行为方式往往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在日本的明治时代,有一位出身世族的剑土,初到三菱公司任职,公司要求他必须对客户恭恭敬敬乃至低声下气。这使得高傲惯了的剑士感到难以接受。公司负责人便对剑士说:“笑脸迎人、低声下气,都是为了金钱。你不妨把客户当做一堆钞票,你朝他一低头,那堆钞票就飞到了你的口袋。这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这的确是一项创意,使得剑士改变了原来的价值模式和行为模式,他眼中的整个世界也都改变了。
大多数情况下,一种价值模式的建立是困难的,而一种价值模式的改变则尤为困难——对于个人、团体乃至整个民族来说,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