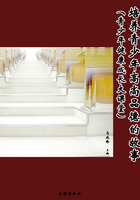对俗世中的人来说,清净是难懂的,难以达到的,然而,净心并不玄妙,它实际上就是生命的一种积极、快乐、简单的状态。只要注重加强自身的心灵建设,持续不断地净化心灵,不藏污秽,人们就一定能活得简约而满足。
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
有一天,奕尚禅师从禅定中起来时,刚好听到阵阵悠扬的钟声,禅师特别专注地竖起心耳聆听,待钟声一停,忍不住召唤侍者,询问道:“早晨司钟的人是谁?”
侍者回答道:“是一个新来参学的沙弥。”
于是,奕尚禅师就让侍者将这沙弥叫来,问道:“你今天早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司钟呢?”
沙弥不知禅师为什么要这么问他,他回答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为打钟而打钟而已。”
奕尚禅师道:“不见得吧?你在打钟时,心里一定念着些什么,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正心诚意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
沙弥想了又想,然后说道:“报告禅师!其实也没有刻意念着,只是我尚未出家参学时,家师时常告诫我,打钟的时候应该要想到钟即是佛,必须要虔诚、斋戒,敬钟如佛,用入定的禅心和礼拜之心来司钟。”
奕尚禅师听了非常满意,再三地提醒道:“往后处理事务时,不可以忘记,都要保有今天早上司钟的禅心。”
这位沙弥从童年起就养成了恭谨的习惯,不但司钟时如此,做任何事,动任何念,一直记着剃度师和奕尚禅师的开示,保持司钟的禅心,他就是后来的森田悟由禅师。
奕尚禅师不但识人,而且还从钟声里听出了一个人的品德,这也由于自己是有禅心的人。谚云:“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森田沙弥虽小,连司钟时都晓得敬钟如佛的禅心,可见其长大之后成为禅师是一种必然。
虔诚的人,能凭借虔敬带来的韧性和智慧,创造数不清的辉煌,这对于那些崇尚机巧的所谓“聪明人”,真是一种有力的嘲讽。
心净来自于简约
文道是个云水僧,因久仰慧薰禅师的道风,故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禅师居住的洞窟前,说道:“末学文道,素仰禅师的高风,专程来亲近、随侍,请和尚慈悲开示!”
因时已晚,慧薰禅师就说:“日暮了,就此一宿吧!”
第二天,文道醒来时,慧薰禅师早已起身,并已将粥煮好了。用餐时,洞中并没有多余的碗可给文道用餐,慧薰禅师就随手在洞外拿了一个骷髅头,盛粥给文道。文道踌躇得不知是否要接时,慧薰禅师说:“你无道心,非真正为法而来,你以净秽和憎爱的情感处世,如何能得道呢?”
一位居士说:心与佛土,非为二事,因山河大地,尽是心中一点微尘。更应知此心非指身中之心脏,乃指无形之心性。此心性自多劫以来,为一切烦恼,密密染污,所以不净,故有种种之污秽现相。如水腐孑孓生,木腐菌霉生,水木不腐,方是好水好木,自无出孑孓菌霉,心断烦恼,便是净心,自无污秽现相。
确实如此,人心就是一副有色眼镜,心是什么颜色,眼中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颜色。物体本身都只是大千世界中的自然存在,因为人的心不净,所以才会对外在事物作出所谓净与秽的评断。
有人说,对俗世中的人来说,清净是难懂的,难以达到的,然而,净心并不玄妙,它实际上就是生命的一种积极、快乐、简单的状态。只要注重加强自身的心灵建设,持续不断地净化心灵,人们就一定能够得到单纯而简约的幸福。
心是光明的,黑暗就难以侵蚀
禅宗典籍《五灯会元》上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德山禅师在尚未得道之时曾跟着龙潭大师学习,日复一日地诵经苦读让德山有些忍耐不住,一天,他跑来问师父:“我就是师父翼下正在孵化的一只小鸡,真希望师父能从外面尽快地啄破蛋壳,让我早日破壳而出啊!”
龙潭笑着说:“被别人剥开蛋壳而出的小鸡,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母鸡的羽翼只能提供让小鸡成熟和有破壳之力的环境,你突破不了自我,最后只能胎死腹中。不要指望师父能给你什么帮助。”
德山听后,满脸迷惑,还想开口说些什么,龙潭说:“天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休息了。”德山撩开门帘走出去时,看到外面非常黑,就说:“师父,天太黑了。”龙潭便给了他一支点燃的蜡烛,他刚接过来,龙潭就把蜡烛吹灭,并对德山说:“如果你心头一片黑暗,那么,什么样的蜡烛也无法将其照亮啊!即使我不把蜡烛吹灭,说不定哪阵风也要将其吹灭啊!只有点亮心灯一盏,天地自然会一片光明。”
德山听后,如醍醐灌顶,后来果然青出于蓝,成了一代大师。不管身外多么黑暗,只要你心是光明的,黑暗就侵蚀不了你的心。
不要被别人的言语所诱惑,围绕着你的心去生活,就能绽放你自己的生命色彩,实现你生命的圆满和美丽。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世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宋代禅僧茶陵郁的一首悟道诗,他说的那颗明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灵,一个人只有找到自己的心灵,才能真正修为有成。
心中不藏秽影
有一位小尼姑去见师父,悲哀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已经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多年,每天在这青山白云之间,茹素礼佛,暮鼓晨钟,经读得愈多,心中的妄念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怎么办啊?”
师父对她说:“点一盏灯,使它不但能照亮你,而且不会留下你的身影,就可以体悟了!”
几十年之后,有一所尼姑庵远近驰名,大家都称之为万灯庵。因为庵中点满了灯,成千上万的灯,使人走入其间,仿佛步入一片灯海,灿烂辉煌。
这座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那位小尼姑,虽然年事已高,并拥有上百个徒弟,但是她仍然不快乐。因为尽管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却无论把灯放在脚边,悬在顶上,乃至以一片灯海将自己团团围住,还是会见到自己的影子。灯愈亮,影子愈显;灯愈多,影子也愈多。她困惑了,却已经没有师父可以问,因为师父早已去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她圆寂了。据说就在圆寂前终于体悟到禅理的机要。
她没有在万灯之间找到一生寻求的东西,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道。她发觉身外的成就再高,如同灯再亮,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唯有一个方法,能使自己皎然澄澈,心无挂碍,那就是,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是啊,点亮心灯,人生才能温暖光明,由心灯发出的光,没有留下自己的影子。
外在声色如梦似幻,内在心灵湛然寂静
峨山慈棹禅师在月船禅慧禅师处得到印可,月船就对他说道:“你是大器,至今终能成就,从今以后,天下人莫能奈你何,你应发心再参善知识,不要忘记行脚云游是禅者的任务。”
有一年,峨山听说白隐禅师在江户的地方开讲《碧岩录》,便到江户参访白隐禅师,并呈上自己的见解,谁知白隐禅师却说道:“你从恶知识处得来的见解,许多臭气熏我!”
于是,便把峨山赶出去,峨山不服,再三入室,三次都被打出来。峨山心想:我是被印可的人,难道白隐禅师看不出我有实悟?或许是在考验我吧!便再去叩禅师的门说道:“前几次都因我的无知,而触犯了禅师,愿垂慈诲,我一定虚心纳受。”
白隐禅师道:“你虽担一肚皮禅,到生死岸头,总无着力,如果要痛快平生,须听我‘只手之声’(参一只手所发出的声音)!”
自此,峨山便在白隐禅师座下随侍四年,三十岁那年终于开悟。
即便是峨山慈棹禅师,要达到心灵的豁然开朗也要四年时间,何况我们呢?当然这是现代社会,文明昌盛,人人耳聪目明,我们未必要花漫长的四年,可一点工夫不花就想捞到人生终极的解脱快乐,恐怕也是怪诞之谈。
一旦尽力去聆听那“只手之声”,你就踏上了心灵的解脱之旅。通向心灵奥秘的桥梁架起来后,眼睛会说:“你超越我看见的东西。”
心灵说:“视觉、听觉的彼岸布满奥秘——你是来自彼岸的使者,就好像夜阑降临,地球的面前显露的星斗,万古长空如今一朝显露。”
正所谓“外在声色如梦似幻,内在心灵湛然寂静”,外部环境复杂嚣噪,内部心灵又是深埋于思想之下。与其被外界的烦扰弄得心神不定,何不明白自己的心灵,倾听无比奇妙的“只手之声”,一劳永逸地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脱?
侧耳倾听蝉鸣声
默雷禅师有个叫东阳的小徒弟。
这位小徒弟看到他的师兄们,每天早晚都分别到大师的房中请求参禅开示,师父给他们公案,用来拴住心猿意马,于是他也请求师父指点。
“等等吧,你的年纪太小了。”但东阳坚持要参禅,大师也就同意了。
到了晚上参禅的时候,东阳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在师父的旁边坐下。
“你可以听到两只手掌相击的声音,”默雷微微含笑地说道,“现在,你去听一只手的声音。”
东阳鞠了一躬,返回寝室后,专心致志地用心参究这个公案。
一阵轻妙的音乐从窗口飘入。“啊,有了,”他叫道,“我会了!”
第二天早晨,当他的老师要他举示只手之声时,他便演奏了艺妓的那种音乐。
“不是,不是,”默雷说道,“那并不是只手之声。只手之声你根本就没有听到。”
东阳心想,那种音乐也许会打岔。因此,他就把住处搬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这里万籁俱寂,什么也听不见。“什么是只手之声呢?”思量之间,他忽然听到了滴水的声音。“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只手之声了。”东阳在心里说道。
于是他再度来到师父的面前,模拟了滴水之声。
“那是滴水之声,不是只手之声。再参!”
东阳继续打坐,谛听只手之声,毫无所得。
他听到风的鸣声,也被否定了;他又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但也被驳回了。
只手之声也不是蝉鸣声、叶落声……
东阳往默雷那里一连跑了十多次,每次各以一种不同的声音提出应对,但都未获认可。到底什么是只手之声呢?他想了近一年的工夫,始终找不出答案。
最后,东阳终于进入了真正的禅定而超越了一切声音。他后来谈自己的体会说:“我再也不东想西想了,因此,我终于达到了无声之声的境地。”
东阳已经“听”到只手之声了。
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谜,人最不了解、最不明白的,恰恰是人本身。最看重智慧,竭力追求智慧的古希腊人,却树立了那块赫然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石碑。在生存和死亡相伴的旅途中,人的本质是一个独行者——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