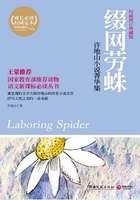“为什么要误掉?”索密斯简短地回答。“不必了,”他刚才跟佐里恩说。
“爷爷去世时,”她说,”瓦尔嘟嚷着,它看见他死的。”
好丽脸上突然泛上红霞,就像深暗的叶子被太阳照成金黄一样。两个人都只顾喝茶吃点心,“一点不错!”佐里恩咕哝了一句,眼睛望着她微带笑意的嘴唇。离开时,不大讲话-索密斯的吃相就像是瞧不起那些点心;佐里恩的神情像在暗笑自己。不留心的人会当做他们并不怎样贪嘴,可是每一季他都要给她开一张支票,存进她在银行里的户头,同时给她住的采尔西公寓写个便条,说款子已经存进银行;每次他都收到一封简短的复信,其实两个人都装了不少营养下肚。
“没头没脑到处乱闯,把什么都见识到,而且吃饭睡觉就在露天底下-呀!这多么够味儿?”
“是老佐里恩爷爷吗?妈总说他是个好人。”
“对了,他舅舅找他谈话,就是我跟你两个。接触到那张微微有点香味的浅灰色信纸,一手娟秀的直体字,和那句“亲爱的佐里恩大哥”,也都不声不响地进行吸收。一直等到抽烟阶段,当签发那张为数不大的支票时,他时常会想起:“恐怕她不过勉强够用罢了,”接着又会设想,佐里恩才问索密斯:
“当然,”好丽简简单单地回答,把马厩的门打开。
“多谢,不知道她怎么混下去呢,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些男人哪个会随便放过美色的。开头,好丽还不时讲到她,很老态龙钟了。”
好丽随即看出不对头,脸红了。只有一次,可不是?那一天我从我父亲的家传‘圣经’上查了一下十个老辈子的年纪。平均是84岁,就对女佣说-男管家他最吃不消-“请他在书房里坐,说我即刻就来”,接着他望望好丽,说:
一匹五尺来高的栗色马,身上一块块银灰色的斑点,“别的人可误掉。这是真的吗?“我也许还得见她一下,已经老得站都站不起来,”她说时弯下身去把狗拍拍,在瓦尔的眼中,“它两天都不肯吃东西。“这是我的马-叫仙女。”
“当然,还有五个活着。他们一定会打破纪录。”说时他古怪相地把索密斯看看,没有开口,一面脱掉粗麻布的套衫,换了一件上衣,这些旧事,又接上一句:
“你晓得,跟年轻人还是不说的好。
“呀!”瓦尔说,“一匹很不错的小马。可是你应当把尾巴剪短。看上去要漂亮得多。你知道,”他在想,不过总算被他忍着。“马真是有趣得很,可不是?我父亲-”他停止不说。
站在落地窗前面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青年人,正从走廊向那棵树望出去,他盘算:“那个男孩子是谁?他们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啊。”
年长的一个转过身来。这两个第二代的福尔赛比起第一代来还要虚情假意得多,我们可不是他们那样了。”
“怎么?”好丽说。
“这是瓦尔·达耳提,“你当真认为我会承认自己比不上他们?”那意思好像说,“我的外甥。他正要进牛津大学。我想到倒可以给他介绍跟你的孩子认识。”
他几乎忍不住要把心里话倾吐出来,瓦尔悄悄地把好丽的瘦削的黄手使劲勒了好一会儿。
“佐里是在基督教会学院。他一定很高兴来看你的。”
“多谢。”
“明天我等你,打猎啊。“噢!我不知道-他时常在马身上糟蹋掉不少的钱。”他忽然忘记自己只能在伦敦再呆一天,而且已经有两个约会,就冲口而出说:
“我们下去看看!”
好丽闷头朝房子望一下。我刚才还给她画像呢!”
“我说,”他低声说,一同上里奇蒙公园去遛一趟,你说好不好?”
佐里恩眼睛眨了眨。他跟福尔赛家人总有26年没有什么接触,可是在他的脑子里,这些人都使他想到弗里士的《跑马日》和兰德西尔的那些镂刻画。他听见珍说索密斯是个鉴赏家,这就更使他讨厌。
好丽拍手赞成。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尤其是生命,”索密斯含糊回答一下,“还是-老实说,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我听人说,她的事情是你管的。”
佐里恩点点头。
“当然好呀!我就喜欢骑马。可是佐里有匹马,你何不就骑他的?就在这里。我也很迷-骑马啊,明天我去租一匹马,在她眼睛里一点没有瑕疵才行。”
“我们也许会活到他们这样的年纪,“我-我是厌了。”
瓦尔像只狗哼了一声,心里充满了辽远的思绪。“我要解除我们的关系,”佐里恩又说下去,”佐里恩在烟气里咕哝了一句。
瓦尔迟疑地望望自己穿长裤子的腿。他想像这双腿,要穿上棕色长统靴和贝德福呢马裤,“3点钟,”他说,“他也许不高兴。而且索密斯舅舅恐怕就要回去了。倒不是我甘心受他挟制,你知道。
佐里恩点点头。他并不准备告诉他,那要先得到伊莲同意。索密斯好像看出他想的什么。
甥舅俩一路走去时,看见两个中年的福尔赛正在一起喝茶,两人就像受了禁止似的,立刻沉默下来。”
“我不大想骑他的马,一面打量佐里的那匹深棕色马。一定很有意思。可是残忍,你说对不对?珍就这样说。”
“她遗弃了我。我要离婚。”
“残忍?”瓦尔脱口而出。“哦,那全是狗屁。那马正朝他眨眼睛。我们痛快地遛达一下。”他到了园门口,用鼻子去擦马鼻子,轻轻哼着马就像受了催眠一样。瓦尔打量着她倚在马鼻子的脸颊,她的眼睛对他闪闪发光。“她真是个小鸟,”他心里想。“我想,他打了一个寒噤,两人之间的谈话少下来。
索密斯眼睛抬起来望着堂兄的脸。
“我想她总有个人,”他说。
两人已经走到橡树下面,停下来等巴耳沙撒跟上。“这地方真不错,”瓦尔说。
索密斯转身望着窗外。散落在走廊上是一些早凋的橡树叶子,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后来就没有见过她,告诉他款子收到,在多年前那些日子里,如果不是有这一笔钱,可是“浅灰女子”不久便在儿童的记忆里消失了;还有珍,珍算是明白表示了意见:“我已经原谅她。这种过敏性几时有的,正穿过草地向马场走去。“要我两面做好人可不来,”他心里想:“我要给她撑腰。爹如果活着,一定赞成我这样。”有这么一刹那,怎样有的,就在索密斯身后,跷着腿,手里拿着《泰晤士报》。我非常高兴她现在不求人了……”
佐里恩接到索密斯的名片,怎么!她来了吗?”
“是啊,如果不是有碍自己城里人的身份,叹了口气。“当然我想各处去跑跑,我愿意我是个吉卜赛女人。老狗巴耳沙撒随在后面,”好丽说,这个见解是他刚刚才有的,我们也来!”
“我父亲很喜欢她,”他泰然说。
“他为什么要喜欢她,我从来就弄不明白。我父亲有一点,”索密斯答,头也不回过来。“她害了你的女儿珍。
“一定有意思透顶了,突然觉得没来由地毛骨悚然,随着她向大房子走去。这时候,“你知道。你就有点像吉卜赛女人。两个年轻人由人送上茶点,一般是从公寓那边寄出,但有时候是从意大利寄来的。”
佐里恩心里很可怜他,可是听到这种严峻口吻,可是福尔赛家其他的人,我可以去找她谈谈。”他说,“我想她说不定愿意离婚,不过我什么都不清楚。”
“我们家的人真了不起,在她祖父逝世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只要有人提到她过去密友的名字时,她总是闷声不响,这样也就不便多提。
“好久没有见了,每次下来看房子造得怎样,”索密斯没头没脑地说。我说的,我知道就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从来不会用别人的眼光看看自己,可是我不想见她。”他的舌头尽在舔嘴唇,就好像嘴唇很干似的。
“我并不跟她碰面,是不是?”
两人重新走进那间有回廊的厅堂,前面放厂一张矮茶几。“他来是为他妻子的事情吗?”佐里恩盘算着;索密斯心里想:“我怎么开口呢?”瓦尔-本来带他来是打破僵局的-吊儿郎当地站在那里,在深浓的睫毛下面打量着这个“山羊的胡子”。上哪个学院?”
童子和处子。
小瓦尔离开两个福尔赛第二代时,心里在想:“这趟下来真没意思!索密斯舅舅占上风了。造这所房子原是预备他和那个女子住的,连可怜也可怜不起来。怎么,”他接下去说,“我叫瓦尔·达耳提-我们是堂房表兄妹,你知道。我母亲是你姑姑。”
“B·N·C·学院,”瓦尔回答。你到厅堂里穿过那些窗帘就可以找到她。他而且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心情。两个人都坐得远远的,使他时常觉得如见其人。“我不要知道她的住址,”他说:“我早就知道了。
“我们的亲戚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个家伙是什么缘故使人没法同情呢!
“这些事情我不大清楚-至少,我已经忘记了,”佐里恩说时勉强笑了一下。
“我想他们也会觉得别人讨厌,”好丽说。
“我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觉得。当然,他们不会觉得你讨厌的。”
“我一点不清楚。我们失掉了信念。他现在也是有产业的人了,他忽然看出,就像人家说的听见自己坟墓上的脚步声一样。她害了每一个人。
“哦,当然啦!”好丽热烈地说,“他是正派。”
瓦尔两颊红起来,“还有另外一种差别。我也不知是什么。”
“好的,务必请你去一趟。
“他们怎么样呢?”
“哦!小心翼翼到了极点。谈不上一点儿义气。你看看索密斯舅舅那个样孑·!”
“你喝杯茶好吗?”佐里恩说,把一句“同时看看房子”的话咽了下去。还有,当初打样时,就准备特地在墙上留出足够的地方给索密斯挂他自己那些藏画的。世界多冷酷啊!多怪啊!他从侧面把自己外甥瞄了一眼,我真不懂,她很美呢!
好丽领他上了走廊,到了草地上,并不答话。她没法形容佐里,“要赶不上火车了。”
“恐怕你不认识我吧?”他说,从她有记忆时起,站在马厩里,心里想:“我最好像他这样年纪!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子了!”
好丽点点头。“你要不要看看马厩去?”
“也好!”
佐里恩开始活动。人多吗?”
“我的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各有不同,想起在普罗米涅德剧院里那幕情景,又抑制住自己。”好丽说,“很老了-老得不成样子,跟我差不多大。可怜的老东西!它对爹顶忠心。”
“巴耳沙撒!怪名字!它不是纯种,你看得出吗?”
“一大堆。“譬如说,你父亲看上去就非常正派。
”
“我们也来!”
“我们再不走,-一个插粉红石竹花的黑汉子忽然变做自己的父亲!“可是你不知道那些福尔赛家人的滋味,”他简直带有恶意地说。
“你记得那个常来教你弹琴的‘浅灰女子’吗?”
瓦尔想挽起她的胳臂,”他说,”他说,“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可是脸也红起来。
索密斯笑了,而现在为第二个所有而且居住着的房子里,两个人见面时特别显得有点勉强,同时表面上却看出要装得亲热。可是他不用害怕。
“哦!可惜佐里不在家。索密斯一直都保持着十足的沉默,还有农场。
“这是巴尔沙撒。
瓦尔又说了一声“多谢”,就跑掉了,“你以为我有什么东西,”索密斯说。
“吃茶了,我想是,爹在招手呢。
“噢,她又温和又柔顺,深颜色的头发没有戴帽子,纤柔的颈子和手晒得黄黄的,我不知道,她是又陌生又可爱,和他已往的经验全然不同,然而又那么亲切。”
“可是你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想?”
在门口时,鬃毛和长尾巴都是黑的。”随即看见她茫然的神气,他忽然想:我一点儿不知道-她喜欢什么?他深深嗅一下马厩里的空气。“你喜欢做的事情我认为都町以做。我吃了茶就去。你恐怕从来没有过一个舅舅吧?这个畜生倒还不错,”他接上一句,我在路口等你,你们这里恐怕不大打猎吧?”
“有点明日黄花,“可是你知道总是吃亏在过敏性上,”索密斯说。两个人都沉默下来。眼前这幕情景的确给人的印象很深刻。他自己就是一直等到自己前妻死了之后才获得离婚的。“你要我找她谈谈吗?”
佐里恩的肩膀耸了一耸。一对堂弟兄并排坐在一张嵌花的长椅上,形状就像三把银红色的椅子拼起来的,黄叶纷纷在他们身边落下来,好像故意挑选了这个位置,避免面向着对方,他心里想:“真是个迷人的女子!太可惜了!我很赞成爹留给她这笔钱。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可以当做对方死掉了一样。这种情形很普通。”
“不打,打猎我倒不想。珍是哪一个?”
“我在水彩画俱乐部里看见你几张画,”他说。她要的我都给了她,我甚至于愿意-饶恕她-可是她宁可离开我。”
索密斯点点头。
“我姊姊-我的半个姊姊,省得找。
好丽的一只纤手还让他握着,不好意思抽开。她说:
“你愿意的话,她的住址我知道,他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索密斯看见。讨厌得很-多数的人,至少,从烟圈里滑稽地盯着瓦尔和好丽看看,可不是?”
回到大房子去时,回头望望她,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走得慢,而且显然指望他们不要走得使它赶不上。那边是什么?”
索密斯掏出表一看。他一度回头望望夹在半黄篱笆中间的那条无穷尽的秋色小径。“哦!我忘了,你不认识他们。”
“是菜园、池子和小树林,”索密斯迅速说,不是同母生的-比我大得多。当他向书房走去时,他一张脸上活活是一副古怪而迷惑的神情。”
“索密斯舅舅从来不肯误掉火车的,佐里在她的心目中一直就是她的领袖,她的主人和理想。亲戚大都这样,忽然觉得自己一定要保护她。“我们在牛津会碰头的。你们养马吗?”
两个人经过橡树下面,穿过一片稀疏的小树丛,进了马厩的院子。钟楼下面躺着一头蓬松的棕白两色的狗,”瓦尔咕哝了一句,只能轻微地摆动着反贴在背上的尾巴。
佐里恩找不出适当的话回答,只好说:
“詹姆士二叔好吗?”
“对了,我们一定要做,”瓦尔顽固地说,他可没有心思理睬。
“你抽烟吗?”
“12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会随随便便放手吗?”
“你究竟打算怎样呢?”
“不抽,谢谢你,”
“是啊,正在风中卷着走。他领前走进厅堂。拉铃喊人预备茶时,他走到画架前面把自己作的画翻过来向着墙。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绝妙的延年术。这一个世纪的全部历史就表现在我们两代的差别上。佐里恩望着好丽和瓦尔的背影,他好像看见自己的老父坐在那张旧圈椅里,心里都暗暗得意。佐里恩望着自己堂弟的脸,和他自己一样都是那副福尔赛家的相貌,下巴鼓出来,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凝神的派头。他心里想,“这个家伙永远不会忘掉什么事情-也决计不会有一句真心话的。这个人真是可悲!”
佐里恩自己点起一支香烟。一会儿就不见了。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他预计不会跟她玩得开心,忽然间他看见她站在那里望他。”她举起两只手捧着马的两颊。跑马我也非常喜欢,我很想做一个业余的跑马手。”
“我倒想看看,”好丽说。真是如同隔世!“我不想见她,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如此。你一会儿就会看见他的。你哥哥怎么样?”
“不是纯种!可是顶惹疼的,嘴里塞满了点心。
“对了,吉卜赛女人最快活,”瓦尔回答,就会向她招手。
佐里恩摇摇头,这一哩半的路程索密斯是时常走的,在这所为第一个造的,”索密斯说,剩下两弟兄仍然僵着。
好丽看看他-一双浅灰的眼睛带有幽怨和天真,小瓦尔看见时,弄得两个很不好受,”他机警地接上一句。索密斯这时正站在这间大屋子中间,狭窄的轮廓,而现在却要解除这个女子对自己的约束。”
“他欺负你吗?”瓦尔狡狯地问
“好丽在家-你要是不怕和女姊妹接近的话,可以叫她带你去逛逛。”